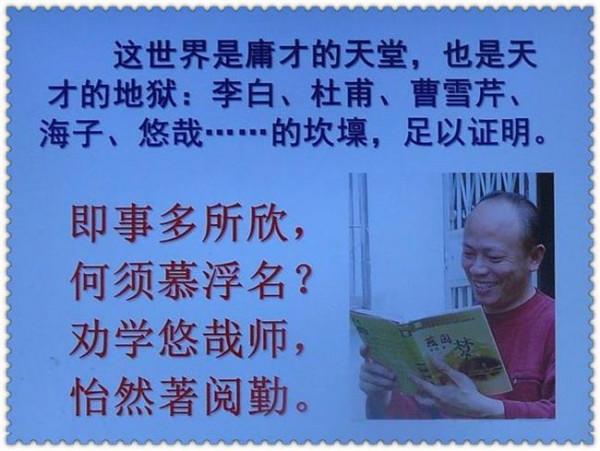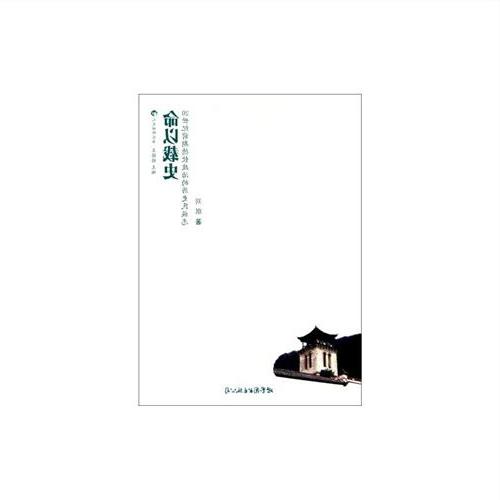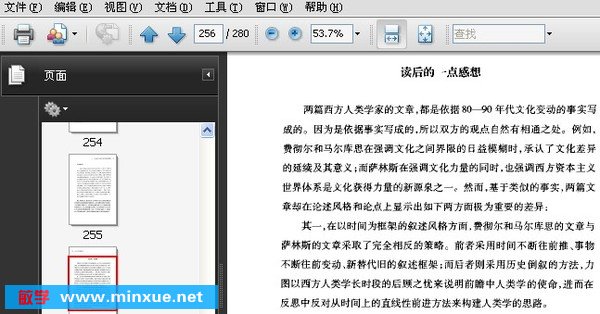王铭铭人类学讲义 《人类学讲义稿》试读:一、人类学
一提“人类学”,人们眼前便浮现出某种古怪人物的形象——用放大镜费力端详一块化石(通常是猿人头盖骨或牙齿化石)的老学究,在神话堆里漫游的哲人,身着探险家制服(有点像军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考古学家,坐在摇椅上玄想关于人的宗教本性的哲人,穿越于丛林、山地、雪山、草原、农田之间,亲近于自然的过客,总是不着边际地过问最平凡不过的生活的“好事者”……人类学确与这种种形象所代表的求知方式有关。
而如上所说,近代以来,欧美人类学形成不同的风格,风格的差异,使我们面对一个困境:人类学汇聚的知识,既从如此众多的渠道涌来,则人类学家所涉足之范围,便因之宽泛得不易界定。
为什么古人的化石、神话、考古、宗教、日常生活的研究可以叫做“人类学”?这本身更不好理喻。
加之,人类学家用以把握其具体研究内容的理路似过于芜杂,此人类学家说,人类学是对个别社会的素描,彼人类学家说,人类学的追求在于从广泛的跨文化比较中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人类学家说东道西,常导致迷雾重生的“乱象”。
在人类学界,即使已成专家,对其学科到底为何存有这样或那样似是而非的印象,似乎以为正常。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专家们之所以是专家,好像是由于他们对于这门学科的边界,向来没有存在过一致意见。
这个现象既有浅层次的解释——兴许专家不一定很“专”,也有深层次的解释——同一名称的学科,在不同国家却有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定义。19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刚从百般破坏中走出来,百废待兴。
一些高校里致力于重建这门学科的老师们教导学生说,若要重建这门学科,就要效仿国外,而所谓“国外”,当时主要是指以上所说的“大人类学”及其在当今美国的遗存。在重新引进人类学时,老师们面对一些问题。
美国人类学依旧如19世纪的西方人类学,是个宏大的体系,但国内这门学科却因已“四分五裂”,而难以作为整体立足于学林。记得我的老师们一提到人类学包括体质、考古、语言、民族,便迅即遭到同行们的质疑:“这些能不能被你们包进去?”于是,老师们便反复写文章,致力于澄清学科之间的区别,就此,他们消耗了不少光阴。
当时中国人类学家面对的难题,今日尚存。今日,人们似乎不再过分质疑人类学存在的合理性了,但搜索一下带“人类学”三个字的学术期刊,你能发现,那本叫《人类学学报》的杂志,还是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办的;它刊登的文章,大多数属于体质人类学的范围。
你去图书馆查阅人类学的书籍,会发现,它们有些放在社会学或民族学边上,有些居然与动物学与植物学并列。
你若是问一位知情的专家,要了解人类学这门学科,可看的学术杂志有哪些?那他肯定会举出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则尽与“人类学”这三个字无关。不少人类学研究者的科研成果,如果不是发表在综合性的学术杂志(如各大学学报),便是发表在《民族研究》、《社会学研究》这样的非人类学杂志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兴许历史就是解释。1949年前,中国学者理解的人类学,确与我的老师们所理解的“大人类学”相似。
到了50年代,因政治原因,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学科重组,人类学一部分进了民族研究,一部分进入生物学,一部分进了语言学,再到80年代学科重建之时,这门学科又有一部分进到社会学里去了……这段历史,令那些致力于学科重建的老师们感到无比郁闷。
对学科存在的这种中外“不接轨”现象,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抱怨”。对人类学接触愈多,我们愈加明了,国外这门学科的定义,与国内一样混乱。
美国式的“大人类学”,在英国子虚乌有。英国除了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CL)比较有“大人类学”的野心之外,其他四、五十个人类学系,都自称拥有“社会人类学家”(social anthropologists)。
这些学者对于体质人类学漠不关心,还时常讥讽这类研究,说它们不三不四。法国人类学过去长期叫“民族学”(ethnologie),德国与人类学研究接近的东西也长期叫“民族学”。令人困惑的还有,在西欧各国内部,不同时代学者对于同一门学科定义如此不同。
比如,20世纪初,法国人类学曾以“民族学”为名,为社会学年鉴派学者提供比较社会学的素材;到50年代,随着结构主义的确立,这门学科才在称呼上模仿英国,改称“社会人类学”,而内涵上却保持其民族学的追求,注重文化异同的研究,尤其注重对意识与无意识深层思维结构之分析。
加之人类学下属分支的领军人物一旦成为“大师”,则也可能将局部的研究推向普遍化,使局部成为学科的象征,“人类学”这三个字代表的东西,就愈加捉摸不透了。
为什么美国人类学保留了“大人类学”,而欧洲人类学蜕变为“小人类学”?背后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美国人类学主要以研究印第安人为主,对这些人的种族属性、历史、语言、风俗、精神风貌、物质文化的研究,都服务于作为美洲征服者的白人对成为美国内部“异族”的印第安人的认识;而在欧洲,学科的区分严密得多,研究现存“异族”的人类学者,与研究包括己身在内的人的体质特征、古史、语言的学者之间早已产生“分工”。
人类学到底是什么?兴许是因带着同样的焦虑,当年的哈登才企图给人一个更为清晰的印象。他在其《人类学史》的“导论”中说,人类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科学进步”:首先,[人类学]是一堆杂乱的事实或猜想,是历史学家、冒险家、传教士的遗物,它乃是各种认真程度不同的业余学问家所喜欢涉猎的地方。
其次,我们看到从混乱中产生了秩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许多建筑物,但却有着不稳定性和不完美性。
最后,它们为一座具有坚固结构的连贯整体所取代。哈登:《人类学史》,1页。哈登所言固然不是要骗人。到20世纪初期,人类学这门“科学”,确实有从“杂乱的事实或猜想”中解脱出来的趋向,它至少已形成了某种学科“秩序”,俨然成为一部巨大的认识机器。
不过,他对于学科可能有过于乐观的一面——或者说,他说这话,可能主要是在表达他自己的雄心——将古今种种与人类学相近的知识视作人类学知识机器的零部件。
把人类学视作一部巨大的认识机器,赋予这门学科“超大的兼容力”,已被后世看成是不合时宜的。历史使人郁闷。假如哈登在世,那么,他肯定会悲凉地发现,时至21世纪的今天,知识的进化与他个人的雄心,都尚未实现。
生活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学家对人类学的定义依旧五花八门,即使某些学者共享一种定义,在这个定义下给出的分支却也必定因人而异。加之,人类学家相互之间辩论得喋喋不休,对人类学研究的宗旨莫衷一是,这就使我们更难以理解他们研究的究竟为何。
耗了不少年头学习和研究人类学,对于这门稍显古怪的学科,如我这样的人,态度不乏会有一些矛盾。一方面,我可以想见,我们所从事的这门学科,是个时下多得难以引述的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的“殖民现代性”西学的“烂摊子”或“大杂烩”,它杂乱无章,捉摸不透,以捕捉遥远的故事、邻近的奇风异俗为己任,缺乏“科学”的严谨性;另一方面,我却不易放弃对这门学科的信念,而长期感到,这门学科起码还是有不同于其他所谓“科学”的精神的。
人类学求知方式的“放浪”,为了求知而展开的身心旅行,为了将我们从常识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所做出的牺牲,都让大家觉得这门学科已达到一个一般社会科学不易抵达的境界。人类学对于自身的质疑,又使我们反观社会科学界广泛存在的那些“方法论伪君子”(即那些以为引申一些外国的本科教材上的方法公式,就可以落实国内博士教育政策的人),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学的人文主义对我们而言有着至为珍贵的价值。
对人类学的反感,没有使人放弃对它的盲从;对它的盲从,没有使人放弃对它的反感。就在态度上的矛盾中,我不止一次以这门学科之“乱象”为开场白,阐述其意义,面对人类学这门“混合”与“混沌”的学科,向它的“受众”表明,要把握这门学科,先要把握它的“乱”。
这不意味着,伪装出一副“道家”模样,追求“绝圣弃智”,体认“道可道,非常道”,是我的目的;我只不过是要表明,人类学作为有关人类自身的“一堆杂乱的事实或猜想”的“堆放处”,显示出这门学科的“诚意”。
如何理解这一“诚意”?先说在我心目中占核心地位的人类学。于我看,人类学与知识的种种“乱象”紧密相关,但这些“乱象”背后,隐约还是有某种“核心”。那么,这个“核心”是什么呢?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固然也在变,但就我所认识的人类学总貌而言,它还是有某种连贯性的。
人类学的“核心”——即它的理论与方法动力源——一总在其社会与文化的研究领域之内。如美国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波亚士(又译“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所说,研究人自身的学科很多,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可算在内。
在众多其他学科中,作为类型的个体,是核心的研究内容。而“对人类学家而言,个人只有作为种族或社会群体的成员时才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学家一致关注的重点主要是群体而不是个人”。
波亚士:《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刘莎等译,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说人类学家关注的主要是作为“群体”的人,不是说人类学家与其他研究人的学科毫无关系,更不是说他们从其同行从事的体质、考古、语言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启发,而是说,世界各地的多数人类学家认定要研究人类,首先要认识人的实质,而人的实质从其活生生的社会存在中透露得最为清晰。
人类学始终关注人的“活生生的社会存在”;人类学虽指代过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但这门学科保有的“身份”,一向主要是社会科学。波亚士在论述人类学的定位时,举出一些事例,与人类学意义上的“活生生的社会”作了比较,推演到他自己的定义。
这个定义,突出反映了20世纪初以来人类学的人文主义。人类学不是自有学科以来就具备了这种定义的。作为社会科学之一门的人类学,前身深受“人是机器”这个近代哲学笼罩下的“社会物理学”的影响,其近代轮廓在1850年出现。
今日我们理解的人类学,是在这门学科此后的一些年头里才渐渐发育的。19世纪人类学家对他们的学科的看法接近于生物学,但其所受的影响、提出的观点,与这一阶段中的西方社会思潮息息相关。
在19世纪后半期,无论是称自己为“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还是“社会学家”,与其他学科的从业者不同的是,人类学家将自身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作为团体的他人”。
这个“团体的他人”,在后来的人类学反思中被概括为大写的“他者”(Other)。什么是大写的“他者”?这实指西文中相对于我群的“异类”(alterity或alien)。异类的类别,在所有人群中都广泛存在。
西方人类学“他者”观念之前身,可以向前推到希腊时代史学和哲学的先驱有关异族的论述;即使将视野局限于近代,这类观念,至少也可以推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及之后的启蒙运动的“他者”观念。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他者”是非欧洲的“异类”,对这些“异类”的解释,凭靠的是基督教的宇宙图式,“异类”常被“妖魔化”,与“魔鬼”、“撒旦”的意象接近。
启蒙运动期间,欧洲的“他者”观念产生了变化,对于“异类”的解释,与“无知”、“错误”、“未开化”、“迷信”这些字眼紧密结合起来,“异类”成为“所有真理与知性的对立面”。
Bernard McGrane, Beyond Anthropology: Society and the Oth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es, 1989, p.
ix.到19世纪,人类学家才在远古历史上及偏远的非西方寻找实属自己的同类的“异类”,以期理解“我群”的源流。
在将“他者”与“自我”相联系的过程中,人类学家重组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他者”观念,将欧洲之他者定义为历史阶段的差异,将启蒙运动时出现的无知—知性、谬误—真理、未开化—启蒙、迷信—认识等人类状况的“对子”整合为落后—进步的“认识论对子”,将欧洲近代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观念运用于自己的研究,还从生物学和地理学中汲取养分,在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里提出了有深远影响的进化论(evolutionism)。
直到19世纪终结,给后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类学家,多数是采用进化论观点的。然而,由改造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密切相关的“他者”观念而形成的进化论,不过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人类学的一个方面。
不久前,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tzfeld)说:很久以来,人类学这一学科就对它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表现出一种讽刺意味,它特别适于对把现代性和传统、把理性和迷信割裂开来的做法提出挑战。
赫茨菲尔德:“人类学:付诸实践的理论”,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3),7页。赫茨菲尔德紧接着指出,可笑的是,现代性和传统、理性和迷信这些“对子”的出现,部分确应归因于人类学自身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对于人类学家,一个最生动的形容是,他们在现场把自己的文化背景不断暴露在“异类”文化前面,一方面,他们对于自己带来的世界权力中心的文化有虚荣心,另一方面,在被研究的“异类”文化前面,他们又时常感到不自在。
同上。吊诡从何而来?源于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大凡要理解“他者”,不能不理解“自我”,反之亦成。就人类学而言,其所采用的“他者”观念,与近代欧洲的“文化自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是在观念的近代化过程中,人类学接受了其所在国各自的“民族自觉”模式,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与认识旨趣。西方人类学主要有三种传统,第一种是英国与实利主义哲学有密切关系的人类学传统,很现代,也很实在,尽管大量吸收了欧陆的观点,却一向保持自身的特征;第二种是德国和美国的,是以“民族精神”(ethnos)或“文化”(culture)概念为出发点的,相对古朴而注重历史,广泛流传于德语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美国得到发扬;第三种是法国的社会学年鉴派传统,社会哲学意味很浓。
我已指出,人类学的国别传统与欧洲三种启蒙传统有关系,比如,英国启蒙以苏格兰的实利主义为特征,注重制度与个体理性,而法国社会学派则侧重社会理性与现代性(所谓“现代”指的是有一种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德国传统则注重集体文化的历史命运及其对于个体的“号召”(要求个人承载历史命运,使集体产生“民族自觉”)。
王铭铭:“关于西欧人类学”,见其《漂泊的洞察》,43~7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