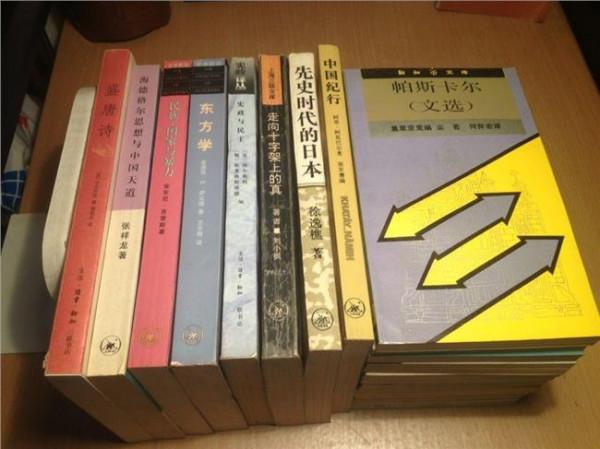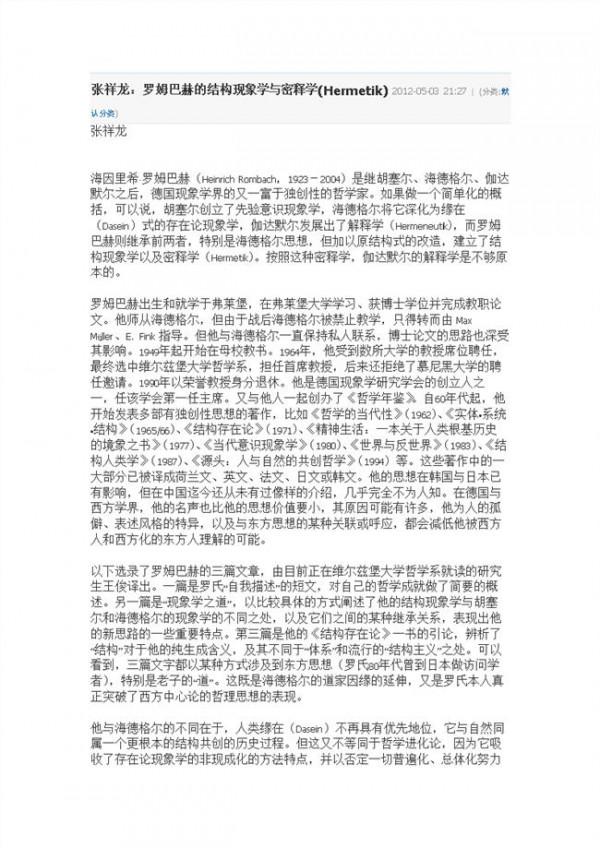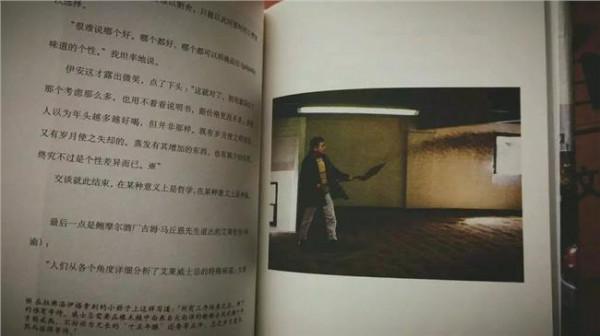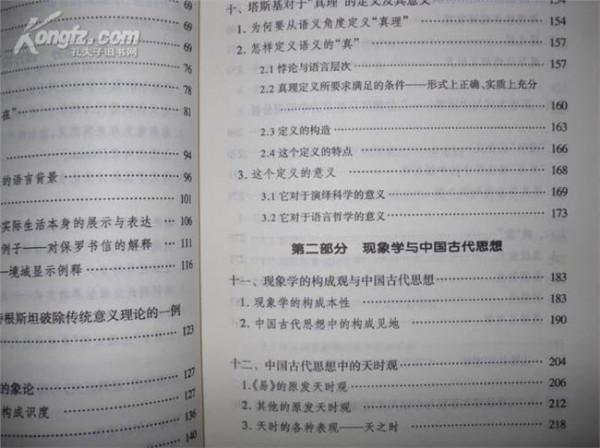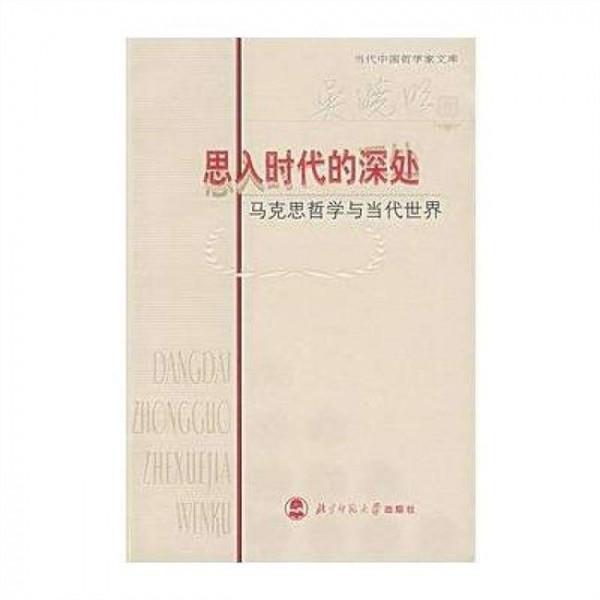张祥龙海南 读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
读张祥龙先生的书,总是有种内心激荡但说不出来的感觉。或者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时,才能体会出心智的局促和有限吧。如其《西方哲学笔记》、《现代西方哲学笔记》,大略看看,总是能生出某种新意。
又如《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一书,读起来竟然能破除诸多旧见,而向思想的深处走去。这种思想的新意和深沉的思索大概是最为重要的。所以读张氏的书,多要在看完几页之后深深呼吸,仿佛这样才抵得住那些词句中蕴涵的生意一样。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北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07年版,下引此书为此版本。坊间尚有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版,但尚未读)是一本致力于中西哲学比较的书,如果要说的认真些,比较显然不能全部把握其中的意思,或者可以说是一部让中西哲学在某种“枢机”中发生对话的书。
这样来表达还嫌不足,但是有时候人的语言会面对无限的困顿,或如本书中所提到的几位大哲学家——老子、庄子、孔子、龙树、海德格尔等——他们应该都对语言的有限性有很深的知觉。
而我总以为,哲学家就是要把那些原本不可说的东西说出来给人。或如维特根斯坦,即使他划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但是还得有所述说,而人们理解他的思想的时候,往往不是以可说或者不可说为界限,而是以沉默或者不沉默当作界限。
哲学家往往容易被误解,或者这与他们使用的语言有一些关系吧。
这样说来,我未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此语来表达本书所要展现的内容,况且,一个词肯定也是不够的。那就如此吧,或者慢慢能表达出这种意思呢。 海德格尔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在我看来,现代哲学中能和他对话者少之又少。
胡塞尔开创了现象学,而海德格尔作为现象学运动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哲学家,其对当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这里不是要谈海德格尔对现代哲学的影响,而是想说明,如果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古老的中国天道思想竟然有某种契合的话,那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现象学主张,“回到事情本身”,这个口号的实际作用是否能和它本身所表达的意思一样伟大,至少在现代哲学中已经得到了部分的说明。而现象学之眼是否能“看”到遥远中国天道观中蕴涵的本真意义,或者是这本书的作者想要阐明的思想。
张教授颇有现象学之识度,而这种识度到了对具体哲学家的解释之中就变得微妙起来,以至于处处生花,让人读之不倦。然而,即使如此,我也不敢说,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到了何种程度,这里说的,不过是一己的私见罢了。
对于海德格尔,虽然我读过几本他的书,但是也不敢妄称把握了他多少思想。游心于张祥龙先生对中国天道思想家——孔子、墨子、韩非子、孙子、老子、庄子——之解释,又往往会发现,自己现成所具有的见解竟然被一个个破除,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懊恼的事情,然而,这种懊恼又岂不让人心旷神怡呢。
如果,流行的说法能在某种书中得到新解,我倒以为是有意义的。
否则,读书则为自述耳,又何必苦心孤诣地去和别人寻找对话的“枢机”呢。而我也在此书中看到,这种对话的“枢机”发生在伟大的哲学家之中,因此才有无穷的妙趣横生。而这种妙趣,恰恰是借着原来不同的视域而生发出来的。
如果海德格尔和中国天道思想家原来就是一样的,那么对话,也就不必要了。这种对话,当然可以发生在比如,古老的天道思想家之间,因为诸子时代,儒、墨、名、法、道之间也曾经发生过几百年的对话。
虽然庄子说,学说之间的交流不过“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天下各闻风而悦,结果便是“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我倒没有那么悲观,因为如果没有先秦时期,这些伟大思想家之间的对话,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将必然是枯萎而没有文化生气的。
这种情况,当然也适合与西方哲学,海德格尔与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发生过间接的对话,而与同时代的胡塞尔、雅思贝尔斯也发生直接性的对话,这些对话,至今对我们还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而海氏与遥远而古老的天道思想家之间的对话,是我们进入张祥龙先生此书的“枢机”。显然,这些都表明状况要比庄子的想法乐观很多。然而,困难依旧存在。
今天的中国学者,往往面对一个巨大的理论困境,即中国古老的哲学智慧和西方哲学之间的交流。这种对话自清末,或者更早一些时间以来,就逐渐打动人心。然而,或者面对思想的飓风而不知所止,或者一味崇洋媚外,或者东拉西扯而不知依托。
总之,还处于一种简单的对话之中。而当代西方社会,给与中国学者的挑战更是多样而复杂的。我们往往要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挣扎,我们也必须在古老的中国哲学智慧和西方哲学传统之间挣扎,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无疑更让这种交流和对话复杂起来。
而面对无往不是的困惑,中西文化的交流,其实还在起步。或者说,还处在一种混沌之中。这个中西古今问题,困惑了近现代中国学人几百年,而在这个世纪,或者还将让中国的学者困惑下去。
作者以为,海德格尔哲学的出发点乃是“实际性-形式指引-时机化”,从这个起点出发,海德格尔拒斥了西方哲学现成化的概念框架,从而能够真正将现象学的还远贯彻到底。
我们看到,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Die Lebenswelt)还是一个不明确的意义世界,而到了海德格尔这里,生活世界因为能通过当场的体验和源发的机制而得到其意义的源出,正所谓“恍兮惚兮,其中有象”(《老子》第二十一章)。
而这意义的始基得到了确立之后,生活世界就不再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能与每一个此在(Das Dasein)发生切身关系的场域。而海德格尔正是在这样的场域中确立了自己哲学的深刻性。
与中国的哲人重视现世的情结相比,海德格尔更能与中国天道思想家们对话。然而,这种对话并不是单纯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这之间的双向互动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是一位深谙西方哲学传统的思想家与中国哲人的对话,他们之间互相沟通的意义更有助于中西哲学之间的交流。
其次,作者显然是想用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识度来重新诠释中国古老的哲学智慧,而这种阐释无疑使得中国哲学在其笔下得到了某种更新和再创造的可能性。
如此说来,对于海德格尔“形式指引-当场体验”的哲学起点的理解,毋宁说是一种中西哲学比较得来的成果。第三,这种“形式指引-当场体验”的现象学原则被用来理解中、西、印的伟大思想家,就触发出新意。这种新意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也是“形式指引-当场体验”的。
而作者持此“道枢”游刃于先哲的思想世界之中,“应其无穷”(《庄子•齐物论》),总能深入其最微妙的地方,从而得到思想之真意。 这样看来,“面向事情本身”在作者心里是有其特别意义的。
而我读此书,最深的感触就是中国思想在当场处境中要比西方的概念化哲学高明很多。我在读僧肇和禅宗的著作时,经常想到张祥龙教授的一些思想,从而渐渐就加深了自己的理解。
这种助益,不是一般的著作能给的。我以为,有些书仅给人知识性的东西,而有些书因为其方法的独到而受人重视,而有些书,总能在深处启发读者,从而有历久弥新之功。张氏此书,大抵属于后者,是能反复阅读而层出新意的书之一。
虽然其研究的内容是狭窄的,但是,通过这个狭窄的“缝隙”(Der Riss),实在是能看到一种文化之间相互比较的“枢机”和“澄明”(Die Lichtung,这个词的词典意义是林中空场,但是稍稍度过海德格尔著作的人当然知道这个词在他那里有特别的用法。
我一度觉得,其实不仅仅真理是如此的,其实哲学也是这样的。哲学,就是在黑暗中给与人一道光缝,然后让人继续走下去而看到光明吧)。而这种比较哲学的视野,乃是这种书中生发出来的境域和原则。
有一些具体的内容,如果条条罗列,则大可不必。我读书的习惯是在书页的字里行间和空白处写下自己当时的看法,需要注意的地方亦会做上标记,这些标注或者亦成为那些读过的书的一部分,将来再读的时候也就知道是否进步。
而读书,或者也如中西哲学的比较一样,“危险所在之处,亦生成着拯救”(海德格尔引荷尔德林诗),时时处处都可能出现危险,然而,这种危险如何又不是拯救呢,因为毕竟通过这种种的激荡而使思想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之中,而此境界之展开,便为有限人生之意义。
而作者关于海氏哲学和中国天道观之比较,如时间观与历史观、人格神与境域之神、人之本性、技艺、语言、道等诸多问题,读者自然能通过阅读文本而得到自己的理解,自然不需要我于此赘言。
因此,读一本书也就是就是处于一种解释学处境之中,这种处境,必然是作者和读者的双向互动,而此文本,也就成为意义的“枢机”。这种“枢机”如何就不是形式指引-当场体验的呢。
中西哲学之间的比较,或者也处于一种开放的“枢机”之中,而能否得此“道枢”以应变中西交融的危险境域,是每个读此书的读者应该去想的问题。而其理解,亦构成一种丰厚的感受,而使读者深受其益。
中西思想发生真实交流之不易(第462页)大抵从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而这种交流的开端就在于“视域的开启与融合”,而融合之处,亦仅是一种开启而已。所以,要走的路还长。作者引海德格尔在《出自思想的体验》中的一首诗言:“朝向一颗星星,只此而已。
/思想就意味着收敛到一个所思;/就像一颗星星,这思想保持在世界的天空。”(第437页)诚如此诗所言,文化之比较,亦须如此。现代世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乃是一无所有,无所不有。
正如此,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最后,还有几处文字上的错误需要说明。第十一章第一节,“古希腊人发现由系辞‘是’引发的‘是本身’或‘存在本身’……”(第237页)云云,“系辞”之“辞”大概是错字,如果是“是”那当然是一个“系词”。
第十五章注释七,“第24品”云云言亦误,查《妙法莲华经》,作者所引“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盖《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句,而《普门品》当《妙法莲华经》之第二十五品,而非二十四品(第368页,另参《大正藏》第9卷,第57页)。
大略如此,而不及详。其余则读者读此书自然可见耳。 如默。
2010年12月10日 附:张祥龙教授回信 如默先生: 已阅惠寄来的文章。
其中多次提及海氏的“形式显示”,这正是理解其基本方法--思想方式、治学方式和表达方式--的要害。
我在另一书《海德格尔传》和即将重印的《现象学导论七讲》(人大出版社,估计明年前半年发行,旧名《面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中,更多地讨论了它。另外,最近一次给学生们的讲座中涉及的“热思”,也与此有关。
寄上学生们整理的讲座稿,供参考。因还未发表,暂不用外传。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两处意见!其中“系词”的错误,已经在新版(人大版)纠正;另一处,我手上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四卷第一册,楼宇烈编,中华书局1992年)所载《妙法莲华经》确是在第二十四普门品(见该书346页)。
估计您手上的本子与这一文本不同,看来品目序数有时会不一致。 祝好! 张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