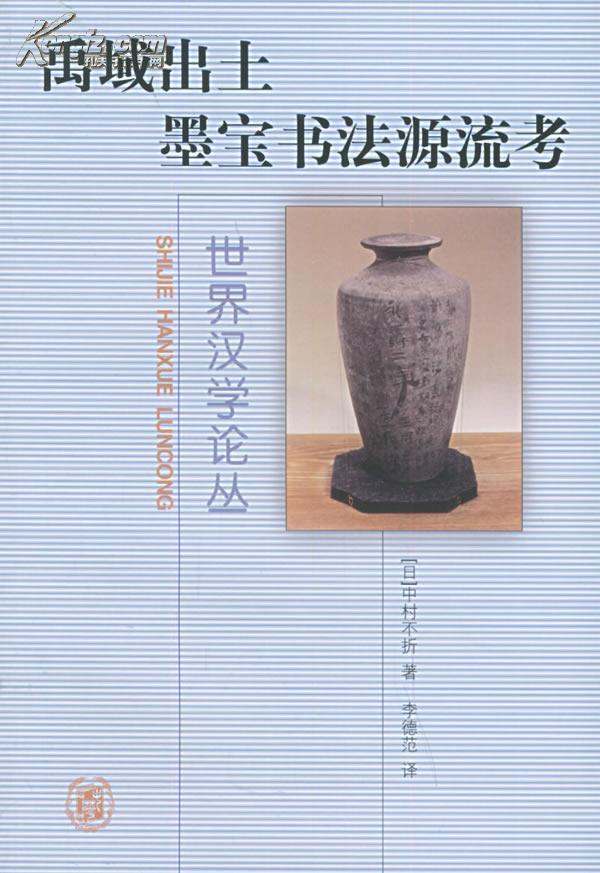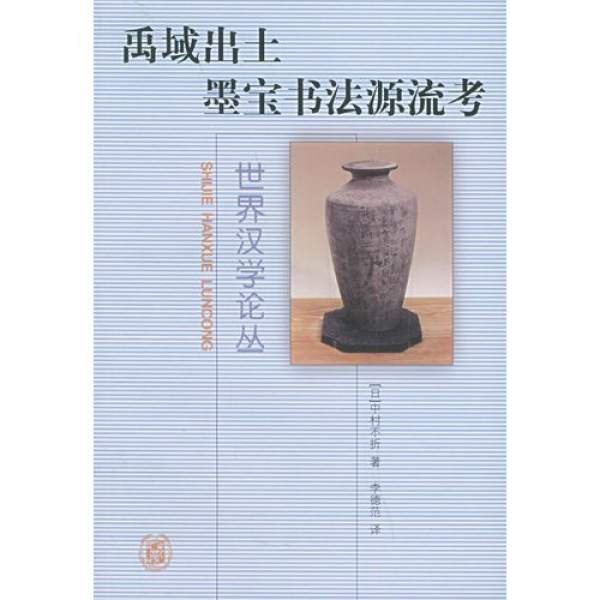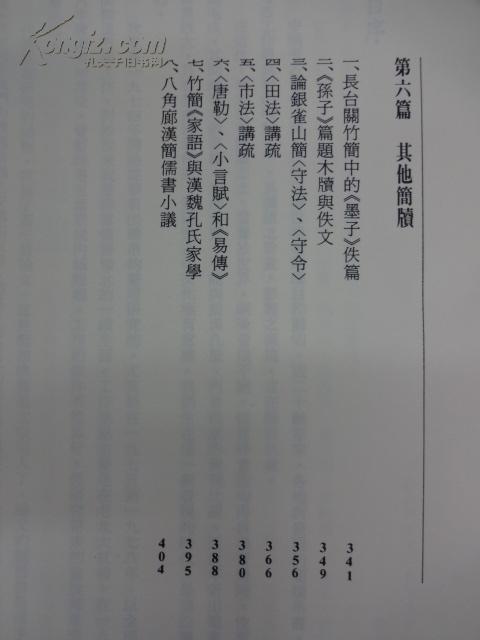李学勤赵国 赵平安:国际汉学中的出土文献研究
我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和传世文献相对而言的,主要是指经发掘出土的先秦秦汉文字材料,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简帛等。在国际汉学研究史中,出土文献的研究是起步比较晚的。虽然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1900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第一次发掘了古代简牍,不过考虑到1898年中国学者王懿荣已经发现了甲骨文,而对斯坦因发现的古代简牍展开真正研究的是罗振玉和王国维,因此说近代国际汉学中出土文献的研究是在中西互动下展开的,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与中国境内的出土文献研究相伴随,并且长期互动发展,是西方中国出土文献研究的突出特征。芝加哥大学的汉学研究很能说明这一点。1932年,美国学者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来到中国向王襄学习古文字,同时参观正在进行的小屯发掘工作,不久出版了名著《中国的诞辰》(The Birth of China)。
1936年,顾立雅回到芝加哥大学担任中国古代史教授。40年代,陈梦家和董作宾先后到芝加哥大学访问讲学。
钱存训也来到这里,担任东亚图书馆馆长,同时跟随顾立雅攻读博士学位,完成学位论文《书于简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从1930年代起,历经10余年的建设,芝加哥大学成为了西方汉学特别是中国出土文献研究的重镇。
国际汉学中出土文献研究的这个特点,是由出土文献的性质决定的。中国的出土文献,出土在中国境内,一般由境内披露,加之用古文字书写,释读难度大,西方学者要进行研究,通常必须借助一个可靠的、便于利用的文本。可以说,西方学者在原始资料和研究基础上具有前提性的依赖。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的中国出土文献研究,在研究的范围和研究规模上,长期难以取得大的突破。
1970年代以后,由于新的甲骨文、金文和玉石文字资料的出土、刊布,特别是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1972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代简牍帛书(1973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1975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1977年)的出土,不仅在国内引起了研究的热潮,在国外也引起了高度关注。
从70年代到90年代,西方汉学界围绕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以及秦汉简帛中的道家文献、法律文献、行政文书、日书的研究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湖北荆门包山简、郭店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陆续问世,学术界迎来了所谓“简帛时代”。这些战国时期的竹简,除了少量的官、私文书外,多为先秦时代的经、史、子类古书,对研究古代的哲学思想、历史文化以及古文献、古文字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学术价值,激发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
在新材料的催生下,西方的出土文献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织。
日本在1995年成立了中国出土资料研究会,会员有200多位。欧洲在2000年成立了欧洲写本协会(EASCM),有50多位会员。这些学会的诞生,因应了研究个体的需求,是出土文献研究队伍集约化的表现。
另一个标志是出版了具有教材性质的权威著作。这类著作日本韩国都有,而最有名的是美国学者夏含夷教授联合欧美几位学者编撰,于199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新史料:阅读铭文与写本的指南》(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
这本书分八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出土文献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为学习者进入这一领域提供了便捷的门径。该书中文版今年已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李学勤先生定名为《中国古文字学导论》。据悉,普林斯顿大学的德裔学者柯马丁(Martin Kern)目前正在跟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毕鹗(Wolfgang Behr)和牛津大学的麦笛(Dirk Meyer)一起编辑一本类似的出土文献工具书,书名翻成中文是《早期中国手写文献:文本、背景及方法论》(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Texts,Contexts,Methods),这本书以简帛为主要研究对象,撰稿人基本上是欧洲学者。
由于侧重点不同,加之欧美学者在学术文化、学科历史、语言及使用这些语言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以及处理研究对象的方式之间存在差别,因而这本书肯定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很值得大家期待。
国际汉学中出土文献的研究,首先是把文物上的古汉语文献翻译成外文,实现语言之间的转换,然后才是从哲学、历史学、语文学、语言学等角度展开专门研究。文字厘定、文本整理是翻译和研究的基础,除汉字文化圈的学者外,以往主要依赖中国学者。
现在的状况已经有了一些改观,年轻学者像美国郡礼大学的顾史考(Scott Cook)和堪萨斯大学的魏克彬(Crispin Williams)、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麦里筱(Chrystelle Maréchal)等在古文字方面有较深的修养,文字研究的成果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普林斯顿大学的柯马丁(Martin Kern)、海德堡大学的纪安诺(Enno Giele)和科罗拉多大学的李孟涛(Matthias Richter)等十分重视对出土文献文本本身的整理研究,如文本的书写和结构、口头传播的影响等,这在过去也是很罕见的。
这些直面本体基础的研究表明,在哲学思想、历史文化等传统领域取得进展的同时,国际汉学中出土文献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向,也标志着国际汉学中出土文献研究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夯实和拓宽了深层对话的基础。
中西方学者的对话从未像现在这么紧密,也从未像现在这样不断地碰撞出耀眼的火花。1998年艾兰(Sarah Allan)在达慕思大学举办了“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其成果《〈老子〉国际研讨会纪要》(The Guodian Laozi: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Dartmouth College,May 1998)在西方中国研究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10、2011年,达慕思大学和清华大学合作,就清华简《保训》、《尹至》和《尹诰》召开了两次小型的研讨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今年达慕思大学又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了“清华简国际研讨会”,70多位中外学者齐聚汉诺威小城,共同研讨去年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在西方反响热烈。
目前,中西方有关中国新出土文献的整理合作已经展开。据我所知,魏克彬参加了温县盟书的整理工作,陶安(Arnd Helmut Hafner)参加了岳麓书院秦简的整理工作,达慕思大学的学者参与了清华简的整理工作。
可以预期,在中外学者密切合作和共同努力下,出土文献研究一定能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作者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