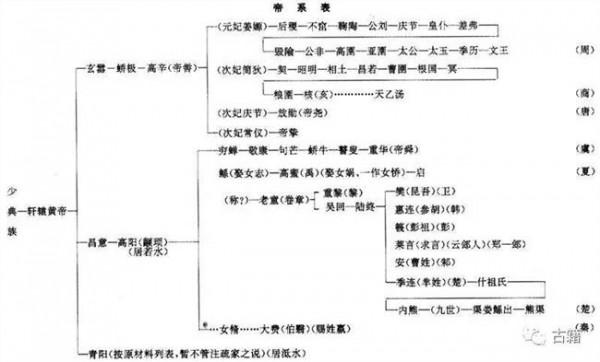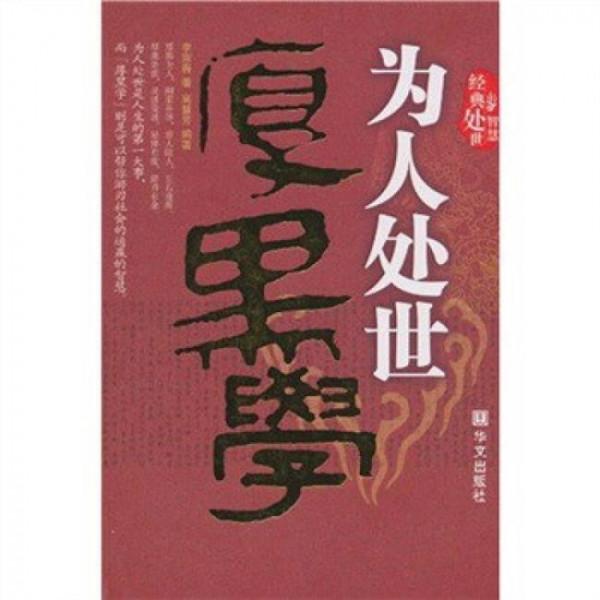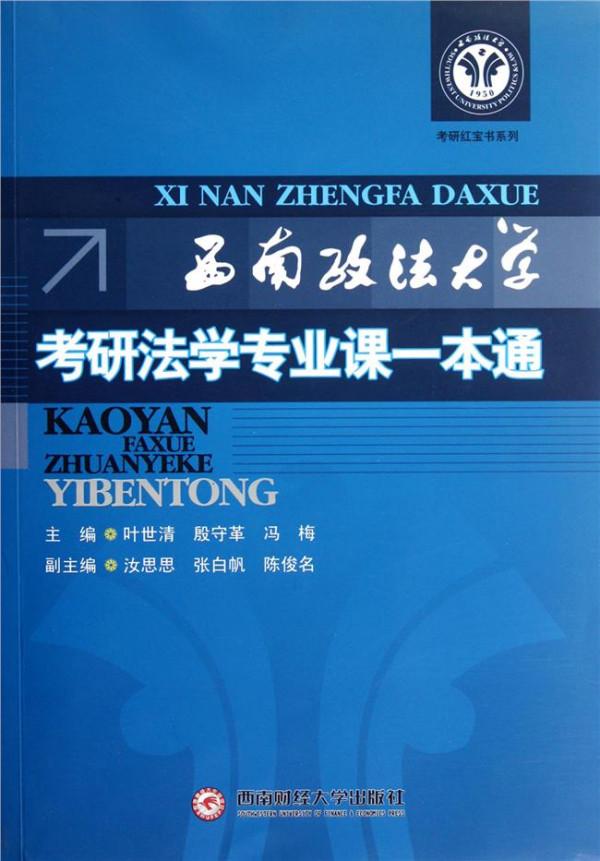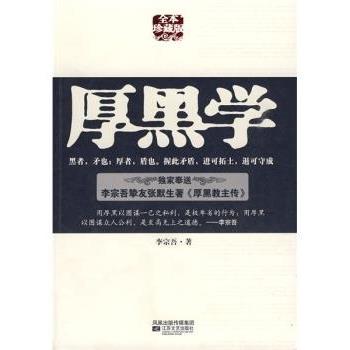李学勤考古学家 考古学家李学勤:不能说黄帝就不存在
李学勤是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文献学家于一身的“十项全能”学者,不过李学勤对自己的定位却只有一个: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者。近日,李学勤出现在“新郑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李学勤依然坚持多年前“走出疑古时代”的看法:黄帝是传说,传说口耳相传,并不能说明是不存在的。
■人物访谈
祭祖是对祖先的一种追忆
新京报:此次您被邀请去新郑参加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但事实上,世代相传的黄帝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考古证明,包括新郑这个地方真的就是黄帝故里吗?
李学勤:在传说里是这样的,新郑是有熊氏之地。传说中记载现在的新郑是黄帝故里。直到现在,新郑还有很多遗迹。
有关炎黄二帝确实是传说。不但是我们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希腊也是一样。它的历史最开始的阶段都是传说。因为那个时代人的记忆都是这样,是历代人口耳相传,但你不能说是不存在的东西。传说时代是古史的一个部分,当然这个部分与有文字记载的部分不同。司马迁就这样,有文献,也会在调查中加入传说。黄帝究竟长什么样,长得多高,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黄帝是代表那个时代的。
新京报:那对于传说中的人物,现在各地都频繁地开始了祭祖活动,你是怎么看的?
李学勤:事实上,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祭祖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古史传说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当时还没有文字,只能根据传说。祭祖是对我们祖先的一种追忆,在漫长时代里对我们民族起了凝聚作用。
新京报:我们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现在不仅是掀起祭祖的追根溯源潮流,也在各地掀起造龙工程,类似前段时间的“祖龙工程”,对此你怎么看?
李学勤:中国龙形象是自古以来的民族象征,它与西方世界的“dragon”还不太一样。至于各地掀起的造龙工程,不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不好发评论。
求学时代
“我学甲骨文没有师承”
“在我看来,甲骨文就同逻辑符号一样,是我不认识的符号,神秘难懂,令我着迷。”
直到现在,李学勤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研究生涯,最令其骄傲的还是甲骨文研究。事实上,甲骨文研究也是李学勤的起家之作。而迷上甲骨文的,竟然是由于年轻时,越是看不懂越喜欢的喜好。
小时候七八岁起,李学勤就迷上看《科学画报》。直到现在,李学勤家中还是每月有《科学画报》的出现,“我对自然科学的很多知识都是从那上面来的,那时很多科学知识我都不懂,但就是喜欢看。”就是这种越看不懂越喜欢的喜好,令李学勤在读到金岳霖先生写的《逻辑》后,就对数理逻辑也非常痴迷。
在读清华大学时,李学勤违背了父母当医生的愿望,选择金岳霖所在的系———哲学系,“我父亲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有个很著名的大夫叫关颂韬,他是世界上第七个能开颅的医生。我家里人很希望我也做像关颂韬这样的人,可我不喜欢。”
不过,就是对数理逻辑痴迷的同时,李学勤也对甲骨文产生了兴趣。李学勤自言自己一直就有对符号的迷恋,各种类型的符号,越是看不懂,越喜欢去看。“在我看来甲骨文就同逻辑符号一样,是我不认识的符号,神秘难懂,令我着迷。”为此,李学勤常常骑自行车到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去学习甲骨文,“人们常说学甲骨文要师承,但我是自学的。
学术开端
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结缘
分期也是断代,这几乎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点。在这项研究中,找出每个年代的具体坐标成为成败的关键。
对于甲骨文的研究,李学勤认为自己注重的恰恰是分期。巧的是,此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与分期有关。
解放后中国科学院内部出售《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的上辑和中辑,下辑还没有印。当时李学勤听说了这个事,就买了一部《乙编》的上辑和中辑。李学勤至今还记得当时是人民币5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50元。作为学生的李学勤开始了甲骨文研究的业余生涯。很快,师生之间就知道了还有个人在研究甲骨文。
买到《殷墟文字乙编》的李学勤,也开始做起了书中甲骨文的整理工作,“因为很容易看到书中有很多东西没有拼缀。”不过,在李学勤的回忆里,当初他对甲骨文的拼缀是有目的的,那就是为了研究文武丁卜辞,为了研究甲骨文的分期。这事很快就在学校里为人熟知起来。“陈梦家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知道我也在研究甲骨文。”
1952年被调到考古所的李学勤开始与曾毅公一起工作,编著了《殷墟文字缀合》一书,“这也是我的第一部书。”说起自己研究甲骨文的特色,李学勤表示自己更注重的是历史分期,“甲骨分期是我研究时间最长的。”
在甲骨文的分期上,李学勤提出了两系说,提议将甲骨文分成两个系统,这便是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进而,在甲骨文研究上,李学勤还分出了非王系统,指出之前一部分讨论中的甲骨是非王卜辞,推动了甲骨文的研究。
“过去甲骨文研究的分期一直搞不清楚,到现在也还是有些问题,而我对青铜器的研究也是从分期上着手的,”李学勤自认之所以喜欢从分期上做文章,是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而分期也是断代,这几乎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点。在这项研究中,找出每个年代的具体坐标成为成败的关键。
走出疑古
“大禹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2002年,青铜器“遂公盨”出现,李学勤对它的铭文进行了解读,从而推断出大禹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
李学勤是“走出疑古时代”的代表人物。此次,出现在新郑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的李学勤依然延续了他那“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李学勤承认,从现代的古代史和考古学的角度,如何去看待我国世代相传的炎黄二帝事迹,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课题。“不仅中国如此,古希腊、古代埃及也一样,文明刚开始阶段都是传说,”李学勤指出《荷马史诗》中神的故事比人还多,但我们对这样的传说不能忽略不计,不予研究。
目前,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又有中华文明起源工程。尽管这一新的工程李学勤参与的并不多,但是他相信随着考古探索发现的增多,一段关于4000年之前的历史记忆终将逐渐澄清。事实上,在追忆中国古代文明的记忆中,李学勤已经为我们找到了大禹的痕迹。
一直以来,考古学家指出几千年来妇孺皆知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只是传说,并没有真实的依据。尽管古书《尧典》等篇里有“禹”的内容,但这些材料在疑古派学者看来是不足信的。李学勤一直在提倡走出疑古时代。2002年,青铜器“遂公盨”出现,李学勤对它的铭文进行了解读,从而推断出大禹这个人物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2002年,一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出现在公众视线。这是西周时期在祭祀典礼上用来盛放食物的器具。李学勤见到遂公盨时,土锈上有明显席痕,且包到口边上,“这意味着遂公盨在地下时已经与盖分离了。”
李学勤被遂公盨上的铭文吸引住了。其上的铭文在盨的内底,共有10行,98字。前9行都是每行10字,末一行只有8字。李学勤考证遂公盨的作者是遂国的国君,是舜的后代,他做遂公盨是要把祖先的“德行”进行传述。
一次次从考古实证中打捞出曾经的记忆,让李学勤坚信中华文明最起源的记忆被转述为传说流传了下来,尽管现在没有文字记载可以说明真人、真事,但是通过不断的考古挖掘也许能渐渐揭开历史的真相。
从事副业
建立第一家汉学研究所
清华大学的国际汉学研究所成立,没有人员,没有经费,没有编制,“当时学术界根本就不理解,认为汉学有殖民主义的味道。
甲骨文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都是李学勤的正业,除此,精力旺盛的李学勤也早在上世纪90年代操持起了副业。那一次的副业,让仅在清华读过一年书的李学勤,又与清华大学发生了亲密联系。那就是在清华大学成立国际汉学研究所。
李学勤心中的中国古代文明是非常古老的文明,同古埃及、古希腊一样。但是对于国外的古代文明都有对应的学术,类似埃及学,亚诉学进行古典研究,研究中国古代的却没有专门的名词对应。李学勤受到打击的还是在于日本人“领先”一步的举动。
日本学者石田干支助,是最早研究汉学史的人。上世纪70年代末,李学勤受到美国交流文化总署邀请去访问美国。这时便需要定一个访问计划,但李学勤一点都不了解美国的汉学研究情况,国内也没有任何人研究。出乎意料的是,李学勤找到了一本日本书,原来日本人早在50年代就开始对世界各地国际汉学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研究。
就是通过这本书,李学勤知道了美国各个大学有哪些汉学系,有哪些汉学家,“我非常震惊,汉学最先研究的竟不是中国人。”
上世纪80年代,清华又想恢复文科,邀请李学勤。不过身处社科院的李学勤回不到清华,于是便在1992年开始建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这可以说是全国最早的机构,”李学勤指出,在早一年,西南外国语学院的张良春建立了一个国外中国学研究所,并出了一本书《国外中国学研究》,是季羡林写的序,不过写了这本书后,这个研究所就找不到了。
清华大学的国际汉学研究所成立了,被戏称为“三无研究所”,没有人员,没有经费,没有编制,“当时学术界根本就不理解,认为汉学有殖民主义的味道,跟现在热闹巨变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