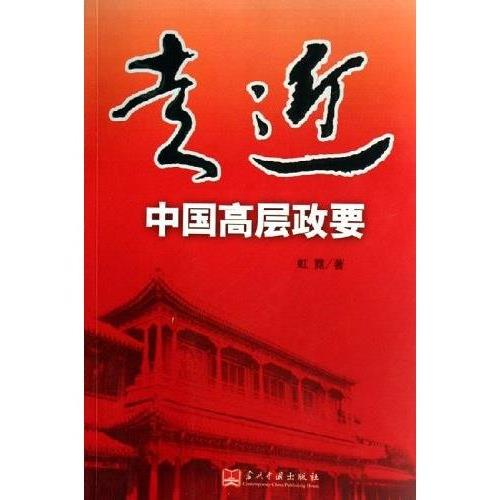钱伟长咋也成了“大右派”?
【提示】邓公在“右派”改正的问题上曾发自肺腑地说:“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这是说到节骨眼儿上的。国宝级科学泰斗钱伟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是最典型例证之一。
我们都知道“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他们是中国当之无愧科学泰斗,为中国科学和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彪炳史册。
然而,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这一“钱”与其他二钱不同,1946年即拒绝美国发给的签证而学成归国的钱伟长,在1957年***发动的“反右”运动中竟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派”!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顶“右派”帽竟压在他头上25年!我们都知道,大约从“反右”后第三年开始,一部分“罪行较轻”的“右派”经群众讨论、上级批准,陆陆续续被摘帽,成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但恢复原岗位工作和待遇的极少,政治面貌依然叫“摘帽右派”),而钱伟长的“右派”帽子却一直牢牢地死扣在他头上,直到粉碎***以后的以后——1983年才拿到那张“右派‘改正’通知”。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先看看钱伟长教授为何被打成“右派”的吧——
一、百分百因言获罪——而绝不是什么“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别说“反右”,还早在“整风”开始之前的1957年1月,钱伟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的文章,主张教授治校、理工合校、培养通才。历史记载,在1957年4月30日,***还在民主党派领导座谈会上说过:大学里可以考虑教授治校,这恐怕有道理。可以研究一下。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但在当时,钱伟长万没想到说点儿常识也会犯“大错误”!
距钱伟长那篇文章发表三个月后,“整风”开始了,毛及中央号召“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而“整风”的第一条就是帮助党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钱伟长在《人民日报》发又表了《语重心长谈矛盾》一文,但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是老清华了,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这成了典型的“右派”言论。
当然,按当时的逻辑钱伟长此话自然了不得:中共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高唱中共和毛是“大救星”还来不及呢,钱伟长竟然敢说“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这岂不是大逆不道?
前一篇文章,钱伟长对苏联教育模式和办学方法以及理工合校的观点提出异议,这在当时中共号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完全效仿苏联)的背景下,似乎无疑间接违反“中苏友好”政策了——须知,当年“反对中苏友好”是一种罪名,对某些人来说是可以判刑入狱的。而后一篇,则是他作为民盟一员响应“整风”号召与同仁一道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的心里话,却变成了反党言论,成为被划“右派反党分子”的确凿证据。
钱伟长的那些话若在当下,应毫无问题,比这更尖锐的批评党和政府政策的言论多了去了,但在那时却是犯忌的。可记得***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呀?而且在具体“指示”中明确说:“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怎么后来……?
二、钱伟长的“右派”帽子被牢牢扣稳了
随着“整风”在半个月后突然转为“反右”,钱伟长立刻遭到批判和攻击,这其中既有响应毛和中央号召的一般教职工,也包括他的两个老同事——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和时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的钱学森,他们响应“反右”号召,表现出坚定的“革命立场”,并且在《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批判钱伟长的文章,其措辞之尖刻之犀利,非比寻常,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实事求是”了——当然,被打成“右派”的厄运自然也不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了,这叫做“响应号召,划清界限”。
1959年,钱学森入党了。
1958年1月15日,钱伟长在清华大学被正式宣布为“右派分子”,并定为右派中的“极右分子”(这是最严重的等级),撤销一切职务,接受批判。那年钱伟长45岁,正是生命日当正午的盛年,他却被一度剥夺了讲课和从事科学研究以及发表文章的权利。就连已经排好版的他的专著《应用数学》也被封杀。好在他的另一本书《弹性力学》赶在“反右”的前一年已经出版,否则……
1957年反右,是无法治可言的。“群众”与上级党委的话就是“法”,而“群众”又是必须“听党话跟党走”的,否则也是非“右派”莫属。定某人为“中右”还是“极右”,是开除公职还是逮捕判刑,是劳教还是留原单位监督劳动,为期几年等,皆无明确可操作裁量标准,除逮捕的外,其它皆无须司法审判程序……
让不让某人当“右派”,领袖一句话可定夺。毛保荣毅仁等过“反右”关,却不保钱伟长,这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发人深省的。
荣毅仁可谓大资本家,“鸣放”中也有颇为“极端”的言论,甚至还有定期聚会的“小团体”,已遭大字报揭批。但毛明白地对统战部长说,荣毅仁他们“不划为右派,但回去要好好检查”。荣千恩万谢,痛骂自己,过此一关。毛也放话保过其它几位科学家和相关人士,而对钱伟长这样国宝级科学家,毛却并未放其一马,但说了一句“钱伟长还可以当教授嘛”——一句话,荣毅仁等过关了,一句话,也使钱伟长虽为“极右派”却免于像丁玲那样去北大荒流放劳动改造。
可流放幸免了,但一级教授降为三级,工资大幅下降,这是不给例外的;儿子也受牵连,考上大学照样“不予录取”。这也是当年“右派”子弟十之八九的下场。
和许多受到冲击与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于钱伟长来说,1966年开始的“***”噩梦要比“反右”更恐怖。1968年,他头顶“右派”帽子又加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再次挨整挨斗,还被强制送到首都钢铁厂劳动改造。56岁的国宝级科学家成为一名炉前工,不仅力不能支,且内心极端苦闷。他在事后谈起这段往事时说:“这分明是拿好马当驴使啊。”
***中,中国有与兄弟国家的科学教育交流往来的需要,这为***保护一些“国宝级”人才带来了机遇。反右毕竟过去10多年了,凭总理一张条子,多年“沉默”的钱伟长从1970年开始可以接待一些来华访问的外宾了,也凭此需要,家庭起居条件得到相应改善,日常生活不再过份寒酸、局促——否则何以面对外宾?在周总理的特殊关照下,钱伟长戴着“右派”帽子,还曾在***安排的出访计划中作为科学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国访问过几次。
但有人提出:他是“右派”,会不会跑出去不回来?
钱伟长说:笑话,“当我是壮年之时,我舍弃了美国的优越物质生活而回到祖国,为的是要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生我育我的祖国母亲,奉献给我的亿万同胞。这才是我最大的愿望。”(当年在美国时,钱伟长是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的工程师)他还请记者代为传递一个信息:“转告关心我的读者们,我的岗位就是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这就是“右派”钱伟长!是的,1946年钱伟长回国后,在清华,一般教授一星期上6堂课,他却上17堂课,没有一点儿怨言。
钱伟长爱国之心固然尽人皆知。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周总理的保护和安排继续发挥着“统战”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之“统一战线”,曾是中共制胜三大法宝之一,而这一“法宝”在1957年“反右”和“***”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无情践踏。我们无法不承认,这使中共“凝聚力”大***扣。
钱伟长虽有限制地在外事活动中露脸,但“远香近臭”——回到国内,回到清华,他还是准“右派”,并无任何光鲜。学识渊博的科学家、教育家随时与扫帚、墩布、抹布为伍,整日与灰尘和油渍搏斗。看书钻研学问,那只能挤休息时间了。
三、“极左”路线余毒,使“右派”帽子在他头上又多戴了3年!
粉碎***三年以后的1979年夏天,党中央以文件形式公布55名党外著名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一律予以改正(包括反右运动中被错划的著名“六教授”另5名: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并恢复名誉。可此时,许多宝贵人才已经在漫长的折磨中含冤死去,钱伟长是这55人中“还活着的 7人之一”。
但钱伟长在他的《八十自述》中这样写道。“但在清华大学,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受到阻挠达3年之久。迟至1983年 1月12日,在中央决定把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担任校长一个月后,才勉强给了我一张“右派‘改正’通知书”——当看到如今还有人(甚至所谓“学者”)还在为当年的“反右”乃至“扩大化”百般背书、招魂时,我们对此应当是完全可以理解了。
邓公虽然当年也曾挺“左”,但他毕竟是清醒的,他在“右派”改正的问题上曾发自肺腑地说:“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这是说到节骨眼儿上的。即如钱伟长,如果不是被打成“右派”,“好马当成驴使”,他能为祖国做出多少更大的贡献啊!可是在1957到1976年间,钱伟长无权发表任何学术论文!这难道不是国家无法估量的损失?!
历史证明,毛是“反右”这场大战的策划者、指挥者、督阵者,邓公作为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无疑还是在毛领导下工作,岂能有丝毫走样?但邓还是不无内疚地自我批评说道:“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呀!
”不论邓还是毛,“扩大化”是自上而下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种认为“扩大化”不是毛的本意的人,请重新按时间顺序读一读1957年5月以后毛亲手撰写的一系列社论、党内指示吧。对一场反错了99% 以上的“反右”,面对钱伟长一类“右派”案例,还要坚持说它的“必要性、正确性”,有意思吗?
四、被打成“右派,几乎是所有“钱伟长们”的宿命
中科院著名院士郑哲敏说:钱伟长在那个年代虽然和一些人意见不合,但他“公开讲他的想法,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人”。的确,不论从整风中钱伟长的直言,还是关于两弹一星的决策态度,钱伟长就是这样一个敢想而直言不讳的人。
周总理对钱伟长的了解,其实正缘于1956年国家科学规划会议上的争吵。当时,钱伟长着眼于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提出5项国家科学优先发展重点:一是原子弹,二是导弹,三是航天,四是自动化,五是计算机。没想到,与会的学界元老们有400人不同意。
1比400,钱伟长很孤立。只有两个人支持他,一个是钱三强,另一个是钱学森,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最后,周总理拍板:“‘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三钱”的特有称谓,就是这么来的。
此后,钱伟长与钱学森等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等职。这些历史细节,在当今的一些影视作品中已极少被提及。(以上史实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8月25日第7版相关报道)
早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修时,钱伟长与钱学森、郭永怀等同窗相聚一起,常常畅谈国事、憧憬未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回去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有如此报国情怀怎会因惮于人情世故而讲话畏首畏尾?而正因对人对事直言不讳,使钱伟长在“反右”中终于在劫难逃!“右派”成为大大小小“钱伟长们”的宿命,使得他们自己和国家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五、反思:“这不但是他们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
***说:反右“带来一个缺点,就是大家不敢讲话了”(见应克服:《反右斗争的历时后果》)。毛在这里是实话实说了。
“反右”的后果,不是如某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大家“更加一致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而恰恰相反,党的“统一战线”制胜法宝受到极大践踏,许多人对执政党只有无可奈何地敬而远之,举国上下一片“赞歌”的背后却是噤若寒蝉,万马齐喑。
***本人也隐隐感到了这样的非正常状态。毛说“大家不敢讲话了”,此言毫不夸张。以“反右”为鉴,人们明哲保身,或保持沉默,或说假话,说违心话。如此“团结”而已。于是便有了后面的“***”和“反右倾鼓干劲”的浮夸风。
有人总拿当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国际形势等“历史背景”说事儿,以此论证当年“反右”确有必要。其实我们无须举出不胜枚举的“钱伟长们”的案例,即便上世纪90年代苏东巨变、柏林墙轰然推倒,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1966年就说“世界上一百多个党大多不信马列”了,如此“背景”之“险恶”难道不远超过1957年?如今批评党和政府的言论还要怎样直言不讳?中国搞了什么“政治运动”反这个那个了?中国发展受阻了吗?——当年得不偿失的反右给执政党和国家发展造成多大损失?“必要性”何在?还有人说,钱伟长后来也挺“左”——姑且不论事实如何,即便如此,这不也恰恰证明他当年被打成“右派”正是执政党的大错?
如此爱国的“国宝级”知识分子钱伟长1957年尚且在劫难逃,全国爱国知识分子遭到怎样的整肃和打击,可想而知。邓公说到了节骨眼儿上:“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1956年以后,我们搞了20年的‘左’”。“综观我们党70年的历史,突出的,都是‘左’……‘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啊!” (1992南巡讲话)
邓公是既反“左”又反“右”的,但他明确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不能说不是历史的经验总结。前车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