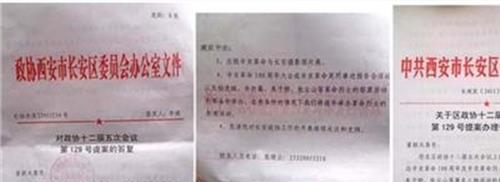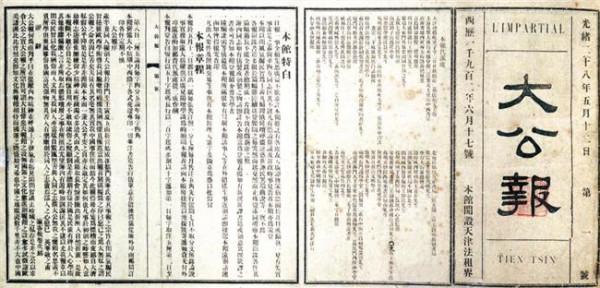张季鸾的政论特色
张季鸾,原籍陕西榆林,出生地山东邹平。榆林地处陕北,风俗尚武,张氏先世亦皆为武官。张季鸾的父亲张楚林,字翘轩,少时弃武从文,在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兆槐的栽培下,考取进士,成为榆林近百年历史上的破天荒。张楚林为感刘厚基和蔡兆槐的恩德,曾在家中设立两人牌位,令子孙后代祭祀。
这种报恩思想对张季鸾的影响很深。张楚林虽中进士,但仕运不济,在山东做了几年知县,1901年病死济南时,家中一贫如洗。张楚林死时,张季鸾年仅13岁。
其母王氏领着张季鸾兄妹三人扶柩归葬。王氏是一位善良而坚强的女性,一人承担艰难家计,令张季鸾早出游学。由于操劳过度,1904年便告别了人世,时年37岁。张季鸾年幼懂事,聪颖过人,延榆绥道陈兆璜爱其才,怜其贫,召入道署,令与子共读。1902年,又出资送至咸阳醴泉“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老先生,打下深厚的文史根基。
幼年时的生活经历,对张季鸾思想的影响很大。1934年9月,为纪念其父张楚林冥诞一百年,其母王氏忌辰三十年,张季鸾曾专程从天津回榆林扫墓、立碑。在《归乡记》一文中,张季鸾在叙述了上述经历后说:“我的家世,大概如此??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
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我的思想,是赞成维持中国的家族主义,但是要把它扩大起来??从报答亲恩,扩大为报答共同的民族祖先之恩。”(张季鸾《归乡记》,《国闻周报》,第20卷第1期,1935年1月1日)
张季鸾的这种报恩思想在以后的办报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以文章报国。
如果说幼时的经历和所受到的教育打下他爱国忧民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真正促使他走上“文章报国”道路的是辛亥革命的大潮。少年张季鸾留学日本,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经济理论,亲眼看到了日本的社会现实,打开了他的视野,开阔了他的眼界。
此时,又适逢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利用报刊进行论战,张季鸾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论战,但从中受到了教育,接受了革命派的理论和主张。在日本,张季鸾参与编辑革命派的刊物《夏声》而开始其报人生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11年,学成回国,立即投身报刊活动,与报刊结缘一辈子。
“报恩主义”与“文章报国”是张季鸾为人与为文的思想主线,也是他一生的执着追求。
二、张季鸾的政论写作
从1911年张季鸾应于右任之邀,赴上海担任《民立报》编辑起,至1941年在主持《大公报》言论15年后病逝,30年间共撰写文章不下3000篇,其中绝大多数为社评。《大公报》在当时之所以成为“舆论重镇”,与张季鸾及其社评的作用及影响直接相关。
张季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及社论主笔的15年,中国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先后爆发了四.一二事变、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
作为一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张季鸾在秉持中国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传承的同时,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并将这一传统提高到一个新的地位。胡政之在1944年出版的《季鸾文存》的序中提到;“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
”作为一名报人,张季鸾以“新闻救国”、“言论报国”为理想,凭借手中的笔,以报刊社论为载体,针砭时弊,议论国是,坦陈时政,分析变局,其言论不仅奠定和提高了《大公报》的社会地位,也每每对当局或时局产生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1、张季鸾社评的写作原则
社论通常被称作报纸的灵魂,《大公报》是一张新闻纸,但由于其重视言论,特别是由于张季鸾主持的社评的鲜明特色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使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该报是一份政论性报纸。
《大公报》奉行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不仅是该报的办报宗旨和发行宗旨,也是张季鸾写作社评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一指导原则在实行中具体表现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言论信条。
作为一张独立的民间报纸的社论主笔,张季鸾言论的“四不”原则首先表现为“立言为公”,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1931年5月22日);其次,表现为言论独立,即“不以言论做交易”,不为政党所用,不为权势所迫,也“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其三,表现为持论公正,即不随声附和,不一知半解,不感情用事;而是态度严谨,分析客观,判断公正。
2、 张季鸾社评的选题范围及政治态度
虽然自1926年11月7日起,《大公报》社评取消了署名制,“若干重要文章且多系大家商讨后由一人执笔”(胡政之:《季鸾文存.序》,大公报馆1944年4月出版)。但在张季鸾担任总编辑的15年间,《大公报》绝大多数社评出自他手。
由于兼具文人的深厚学养与报人的职业敏感,他的社评往往目光敏锐、视野开阔。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局的变动,其社评的选题范围和关注重点也不断拓展或转移:从百姓疾苦,到政府腐败;从时局变化,到前方战事;从国内事变,到国际形势……凡属值得评价、需要议论之事,几乎均有涉及。
张季鸾社评的选题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揭露社会黑暗,抨击腐败政治
作为一名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报刊政论家,张季鸾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十分鲜明。其批评矛头所向,往往直指当权者,揭露其反动、虚伪的真面目。在他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兼社评主笔的初期,曾发表了3篇斥责权贵、胆识过人的社评,即著名的“三骂”:一为《跌霸》(1926年12月4日),对曾“独霸一时”而今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之所以有今天的结局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该文也成为吴氏及直系军阀的送终之作。
二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1927年11月4日),对忽而“联共”、忽而“清共”、“分共”的汪精卫之反复无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十余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原因,是“领袖欲与支配欲为之祟耳”。
三为《蒋介石之人生观》(1927年12月2日),专门就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发表的声明进行了深刻而辛辣的讽刺和批判,不仅揭露了蒋介石的虚伪,还将蒋宋联姻放在大批兵士殉生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对照,表现出其社评鲜明的立场和强烈的爱憎。
张季鸾出身寒微,多年形成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表现在其社评的选题上,是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关注,对吏治腐败的深恶痛绝。前一类的代表性社评《中国的文明在哪里》(1930年11月2日),是《大公报》派遣记者到河北农村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后配发的,作者在文中对多重剥削之下生活悲惨的民众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对中国农村及农民现状表现出深切的忧虑。
后一类的社评有《论建成廉洁有能之政府》(1930年11月14日)、《官吏不得经商投机》(1930年11月23日)、《刷新地方行政之亟务》(1930年11月28日)、《人民与政府》(1930年12月30日)等。
其中,在《人民与政府》一文中,开篇即指出:“近代中国人民最普遍之政治观,为骂政府,若曰人民一切不幸,皆政府之不良致之。苟有良政府,则国家地位,人民境遇,必不如此。”揭示出当时国势衰微、民怨四起的根本原因。
(2)揭露日本野心,宣传抗日救国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在其主持《大公报》笔政的15年间,先有“九.一八”事变,后有“七.七”卢沟桥事变,他目睹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变为侵略行为的过程,直至他去世之时,抗日战争仍处于僵持阶段。
因此,在张季鸾大量的时事型社评中,有关日本问题、中日关系和抗日战事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台湾学者陈纪滢曾说:“季鸾先生洞察时事,眼光之敏锐与远大,就中日关系来说,先知先觉,是最权威之政论家。”(陈纪滢:《报人张季鸾》第17页,台湾重光出版社,1971年版。)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季鸾凭其对日本问题的关注与了解,已开始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野心。1931年7月12日,他发表《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文中忧虑地指出:“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国一切赖舶来;日本且叹‘不景气’,中日前途更是何等结果?此吾人所大感危惧者一也!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的著名社评《国家真到危重关头》(1931年11月22日),对“九.一八”后两个月间的国内、国际局势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醒政府和国民:“盖日阀行动,证明其志在灭中国,不止在并三省,其行动之范围,常以国际形势所许之最大限度为限度,而求以最小牺牲,得最大效果??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
此后张季鸾撰写的有关这方面内容的社评还有《愿日本国民反省》(1931年9月26日)、《望军政各方大觉悟》(1930年10月6日)、《马占山之教忠!》(1931年11月20日)、《救东三省避伪独立》(1931年12月10日)等,结合最新事态,从不同角度分析时局变化,警示提醒,告诫世人。
此后,张季鸾的社评重点放在宣传救亡图存,主张“明耻教战”和谴责“上层误国”上。“西安事变”中,他撰写的四篇社评,虽曾遭到疵议,但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季鸾的有关抗日救国社评所占的比重更大。如1937年“九.一八”6周年纪念日发表的一组社评《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1937年9月18日)、《感谢卫国军人》(1937年9月19日)、《勉全国公务员工》(1937年9月22日)、《勉出川抗战各部队》(1937年9月30日)等,既有对抗战历程的反思,更有对民心士气的鼓舞。
而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及其后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张季鸾撰写的社评无不体现出其强烈的爱国之情与坚定的抗战之志。
其中《最低调的和战论》(1937年12月8日)是对时局的准确分析,《置之死地而后生》(1937年12月11日)是对民心军心的大力呼唤,《为匹夫匹妇复仇》(1937年12月28日)则是对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对侵略者兽行的强烈声讨。
直至1941年9月去世前,对于战争局势的关注,对于政府和国人抗战精神的激励,一直是张季鸾社评的重要内容。
(3)“反苏”“反共”,“骂蒋”“拥蒋”,坚守“国家中心论”
张季鸾的“报恩主义”,使其将报亲恩与报国恩联系起来,这既使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又使他坚定地抱持“国家中心论”,对其有“知遇之恩”的蒋介石有骂有帮,先骂后帮。而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政治理想是建立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对于共产党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抱有相当的成见和天然的戒心。表现在其评论的内容上,则是有相当的篇目与“反苏”、“反共”及“骂蒋”、“拥蒋”有关。
其中,在《明耻》(1927年1月6日)一文中,作者指出:“中国有赤化问题之发生,中国之耻也。”表现出明显的反共倾向。即使在国共合作、共御外侮的抗日战争期间,在张季鸾的有关社评中仍可看到这种倾向。如1941年5月23日发表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中,虽然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等方面的努力,但对中共十年间对国家贡献的基本判断却是“负号的,不是正号的”。
在有关苏联的评论中,张季鸾既指出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又提出向苏联学习工业化、电气化的建设经验(见《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列宁逝世》等文),观点看似矛盾,其政治立场其实是一以贯之的。
这种政治立场的集中表现,就是对“国家中心论”的强力维护。无论是张季鸾早期在《蒋介石之人生观》中对蒋介石的“骂”,还是在有关“西安事变”中对蒋介石的“保”与“拥”,包括对于抗战爆发前夕对蒋介石政府“缓战”政策的支持,都是出于对国民党“正统”政府的承认与维护,对“国家中心论”的坚信与坚持。
(4)关注社会教育,开启民智民风
张季鸾“新闻救国”、“言论报国”思想的另一表现形式,就是他的社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关心青年,关怀妇女,关注教育,以此来开启民智,倡导新风。
《大公报》1931年4月12日刊登的社评《青年思想的出路》,是张季鸾有关青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面对危机的国势,纷乱的世事,渺茫的前途,文章首先对青年普遍存在烦闷与彷徨心理表示理解,指出:“为思想的出路而感觉烦闷之青年,为社会最有用之一部分。
人类之幸福,世界之进化,皆赖此辈求之。就中国论,亦只患青年无思想,并不患青年有烦闷。”在对青年的烦闷予以理解之后,文章更多的是为青年的发展提供中肯的建议:“其一,趋自然科学,加速度地学习西人所已能,更发明其所未能,求现代的利用厚生之技术,以救中国同胞之穷;其二,则趋社会科学,根据外国学者研究结果为基础,再思索之,讨论之,以求真理最后之归宿,决中国永久之针路。
”及至今日,这一建言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示性。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两个多月后,张季鸾在《中国青年》(1938年2月8日)一文提出:“救亡建国的艰难重任,无疑在全国青年肩上。因为青年能刻苦,有勇气,可以做困难工作,可以克服逆境。特别是青年的荣誉心、责任心、正义心,都旺盛,可以将拥护中国独立自由的大业担负起来。
”文中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青年,不仅指学校学生,也包括“广大的武装卫国的青年和有爱国心意识的一般青年民众”;不仅指男青年,也包括女性青年。呼吁他们在为同胞悲痛,为人类文明悲痛,为日本的堕落悲痛之余,“鼓励自己,坚决奋斗”。
刊载于“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日的社评《学生与政治》,不仅是应时之作,而且是应需之作。文章紧扣国难当头之际,青年学生如何处理学业与政治、学科与政治、人生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议论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特别是在议论只讲专业不讲政治的危害时,就理工、文哲和经济各科可能出现何种于国有害的后果逐一述之,既切中肯綮,又令人警醒。
其中,自然科学教育“如不适合人民利益的进行,则技术人才有时反演助纣为虐之角色。如造械徒以杀人民,飞行亦足奖内乱是也,即不然,徒增长少数人利益。
或甚而作国际资本之工具,以剥削其本国之财富,此技术万能之说不成立也。”此番议论看似危言耸听,实则振聋发聩,即使今日读来,亦极具预见性与启迪性。
(5)申明办报宗旨,倡导新闻自由
新闻媒介之社论,不仅可以代表媒介发表对新闻事件及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可以代表媒介传播其办报宗旨及职业追求。
作为总编辑兼社评主笔的张季鸾,在其职业生涯中,不仅深感新闻自由之可贵,亦感新闻自由之必需。在其撰写的社评中,多次表达出对国民党政府控制舆论、限制新闻自由的不满,并在文中直陈其危害。此类评论有《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与表示》(1929年12月26日),《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1936年4月2日)。
而发表于1939年5月5日的《抗战与报人》,则直接联系到日本侵华对新闻自由的毁灭,议论“任何私人事业,与国家命运不可分,报纸亦然。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更谈不到言论自由。”作者将“新闻自由观”置于“国家观”之下进行新的考察,体现出作为职业报人的张季鸾对既有的“新闻自由观”新的思考与诠释。
《大公报》的社评,也是该报办报理念、办报宗旨的载体。自1926年新记大公报续刊至1941年张季鸾病逝,《大公报》每遇重大变动或重要纪念日,常有社评发表。如《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1931年5月22日)发于《大公报》出刊10000期之日;《今后之大公报》(1936年4月1日)发于新记大公报续刊10周年之际;《本报在汉出版的声明》(1937年9月18日)发于该报在沪汉两地同时发行之日;《本报迁渝出版》(1938年10月17日)则发于该报自汉迁渝后公开出版之日。
这类由总编辑张季鸾亲笔撰写的社评,既表达了报馆对读者的尊重,更是媒介自身理念与追求的概括。
三、张季鸾的政论特色
张季鸾逝世后,周恩来同志在唁电中称其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介石则将其誉为“一代论宗”。亦有台湾学者认为“论文笔,论影响力,他超越了梁启超。”(李瞻:《张季鸾传》,国史拟传第九辑抽印本第142页,2000年12月初版。)
中国报刊政论自王韬始,经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发展传承,到张季鸾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张季鸾的社评已基本完成了从报刊政论向新闻评论的过渡,使这一历史悠久的文体,摆脱了“设言立说”和“坐而论道”,开始真正成为“对于新闻的评论”。除前文提到的选题范围的极大拓展外,在文体形式、论证方式及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张季鸾的社评都颇具特色。
1、增强时效性,追求新闻价值基础上的评论价值
新闻应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评论也应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评论。但就中国的政论传统而言,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之说。自王韬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以来,突破了“桐城时文”的局限,强调“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自序》)。梁启超在继承和发展了王韬的政论风格的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时务文体”,在纵论时事之中感情充沛,文气跌宕,气势磅礴。但囿于文体的束缚,特别是囿于新闻传播技术的落后和信息传播途径的局限,在新闻的时效性难于保证的时期,遑论言论的时效性。
在张季鸾接掌《大公报》社论主笔之时,中国的新闻事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媒介的增多,信息的发达,使新闻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大大提高。作为一个报人,张季鸾将社评的议论对象,更多地锁定于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在对由头或论据时间的表述上,也从“近日”、“日前”, 逐渐变为“前日”、“昨日”。
如1931年11月20日发表的《马占山之教忠!》,在开篇处介绍了新闻事实:“马占山将军与其所部诸将士,孤军守土,援绝弹尽,竟已于十八日撤退,昨夜日军占齐齐哈尔……”所依事实一为“前日 ”,一为“昨夜”,后者距报纸发排不过几个小时,其时效可见一斑。
在1937年12月11日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中,由头是援引“昨天路透电,暴日五大臣会议,已决定攻占南京后,继续进攻,不到中国‘表示诚意 ’不止。”而是日距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仅两天,足见所评事件之新鲜与重要。
张季鸾社评对新闻性的追求,不限于时效的把握,还注意时机的选择;不限于新闻价值的判断,还注重评论价值的判断。于《置之死地而后生》刊出的前三天,即1937年12月8日发表的名篇《最低调的和战论》,从两则“昨日东京电”中敏锐地捕捉到评论点——敌方消息的自相矛盾之处。
这两则消息分别是“敌外务省发言人说,欢迎第三者调解”,和“东京已准备八十万人的游行庆祝,预备于占领我首都之日举行”。由此文章做出对敌方“欢迎调解”的判断——“只是庆祝胜利后的纳降”,并据此展开分析和议论。
张季鸾何以保证《大公报》社评时效性的实现,重要的做法之一就是“看完大样写社评”。张季鸾在每晚9点审阅大样、小样和各类电讯,确定社评的依据。有时,在付印前传来值得评论的最新消息,他就更改社评内容,连夜赶写,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季鸾对于社评时效性的追求,是其职业追求的具体体现。
2、讲求预见性,洞悉时局与事态的本质及趋势
新闻评论是对新闻事实的一种判断,包括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因果判断、趋势判断等等。张季鸾的评论中,大量是对新近发生的新闻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但其作品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对一些重大新闻的因果判断和趋势判断;而其分析之独到,预测之准确,常常令人啧啧称奇。
以《中国之前途》(1936年11月30 日)为例,在抗日战争尚未爆发,“西安事变”即将上演之际,文章对中日关系走势做出了明确的的预测:虽然“时局紧张与重大”,但“前途光明有必然者”。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统一之凝固,自古以来,无如今日”;二是“在中国自力更生之过程中,国际大事如何,自亦与我有重大之影响,由此而论,亦与中国有利益。
”“西安事变”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珍珠港事件”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形成,都印证了张季鸾在了解国内外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时局走势基本判断的准确性。
在淞沪抗战告一段落,十九路军退出闸北的第二天,张季鸾的社评《沪局与国民的觉悟》(1937年10月28日)发表。在上海市民乃至全国民众对上海沦陷深感不安之时,文章对未来形势做出五点说明,其中第一点即是“上海本不是中国对暴日之决战地,八一三以来之上海战,只是对日抗战的序幕”。
文章在第五点中预测:“这一次,方式是长期抗战,结果是最后胜利”。虽然张季鸾本人未能亲眼见到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那一天,但他的基本估计和判断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张季鸾为一介书生,既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军事家,他对时局判断时常能有所预见,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长期积累和职业敏感。而只有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之评论,才属上乘之作。
3、注重逻辑性,文章结构严谨,论证缜密
与梁启超纵横捭阖,跌宕起伏的文风相比,张季鸾的社评更注意逻辑的严密与议论的严整。
《妇女与抗战》是发表在1938年“三八”妇女节次日的一篇社评,其直接的新闻由头是,前一天武汉妇女纪念“三八”节大会上发出《告全国妇女书》;而直接的新闻背景是,在两个月多前的南京大屠杀中,无数妇女遭蹂躏、被屠杀,日军暴行令人发指。
文章开头部分说道:“此次敌寇在中国,罪恶万端,而特别是凌辱残害妇女,为其最大之罪状。”为何将其视为“最大之罪状”?文章提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是保护女性”,“自古重视婚姻”,“严男女之别”,这也是中华民族形成伟大文明和最大民族的原因之一;但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的“贞操论”。
对“贞操论”应怎么看?过去的看法虽与今日不合,但中华民族的根本道德“以凌辱妇女为最大的罪恶——则永远不会变更。”
以上一个自然段的逻辑论证为基础,文章由古论今,分析男女平等的合法性,使保护妇女有了文化上、道德上以及法律上的依据。接着笔锋一转,提出:日本的入侵与占领,“使我们的文化,法律,善良风俗及传统信仰……立刻一切失其保障”。
在列举日军暴行后,作者提出两点倡议,一为全国男子承担起保护妻儿姊妹的责任;二为妇女自保互保。光保护还不行,还要做实际的指导。而只有保护中国,才能保护妇女。全文立论与驳论相结合,结构严密,层层推进,不仅使道理越讲越明,也使话题越议越深。
张季鸾的其他作品,如前文中提到的“三骂”,“西安事变”中的四评,虽议论方式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其说服人、打动人的逻辑力量。
4、走向通俗性,用平实畅达的语言叙事说理
张季鸾的社评有一个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和过渡的过程。在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初期,他所写的评论半文半白者居多,还带有明显的文言文的痕迹。对此,徐铸成的评价是“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而到其任社论主笔的中后期,白话文运用的越来越多,而且,尽量使用平民的语言,议百姓关心的事情。
在《最低调的和战论》中,有这样一段议论:“这四个月来,以海路空大军进攻中国南北省区,其直接加诸中国的军事的摧残不用说了,其在城市,在乡村,在陆,在海,以飞机,以炮火杀戳我们的平民,不知道多少千,多少万,焚烧摧毁我们平民的财产,又不知道是多少亿,多少兆,这都不用说了,而现在一面言欢迎调解,一面庆祝进攻我首都!
”这段文字叙议结合,以叙为主;句式长短结合,以短为主;既像作者对读者诉说,又像一位劫后余生的难民在向世人控诉。文中“不用说了”,“这都不用说了”这类老百姓生活中的语言,用于社评之中,非但不显得浅白,反而给人以平易近人,深入浅出之感。
若把张季鸾社论写作的通俗性与同处一个时代的韬奋的小言论比较,后者则更为平易、平等,这既与报刊定位、体裁特点有关,也与个人风格有关。
5、 标榜公正性,在“客观”与“敢言”间寻求平衡
“四不”原则是《大公报》追求“公正性”的基石,虽然其“公正性”在报刊发展的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且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但与同时期的大多数报刊言论相比,张季鸾的社评还是力求表现出一种客观公正的取向。例如,在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政治时,能够针对具体问题,做出客观的分析;在困难当头、抗战在即时,能够冷静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提出较为可行的建议;在抗战烽火正烈,全国军民共御外侮时,能够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相区别,不一概而论、统统加以声讨。
张季鸾1936年4月1日在《今后之大公报》中对该报“公正性”的解释是:“要求同人尽可能地剖析事实,衡量利害,不畏强权,不媚时尚,期以工整健实之主张,化全国各种感情思想上之歧界”。
《大公报》还素以“敢言”著称,这一点仍与“四不”原则相关。无论是针砭时政,抨击权贵,还是为民请命,代民立言,张季鸾时期的《大公报》》社论,都以鲜明的个性体现着这位“文人加报人”的职业理想与职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