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家 陈新华 对话陈新华
1972年就读于广州美院国画系,1979年考入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山水画研究班,毕业后留校任教,副教授。
作品《雨林奇》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密林》入选中国当代工笔山水画展;《山家》获全国首届中国花鸟画展佳作奖,《乡土》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奖。
现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更多去博宝艺术家网
(以下访谈内容陈新华简称“陈”,陈振煌简称“煌”,王艾简称“王”)
煌:您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为复杂而充满暗涌的世界,但是里面对象与对象之间的穿插和逻辑关系又透着一股冷静。这是源自您内心世界的外向流露,还是对某种境界的向往?
陈:两者皆有结合。内心流露是人的精神追求的一种结果,也是艺术家的一种内心需求。在不断地学习与延伸情感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在作品上。对意境的向往,实质上是对客观世界、对人生有某种体验,而这种体验就是主客观结合的结果。
对于现实主义画家来说,创作除了传达信息之外,主要是表达主观情感。之前我用了比较长时间画了很多抽象画’,它可以尽情地传达画家的形式感与主观感情,但总感觉抽象形体很难使人保持确切持久的印象。
”85美术思潮之后”,我想寻找一些具象的载体,承载抽象的形式感觉。其实我画画完全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古代高士喜好弹古琴,原因在于乐器里面只有古琴是最适宜弹给自己听的。
我画画也是这样,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所以我偏好画那些有常理无常形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固定形,有利于抽象思维的发挥,别人可能不太懂我画什么。像有一些高空俯瞰的画,虽然很抽象,但仔细辨认它又是具象的。我也喜好画大山河流,这跟我崇尚沉雄博大之美有关。
煌:您对于中国画的看法是怎样的?您在艺术创作中是如何探索的?
陈:我对于中国画的看法,年轻时有点接近林风眠与吴冠中,但又不全然。认同的是认为国画的系统要开放,海纳百川;不同于他们的在于:我认为中国画应该是有界限的,笔墨是中国画特质的体现。另一方面,近几年的中国画坛,有一种回归保守的现象,民族主义的情绪上升,但不应将这种情绪带到学术中,艺术家作为单独的个体,应该有完全的创作自由。
是不是国画?或者有没有笔墨?只要画出来的东西有情趣、有意境就是好作品。但你设定自己是画国画的话,就必须受笔墨的约束;笔墨是一种上千年积累的表现形式语言,它是作为中国画种区别于其它画种的特征所在;笔墨虽具有极高度的审美价值,但它不该是衡量一幅画的唯一标准,不然很多问题的思考,很多情感欲望的表达,就会被束缚住。
80年代我在香港出版过一本画册,就是这种思考探索的记录。画面大多是浓烈的色彩,并融合了多种元素。因为在国画系任教的需要,必须沉下心反复地临习很多传统经典作品,这自然又吸引着我对传统的兴趣;但单凭传统语言,又不足以表达自我的现代感受,必须将其与现代造型技法结合,这也是现代人的文化优势。
但这种结合极为不易,我不断遭受挫折失败,中国画是需要时间来磨练的,所以我有段时间探索色彩、抽象表现等。
后来又将这些探索带进传统,只是觉得缺啥就补啥,从来都不是有意计划的。像80年代大家都在找寻画画的出路,而我则是随着自己的感觉走,没有过于理性地思考国家民族问题,完全只是自己心理的需要。人家已经使用过的形式和做法,我就不想重复了,无论水墨或重彩,我都避开常规画法,这是个性使然。
煌:从《乡土》等早期造型严谨的作品到现在如《海之花》等以笔意定造型的作品,您对造型的认识逐渐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您如何看待造型与表现之间的关系?
陈:我跟黄一瀚都比较注重造型。平常事物使你产生感触大多是因为它自身的造型之美。一些古代画家只注重笔墨而忽视造型,缺少型的传达,形成不了强烈的感染力。而通过画面形态来凸现画家个性这方面,审美的灵性很重要,更多的是后天得来,包括阅历、生活体验、自身的修养等等。我画的对象并不是完全复刻事物的形象,而是我对它的独特感受,旨在表达出我的某种艺术趣味。
煌:您采用了中国画的材质和技法来表现您的画面,强调着水墨材质的自在性。您如何看待您的作品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共通点?
陈:其实我并没有很严肃地思考这问题,只是任性随心地画一段重彩,觉得腻味了又搞一段水墨;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总是要不断地改变口味尝试。在这方面我很花心,各种手法都不能割舍,而各种不同手法的互相渗化作用就是创新的催化剂。
最初我是凭着自身的一种感情,一种自身造型能力来画;后来画的画是在国画系教学期间的研究,主要是实实在在地去了解古画,特别是宋画。而古典作品中那种宏大的气息对我影响很深。我现在创作的这一系列的大型作品,想要表达这大气的境界,完全是来源于对汉唐北宋的经典艺术品的理解。
煌:水墨与色彩这两种并行不悖的表现手法在您的作品中是如此纯粹与彻底。色彩如唐元壁画般华丽辉煌,而水墨则如传统品味般至高无上的冷峻肃穆。您如何思考这两者在您作品中的表达意味?
陈:不管是水墨还是着色,我个人不太喜欢画得跟人家画的类似,我很少用惯常的方式去画,尽量避开与他人的相似之处。我想这是我经—过独立思考的结果,是在学生时期就有的刻意追求,也是长期探索的结果。我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寻找。因为创作宏大复杂分量重的画很不容易,具有挑战性,它需要大量的技法,非常费力。大创作的魅力是无可替代的,过于简单就缺少了震撼力和诱惑力。
煌:我特别注意到您细腻的笔触构成了画面博大雄;凸的张力。从《宝岛物华》到《大美青藏》,生命在讴歌在膨胀,似乎扩张超越了画面本身,这似乎是您对生命的一种思考抑或表现。
陈:我不是哲学家,没有详细地作这方面的思考。平常人肯定对自己的生活、行为、做法有感触和思考,但可能不会很具体地去归纳自己想的是什么。这种追求也可能是对某种文化、传统或人生的理解,或是对对象的认识、审美的结果,像是心里有种无形的东西指引着你。
有了这种追求在绘画技法上会有选择地来学习,选择某本书来看,但是很难具体地说出是怎样想、怎样做的。如果我之前换了一个家庭,或换了一个老师,或换了一个文化环境,就可能不是这一种追求。它不仅仅是主观思考的结果,跟客观的环境亦息息相关。如果我是生活在商人家庭,那种影响、感染又会是不一样了。更复杂的是,它不只是思考的结果,影响的因素包括文化、环境、心理、生理。
煌:能谈谈您对故乡海南的感情吗?在您的作品中总离不开对热带景观的表现,也谈谈写生对您创作的意义。
陈:每个人都有乡土情结。例如潮汕人对家乡的感情很深,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会去表现家乡的风土人情。我很多画也是受家乡的影响。海南是一个热带色彩浓烈的地方,它跟传统国画的趣味很不相符,不像中原、江浙地区。那是一个植物茂密生长的地方,因此视野不会很广阔,往往一个十几平方的地方,就容纳了十几种植物。
我就想探索一种手法把这么复杂丰富的情景里的东西表现出来。这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是难以想象的,可能十几公里才一种树,视野单纯开阔,这时就必须抛去画海南的画法,另辟新路。
所以我认为写生不能用一个方法、一个思维、一个模式,也就是说要不断地思考探索适合审美情感的表达方式。因此,户外写生时每个地方应该就它的特色来表达,任何地方都画一样,这不该是一个有想法、有追求的画家做的。
所以无论画水墨还是其它,都是要按照各自地区的风貌来画,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就是地理环境的影响。我上了大学,学习国画以后,一直在思考如何表达的问题,当时我只是执着地画出我所看见的一切,慢慢地画面形成现在这种感觉。
可能情感的表达是我创作中首要的因素,为了表现某种审美感染可以打破任何传统程序。国画的学习,游弋于笔墨与生活这两者之间,而我认为生活比技巧更重要。
一开始可以不要太传统,先追求感情的真挚,笔墨可慢慢学习探索。但如果开始生活就被笔墨局限,很可能会走不出来。要是有真正的追求,你将会不断地想办法解决问题,不断地学习吸收传统。熟练运用传统手法,是积年累月的长期积淀,非一朝一日之功;画家不同时期应利用不同的文化优势进行创作。我的做法基本是这样子的。
王:对于您的信息,我们可翻阅的资料并不多。在您简短的简历中我们可看到的只是关于学院的深造及多次全国性展览的荣誉,这会让人好奇于这样的作品是源于怎样的学习历程。您能简单谈谈您的求学经历吗?
陈:我觉得自己是为画画而生的。自3岁有记忆时就开始在新买的衣帽上面涂鸦,能涂能画的都被我涂满了,很痴迷于此。小学一年级时,上课就在课本边角空白处画满各种动植物与人物。当时很少人知道画画是怎么回事;我的父亲是中医,也没有想将来要我学画画当画家,画画似乎就像本能需要,没有什么目的性。
从刚开始临摹线描的《西游记》、《三国演义》,到后来慢慢接触中国画的书。最初是钱松岩的《砚边点滴》和吕凤子的《中国画技法》,吕凤子称道的“绵里针”的中锋用笔到后来一直都影响着我对中国画的认识和理解。
但当时小地方从来未见过人画国画,揣摩着印刷品的效果,用图画纸打湿水来画所谓的国画。中国画当中如何用笔是左右我对画家喜好的一重大因素,不知何故自小我潜意识里就十分喜爱含蓄、内敛,犹如虫蚀木、屋漏痕之类的用线,这可能与我自小就性格内向孤独有关。
“文化大革命”时虽然读书升学的机会完全没有,但另一方面,像搞大批判专栏、画漫画、刻蜡纸编小报这种社会学习与磨练现在看来似乎比机械地学素描更生动鲜活。
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当农民,做木工之后当民办教师,期间经常参加县地区举办的美术展览,并获得一些奖。1972年,通过海南地区文艺部门的推荐,我参加美院的招考。
那时我 还没有学过素描,考试之前跟朋友借了一本《怎么画铅笔画》临时补了一下课,我依然能够以高分被录取。而现在学生的学习过程恰与我相反:先机械地学习素描,再学创作。
现在的学生一般素描都画得不错,但一搞创作就相形见绌,可见绘画更重要的是审美灵性而非技术。感性的艺术想象、理性的技巧学习、艰辛曲折的人生经历,加上独特的人格品质,形成了我现在的艺术风格,我的人生理念是无为不争,那么执着地追寻探索,是因为着迷上瘾不为别的。
王: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您的作品一度为香港画廊所推崇。可正当被其它画家投以羡慕眼光时您却拒绝了一切艺术市场上的接触,闭门搞创作。您当时是如何考虑的?现在对艺术市场的态度是怎样的?
陈:当时在香港卖的画都是买家自己来找我,他们首先在杂志上注意到我的画,后来通过朋友联系我说要买我的画,其实我并不认为自己画得很好,只是觉得有人欣赏我的画也是一件好事。后来去香港开了一个展览,效果还挺好,接着就有很多画廊代理找我,谈到签约的事,但我不想把自己置于这种商业运作当中失去创作的自由。
我是一个一旦有了灵感就会抓紧时间表达出来的人,总是旧作没完成又急着画新画,只热衷于过程,不太在乎目的结果。已经画过的就不想再重复,即便有巨大的利益放在眼前还是不情愿动手不动脑地复制。
这并非关乎道德品格的问题,它是性格气质的自然流露。钱当然是好东西,但钱从他人口袋里转到你钱包是一定要付代价的。人生面对很多利益,每个人都不可能全占有,必须做出选择。
安分守己地选择适合自己,真正必要而非虚荣所需。作为一个画家,你既想天马行空为所欲为地胡涂乱抹,又要卖画赚大钱,这是不大可能的。这些问题看透彻就慢慢地学会放弃,放弃一切身外之物。
我现在看到别人物质上获取享受已毫无感觉,但是如果看到别人好的艺术作品,就会很兴奋,想方设法去超越。人活着;第一要务当然是生存,对于我目前的状况而言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够吃、够住、够穿,这就好比一棵花已经具备了生长的基本条件:阳光、空气、水份、土壤、养分,那它就会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对于物质的享用,金花盆银花盆于花而言结果一样。自然界对生命的法则是够用即止,唯有人类贪欲无止。若是真正的艺术家,他就会像花儿一样,画画表达是成长的自然,他无需更多的动力目的。
王:对于艺术市场您有什么看法?
陈:我的心态其实比较像黎先生,不太管别人的事,听陈金章老师讲,黎先生知道别人假冒他的画,也拿到市场上去卖,他只是说了一句话,大家都是吃口饭嘛!他对这些人都是很宽容的态度。艺术作品能够卖钱养家糊口,让人不愁吃穿用,安心游艺,这实在艺术家的幸事。
但事情总是两面的,因为市场的势力炒作,很多原本的艺术价值观念就给搅浑了;面对炒作出来成千上百万一幅画作,很多艺术家都兴奋得晕头转向,耐不住寂寞,直奔画外做功夫,这其中得失,真令人无奈。
人非圣贤,在这烦躁、利欲熏心的物欲俗世中要守住自我之理念,是极其艰难的。在信息爆炸的现代,是寻不到桃花源了。当客观不能转移时,我就背对现实,采取鸵鸟政策,眼不见心不烦。我对人生的看法总体是悲观的,这尤其对于有思想的人更是如此。
所谓“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就具体而言,在生命的每个过程中,只要我们采取达观的态度去对待,就可以超脱其外。在这个层面上我的作为又是积极进取的。我对待人生艺术的态度是自闭自乐、乐己利人,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王:总觉得陈老师是一个大气若钟的人,在接下来有一些什么计划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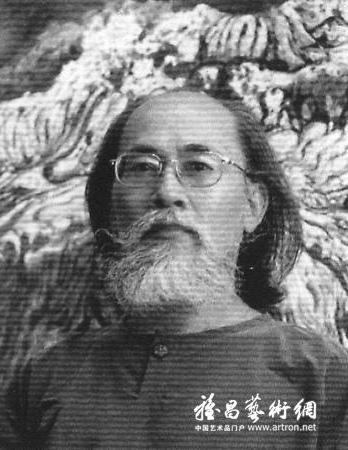



![陈新华乒乓球 陈新华[乒乓球运动员]](https://pic.bilezu.com/upload/1/33/1336345e5e3d0caabadf745e5aff04ab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