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张中行外传 读《张中行别传》感言(靳飞)
孙郁先生特意赶在张中行翁百岁诞辰的时候,印出大作《张中行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这份心意颇为可感。 其实在中行翁的诸多小朋友中,孙郁与他相识不算很早;交往呢,如果对比我与行翁的多到有些腻的程度,孙郁与行翁则不外乎见面的次数较寻常人稍多些而已。
记得仅仅是孙郁与行翁稍多几次见面之后,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出版《张中行散文》,需要有篇论说性质的文章作序言。
我问行翁该由谁来干这个活儿?我所拟的人选,本是请周汝昌先生或是谷林,行翁却毫不犹豫地说,“请孙郁写吧。”老人下了一个“请”字,我很有些惊讶。后来《十月》杂志又搞起一个专栏,要老人们自己作几篇文章,再配发一篇别人写的简传性质的文章,编为一组发表。
轮到行翁的这一期,行翁的意思仍然是请孙郁。 某次我与行翁小酌,行翁忽然问我,“咱们现在真有那么大的名气吗?”我说,“恐怕是真的。
最有说服力的是书摊。您的书左一本右一本选来选去地出,如果卖不出去,书摊是不会接受的。”老人点了点头,似有些快意。我们顺着这个话题,聊着聊着就聊到身后事。我说,将来会有人为他作传,只是为他作传的最佳人选并不是我,因为“太近”。
老人很以为然,“你不要写!不值得。”我说,“不是值得不值得。到时拦也拦不住。您以为谁是作传的恰当人选?”老人沉吟片刻道:“第一人选是孙郁。” 事实上,孙郁是另有许多事要做的。
作为鲁迅博物馆的馆长,他要关注许多大题目。近年来他论鲁迅,论周作人,论胡适,能扛起这三座大山就不容易,更何况他还以余裕论及其他。望着书柜里他的那一排著作,想起行翁的“没有时间”的话,再看看手头这册《别传》,遂感叹老人知孙郁也深,可以说,行翁看孙郁是没有看走眼的。
非常遗憾的是,我始终未曾问过老人何以如此器重孙郁,人品自然是其一,但这绝不仅仅是人品问题。
现在想来,老人隐约是以孙郁为知己的。那时很有趣,我与行翁的闲聊,基本是想到什么说什么,有时是我顺着他的话题,有时是他顺着我的话题,话题有正经的,也有不正经的,反正聊起来就是滔滔不绝,没有冷场的时候。
而孙郁一到,气氛就变了,老人必是正襟危坐起来,谈文论语,差不多是什么话题严肃说什么。作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张中行翁与孙郁,好像是陈寅恪先生与蒋天枢教授的关系,张亦视孙为可以身后事相托的门下弟子。
我读了《别传》后打电话给庞旸,建议她也为老人作一部传记。为了促成这一愿望,我甚至愿意陪一回绑,作一本在行翁身边所见所闻的记录,与孙、庞的传记合为三传,印成合集。
假若说日后形成所谓“张中行研究”的话,不客气地说,这应是至为重要的资料。 回头再看孙郁兄的这部《别传》,表现的是孙郁对张中行翁的所知程度,其特色排第一位的是公大于私。
孙郁是文学评论家,他对中行翁的关注,不是出于熟知或交往的亲近,而是首要的对行翁的文学成就的关注。孙郁在《近三十年的散文》里概括说,“张中行的思想是罗素与庄子等人的嫁接,文章沿袭周作人的风格,渐成新体。
他的文字有诗人的伤感也有史家的无奈,哲人的情思也是深埋其间的。在他的文字里,古诗文的意象,与现代人文的语境撞击着,给人沉潜的印象。他在体例上受到周作人的暗示,也自觉沿着周氏的路径前行。可是有时你能读到周作人所没有的哲思,比如爱因斯坦式的诘问,罗素式的自省,这些因素的加入,把当代散文的书写丰富化了。
他的审美意识与人生哲学,有着诸多矛盾的地方。意象是取于庄子、唐诗,思想则是怀疑主义与自由意识的。
在他的文本里,平民的情感与古典哲学的高贵气质,没有界限。他的独语是对无限的惶惑及有限的自觉,文化的道学化在他那里是绝迹的。也因于此,他把周氏兄弟以来好的传统,延续了下来。”《别传》基本就是围绕这一论定,阐述作为文学家的张中行先生的身与心的经历。
行翁的自传《流年碎影》,定位还是在于“六代之民”的回忆,是“生”多“文”少,孙郁的《别传》则在此方面作出了有力的补充。 《别传》的特色之二,是史大于文。
孙郁没有就文论文,而是把中行翁置身于现当代文学史讨论,较为明确地标示出,张中行及其“张中行现象”是当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页,并且这一页在当代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由批判到全面继承过程中,自有其独到意义。
孙郁以其切身感受描述说:“张中行在审美的层面是有古典的味道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新潮,有时看还像个遗老。但这个遗老却并不腐朽,内心是汩汩流淌的激情。
他在思想上的独异和审美上的古典化,使他既带有了西学的美质,也保持了东方的情调,在韵致上有着美丽的品质。我有时想,西方的那一套和东方的基调要调和起来,在书斋的层面可以做到,可在平民化的基点上就不那么容易。
他的出现,在我看来是把贵族化的叙述方式,和平民拉近了。布衣里还有高贵气,在泥土间升腾的却是天地间的伟岸的日光。不仅自由主义的文人没有过,左翼的文人何尝有过呢?”(《漂泊的心》)个中亦蕴含着孙郁由读中行翁著作而引发的对自身乃至他所属于的世代的深刻反省。
所谓“张中行现象”,固然出了几个如我一样在文字上希图能“山寨”一回的人,但更大意义是启发了一大批如孙郁这样的人。
孙郁兄把“张中行现象”作为“事件”描述而非以文学流派视之,这是非常准确的。 《别传》的好处还有很多,留待读者诸公慢慢品味。专由我的角度所见,总是忍不住见到的都是孙郁知中行翁之深。
沪上王清园元化先生生前,我们一起在联谊餐厅品尝居淮扬菜头把交椅的莫有财莫师傅的手艺,席间元化先生忽然说道:“文心雕龙里的话,我最喜欢的是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读孙郁《别传》,想到此一情景,本拟题一律纪之,涌上心头的却是行翁的旧句,“几回清泪湿衣裳”。情之不能已,便有了以上的这些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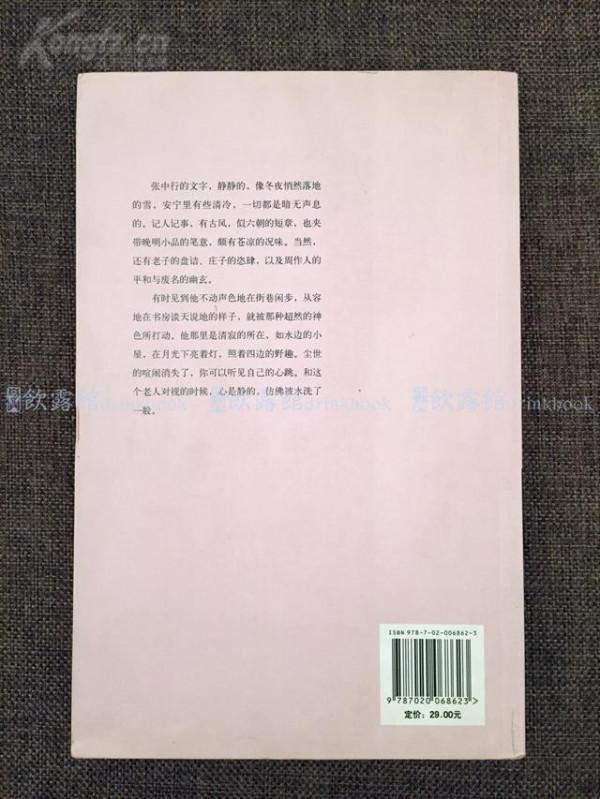
















![>孙郁讲鲁迅 [光明讲坛]孙郁:鲁迅在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选择](https://pic.bilezu.com/upload/9/f7/9f7e43556d817dfb654d9f0ffb1d401f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