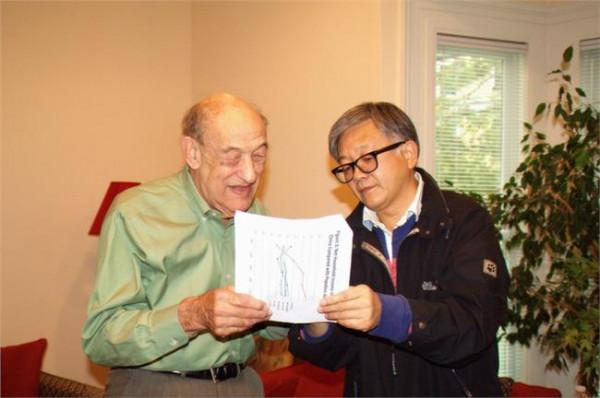周晓虹中国体验 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
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1)_社会民生_光明网
社会心态,社会,社会文化变迁,心态,社会心理
社会民生
作者:周晓虹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受到人们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们的高度关注(孙立平,2005)。“对转型的学术观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周晓虹,2014)。
不过,同人们对转型的高度关注相比,尽管在这一领域也产生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佳作(如伊亚尔等,2008),但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进展尚不能回应转型提出的理论与现实挑战。
不仅“转轨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看上去几乎没有在可观察到的现象中反映出来”(乌斯怀特、雷,2011:25),而且在诸如社会心理学这样的本应关注社会变迁的学科中,也缺乏对社会转型的系统和长期的研究(王俊秀,2014)。
就中国社会心理学而言,不仅这几年许多人意识到社会转型既向中国社会心理学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方文,2008;马广海,2008;周晓虹,2009;王俊秀、杨宜音主编,2011),而且中国学者多年来也一直敏锐地从“社会心态”及其相关领域入手,欲图为有关转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独辟蹊径。
单单这30年中,与“社会心态”一词相关的学术论文不断增多就是一例明证。①这里的问题主要在于,除了不多的一些研究外,不仅大多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都相当肤浅,而且在重建过程中受美国影响较大的所谓中国主流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态的研究依然缺乏应有的兴趣(杨宜音,2006;王俊秀,2014)。
肤浅,会导致在“社会心态”一词滥用的同时,真正关涉社会转型本质的相关议题被遮蔽或过滤;而兴趣的缺失,则不但无法对转型时代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做出富有价值的说明,而且从根本上说也会使得社会心理学的中国化努力最终付诸东流。
一、社会心态:概念厘定与学科谱系
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一词,在中国社会心理学领域大概是仅次于“社会心理”获得最为广泛使用的概念,同样也是“界定多不严格”(杨宜音,2006)、最缺少“学理上的缜密分析”的概念(马广海,2008)。
在中国社会近30多年来的转型实践中,这一概念因与宏观的变动过程的“天然”联系(在中文语境中,“态”或“态势”本身就有一种变动不居的涵义),获得了最为广泛同时也最不严格的使用。这一状况也促使几乎所有稍稍规范的研究在起步之时都首先会认真辨析“社会心态”概念的基本内涵,以期使自己的探索能够奠定在严谨的科学基础之上。
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既有文献中,有关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基本上达成了两条共识:其一,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整个社会或社会大多数成员共有的宏观的社会心理状态。杨宜音提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杨宜音,2006)。
其二,因为受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一社会心理状态是动态的,或者说是变动不居的。
在本文欲与之对话的一篇论及社会心态及转型社会研究的论文中(以下简称“王文”),作者就提出:“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并不断发生着变化的”(王俊秀,2014;马广海,2008)。
上述论文在表面热闹实际上孱弱的社会心态研究领域堪称为数不多的几篇重要而严谨的文献,其作者将宏观性和动态性界定为社会心态的基本特征自然恰如其分。这里的问题是,指出宏观性和动态性是否就把握住了“社会心态”这一概念的全部内涵?换言之,我们是否可以将社会心态简单地表述为在一定时期内弥漫于整个社会或某些社会群体中的宏观的、变动的社会心理状态?
将社会心态的基本特点限定在宏观性和变动性两个特征之上所带来的局限,从“王文”给定的社会心态的定义中可见一斑。在这一定义中,王俊秀强调社会心态是一个社会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也强调了“作为一种氛围,(能够)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但是作者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向读者交代,这种普遍一致的心理与行为特征是从何而来的?或者说是如何形成的?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疏忽”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如果站在单纯的心理学的立场上去解释社会生活及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那么,一方面从主观上说,研究者的关注点就只能像加德纳·奥尔波特那样,聚焦于社会或群体生活对“个体”成员及其行为之影响(Allport,1985/1968);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说,因为缺乏互动的视角,研究者就无法去想象也更不可能去解释,众多单个的个人是如何通过某种社会或心理机制,最终形成一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普遍一致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的。
如果转换到社会学的立场,去思考从单个的个体心理转化为群体或社会心理的事实,在宏观性和变动性这两个基本的内涵或特征之外,社会心态恐怕还有第三个特征——这在我看来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即涂尔干所说的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所具有的突生性(emergence)。
突生性是指包括社会心态在内的社会事实确实源自个人事实或个体心理,但它并不是个人意识或心理的简单之和,它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借用涂尔干的话来说,“集体心态(group mentality)并不等于个人的心态,它有其固有的规律”(Durkheim,1966:xlix)。
应该说,包括“王文”在内,这一领域现有的文献大都比较好地把握了社会心态的宏观性和动态性,但却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突生性。
比较而言,在这一点上,杨宜音的研究离社会学家的视野最为接近,她意识到社会心态“不等同于个体心态的简单加总,而是新生成的、具有本身特质和功能的心理现象”。但是,多多少少受限于心理学的个体主义立场,在杨宜音那里,这个“新生成的”社会心态,却依旧“来自社会个体心态的同质性”(杨宜音,2006)。
如此一来,作者所做的所有向社会学“靠拢”的努力,最终还是在两个向度上化作一场身不由己的“揖别”:其一,既然具有同质性的社会心态原本就是由具有同质性的个体心态而来,那么在这个个体心态向群体或社会心态的“转化”过程中,究竟“新生成”了什么?其二,既然在这个转化的前和后,社会心态的内容都是同质性的,区别只是在其承载主体一为“个体”、一为“群体”或“社会”,那么是否意味着,同质的社会心态可以通过一样同质的个体心态获得一种还原主义的解释?
对突生性的忽视,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还原主义立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王文”有关社会心态的学科传承的讨论。在“王文”中,作者花费了相当的篇幅讨论社会心态研究的学科谱系,但是,由于作者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差异何在,以及由这种差异造成的与社会心态这一研究论域的亲疏远近,以致作者最终得出的结论就只能是:“社会心态的研究既要继承心理史学的传统,也要继承心态史学的传统”,“既要关注社会学的传统问题……也要沿着涂尔干所希望的个体表征与集体表征的心理学方向去努力”,“以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继承和发展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宏观视角和现实关怀”(王俊秀,2014)。
这种折衷主义的立场不仅混淆了上述相关学科的本质差异,而且由于其对心理学立场不恰当的强调,反而有可能使研究误入忽视突生性甚至忽视社会生活本质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