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中学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雁:转轨中如何实现起点公平
《中国经营报》:年初,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向他颁发了国家奖章,前些年我们还了解到他拍摄了某奢侈品的广告,但总体上对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当年东欧剧变中的政治风云人物消息很少,20年过去了,他们如今的境遇如何?
金雁:我曾经去过戈尔巴乔夫正在做的基金会,当时他不在,是他的副手接待我们。剧变后戈尔巴乔夫的民众支持率比较低,这是事实。我觉得两个原因造成了这一局面:一是俄罗斯人有很厚重的“弥赛亚情结”(大国意识),一个庞大的前苏联终结在他的手里,总不能说他是成功的。
二是戈尔巴乔夫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非理性意识比较强的俄罗斯不讨好。因为社会民主党比较温和,而俄罗斯民族意识中非此即彼的张力比较大,对社会民主党这种温吞水的风格不太感冒。而且戈尔巴乔夫这种过时政治家也不擅长煽情造势,不善于利用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他被冷落并不奇怪。
跟戈尔巴乔夫一样,当年东欧剧变时的推手们如今都已经退出一线。2009年11月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了一次苏东剧变20周年的讨论会,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前斯洛伐克总理杨·卡诺古斯基、前波兰总理别莱斯基、前匈牙利外长耶森斯基等剧变中的主要人物都到场了。从这些人在会上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强的失落感。他们认为,民众非常容易忘怀,不会感恩。
其实,经过一个艰难的转轨过程,民众在剧变之初的浪漫幻想已经终结,对国家转轨最初的推手也开始淡忘。另外,这些剧变推手本身很多就是过渡人物,在国家转轨过程中,原有体制要打破,这相对容易,但“破”之后要建立什么制度,他们自己也未必适应。
没有预想的成功也很好理解。剧变之初还有很多球星、作家等明星类人物被老百姓盲目推到了前台,但他们在内政外交上的管理实践、处理事务的能力都不足以掌控一个国家,很快被后起的专业人士取而代之,也很正常。可以说,这些国家筛选政治领袖的机制已经逐步完善。
其实民主政治下人们不“感恩”也很正常。过去二战刚打赢,丘吉尔就落选,海湾战争刚大胜,老布什就被赶下台,何况这些东欧人?民主政治就是允许老百姓对公仆“过河拆桥”的,只有专制制度才会要求百姓“吃水不忘挖井人”。
不过,民主选举得票少只能说明民众不认为他们适合掌权,并不说明民众认为他们就是坏人。像戈尔巴乔夫,如果俄国多数民众认为他是“叛徒”、“罪人”的话,下届还想竞选的梅德韦杰夫向这么“令人反感”的人高调地颁发奖章,就不怕丢掉选票?你能设想一个竞选中的德国政客敢向“新纳粹”颁奖吗?
《中国经营报》:我们该如何认识东欧国家转轨过程中开明领袖的作用?
金雁:东欧国家转轨前的政治领袖,虽然当时有前苏联扶植上台,但为了赢得合法性,他们也争取到了一定的民意基础,不可能一屁股坐在前苏联的立场上,其中的开明领袖是真正的改革派,只不过,在群众大潮汹涌而起的时候,他们所坚持的改革,民众已经嫌慢了。
《中国经营报》:那些基层组织的人物呢?比如我们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看到那些秘密警察人员在剧变之后再就业都面临很多障碍。
金雁:原有的特务机关、警察部门、跟前苏联相关的情报机关的人员,在剧变后肯定受到影响。比如,在这些国家的竞选中,有时候其中一方突然抛出了竞选对手的父亲曾经是前苏联克格勃的线人这样的材料,这是极具杀伤力的,因为东欧国家的民众反苏情绪都很强烈,非常反感警察机关的人物,尤其是给克格勃做过线人的。虽然参选者本人可能并没有问题,但是也会因此失去民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从政了。
金雁:这些国家跟前苏联不一样,它们大多是二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中还经历了1944年到1948年人民民主多党合作的摸索阶段。从二战结束到1989年东欧剧变40年间,虽然东欧国家也有前苏联的驻军、重兵压境,整个社会经济也在向前苏联模式改造,但那种一竿子插到底的社会控制模式远远不如前苏联。
比如捷克,它有发育非常良好的市民社会,包括农民所有的合作社、各种自愿组织等,本身的社会救济、修复功能非常好。另外,各种文艺团体、文化沙龙、学术小组虽然在东欧剧变前是严格禁止的,但在这些国家其实很难完全被取缔,也很难屏蔽外部的消息,因为它的消息源非常多,仅波兰就有1000万人生活在美国,后来又有大批的人流亡到西方。老百姓在社区过日子,而社区都是地方自治性、服务性的,它们以老百姓的需要为基础来运作。
正因为东欧原有的社会建构比较完整,所以后来虽然经历了制度的垮掉和重建,但整个社会不会太乱。
另外,在这些国家,左右党派的差别其实很小。左派说要保障福利,有时候引入自由主义,右派宣扬市场原教旨主义,但也要保障福利,左右逐渐趋同,之间的张力并不大,所以无论哪个党派上台,对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影响。其完善的公民社会跟政府的行政体制不搭界。
《中国经营报》:这么说,东欧国家的民众对转轨后的满意度还是很高的?
金雁: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不能一概而论,这取决于比较的维度。比如原东德在转轨之初社会满意度比较高,因为要跟旧体制相比,但在转轨完成后,比较的参照系变成了德国西部,满意度下降也算正常。另外,剧变时已过而立之年、在原制度中建立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已经进入官僚体制的人,对转轨满意度就很低,而年轻人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与这些“老人”截然相反。所以,不能从一个局部截取出“东欧人民今不如昔,怀念远去时光”的结论。
《中国经营报》:如何看待东欧各国现今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潮?
金雁:只要有民粹出现就是社会的上层出了问题,即在改革过程中,有一部分人暴富,一部分人没有享受到成果。至于民粹主义以什么方式表现,比如民主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则取决于当地的文化。很多转型国家都把民粹看做是改革的大敌。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上层、精英阶层都成为既得利益阶层,那民间肯定会表现为民粹,因为民间没有其他资源,他们只能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情绪来表达他们在转型中积累的不满。不过应该说,除了俄罗斯和一些独联体国家,多数中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总的来说并不严重,至少没有我国那么突出。
《中国经营报》:在转轨过程中,东欧几个国家对国有资产的处置方式各具特色,是什么样的内部因素促成了它们各自的处置方式?你如何评价?
金雁: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个误区,总认为这些国家私有化的方式是“洋顾问”给设计的。其实这些国家在民主化之后,本国的政治家尚且不能左右民众,更何况所谓的洋顾问。
东欧各国的“分家”方式都是经过本国各阶层、集团讨价还价、充分博弈的结果。通过这样的博弈,虽然交易成本比较高,但好处是找到了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利益平衡点。
匈牙利剧变前国家财政破产,政府留下了全欧最高的人均债务,所以它采取了“只卖不分”的方式,由于公开竞价,出价高者都是外资公司,于是出现了“面向外资全卖光”,卖的钱用于还债,用于社会福利。
捷克的国家财政状况较好,二战前曾是世界十大工业国之一,国民自豪感强,不愿意外资收购,于是它就采取了“只分不卖”的方式,即把国有资产的价值主体以投资券形式公开、平等地在国民中分配。然后由他们在开放性的股市选购国企股票。
总结起来,这些方式都是希望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在规则平等基础上找到最终的所有者,都是根据本国状况设计的,也都不是完美的,最终互相学习、参照,殊途同归。
《中国经营报》:但同样经历私有化过程的俄罗斯却形成了寡头经济,这是什么原因?
金雁:俄罗斯其实主要的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有“分”。后来形成寡头恰恰是因为俄罗斯私有化“改分为卖”之后,一些权贵通过“内部人交易”攫取了国家没有分给百姓的那些资产。俄罗斯有个名词叫“诺缅克拉杜拉”,即“组织部安排的官员名单”,就是这些人在剧变之后以权钱结合的方式掌控了国家资产。
东欧国家公平分配国有资产的前提是民主化,所有党派在党国分开的时候都是净身出户,媒体和公众发挥监督作用。
《中国经营报》:这些年,当东欧在我们视野里逐渐模糊的时候,东欧的知识界又是如何看我们的?
金雁:可以说我们之间比较隔膜。东欧都在向西看,它们对中国的报道不是特别多。我在东欧左中右的人都见到了,都比较友好,但他们也对我们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焦虑,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可能改变世界规则的,担心中国模式有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福利政策。
《中国经营报》:从社会结构上来说,农民的数量和组织程度是否是我们和东欧转型国家的不同?
金雁:是的。东欧国家的农民都比较少,而且一些国家像波兰、南斯拉夫原先就没有经过集体化过程,农民本来就是独立农庄,比国企工人自由度要大。所以,转轨以后这些国家的农民反而成为保守的力量,因为他们觉得在转轨过程中自己得到的少,失去的多。
其实除了社会结构上的不同,东欧国家在转轨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带入市场经济结构后发生了整体的市场紊乱,转轨开始的经济滑坡即与此有关。而我们其实在改革前是命令经济,计划也没有,市场也没有,改革的可逆性反而比他们强。
《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金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相关
学界夫妻档
/马连鹏
文艺圈多夫妻档,其实学界一直以来也不乏伉俪组合,如梁思成和林徽因、钱钟书和杨绛、陈乐民和资中筠。
而要提到今天活跃在学术一线的学者夫妻,秦晖和金雁可称其中的代表。有趣的是,作为二人共同恩师的赵俪生先生与夫人高昭一先生也是学界一对著名伉俪,他们联袂成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秦晖与金雁的组合也许可算作另一种师承。
很多第一次见到金雁教授的人,都无法把面前这个整洁得体、气质端庄的女学者跟那个衣着随意、不修边幅的秦晖联系起来,就连很多秦晖的老友们也一直疑惑,优秀如金雁者是如何被秦晖骗来的。
如今夫妻二人都是“术业有专攻”的知名教授。丈夫被称为当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其涉猎广泛,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转型正义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等,都是中国社会最纠结的大问题,他的每一次发言都能在学术界引起震动。
妻子的学术水平也不遑多让,是国内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历史研究的翘楚,尤其对东欧各国社会转型历程的研究独树一帜。一对学者夫妻多年来相濡以沫,互相支持,加之本身两人在研究中又有相当的重合部分,于是常常合作发表文章和著作。
对此,金雁曾言,“多少年来秦晖都能够与我共同协作有关东欧、俄罗斯的文章,而我对他感兴趣的题目却插不上手,帮不上忙,好像显得对他有些不公平,平时我写作的过程也常常与他讨论,或者写完之后让他"润色把关"。”
两人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源于20年前。
1990年,金雁远赴波兰访学,恰逢东欧剧变,在经历的“读书还是读社会”的短暂纠结以后,金雁毅然投入到正在生成的历史洪流之中,两年时间跑遍了整个东欧,亲身经历的东欧诸国的整个转轨进程。
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与留守国内的丈夫的书信就成为这对学者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秦晖的每一封信都包含了大量自己急于了解的有关东欧社会转型的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学者他明白这些事实资料对自己的意义。
金雁在奔忙调研之余给秦晖总共写了300多封信件,有时候一天几封,有时候几天一封。即便如此高密度的通信,有时仍不能满足秦晖的需要,他在一封给金雁的信中“抱怨”:“已经好几天没有摸到信了,我去摸那个信箱,手都磨破了。”
“我知道他不是想我,而是对东欧信息的渴求”,金雁戏言,“但这对我是个鼓舞。”
归国之后,金雁将二人来往的信件整理出来,出版了《新饿乡纪程》,但她觉得比之于社会历史变革的缤纷复杂,这部书显然还不够。
所谓“历史的终结”也有一个长期反复的发酵。作为一开始的观察和亲历者,秦晖金雁一直跟踪这一进程,记录身处其中的历史主体的跌宕沉浮,2004年一部从逆向的视角回顾东欧社会变迁的《十年沧桑》终于问世。
在这一过程中,秦晖的自由与福利、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中国的左与右、分配的公平与正义等等思想逐渐成型。
而金雁在《十年沧桑》之后对东欧的关注其实逐步减少了,东欧也渐渐走出了中国公众的视野。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面对舆论对所谓东欧困境的渲染,金雁如鲠在喉,再赴东欧考察危机中的转型国家,归国后完成《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当然,其中既有金雁对东欧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各个层面的麻雀解剖,也少不了秦晖老吏判狱般的精深分析。
东欧与中国经济社会大有不同,其变革途径也许并不适合中国,但东欧诸国在变革之中经历的社会再造、政府改革、重塑公平等种种难题,也将是中国将来要面对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雁和秦晖对东欧转型的前瞻性研究的重要性应被我们更充分地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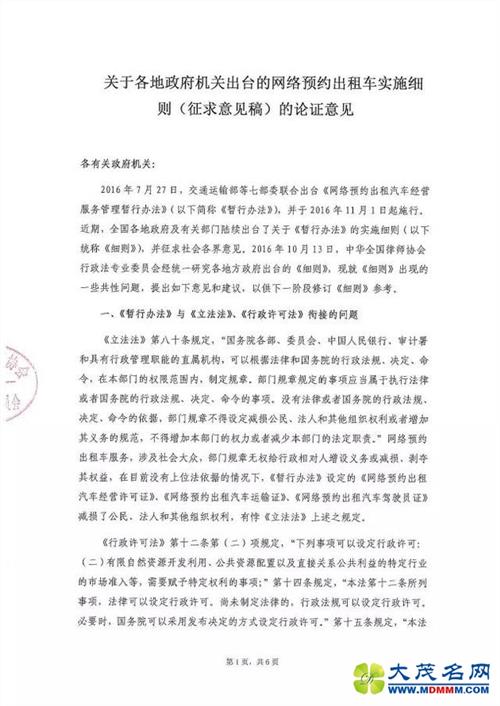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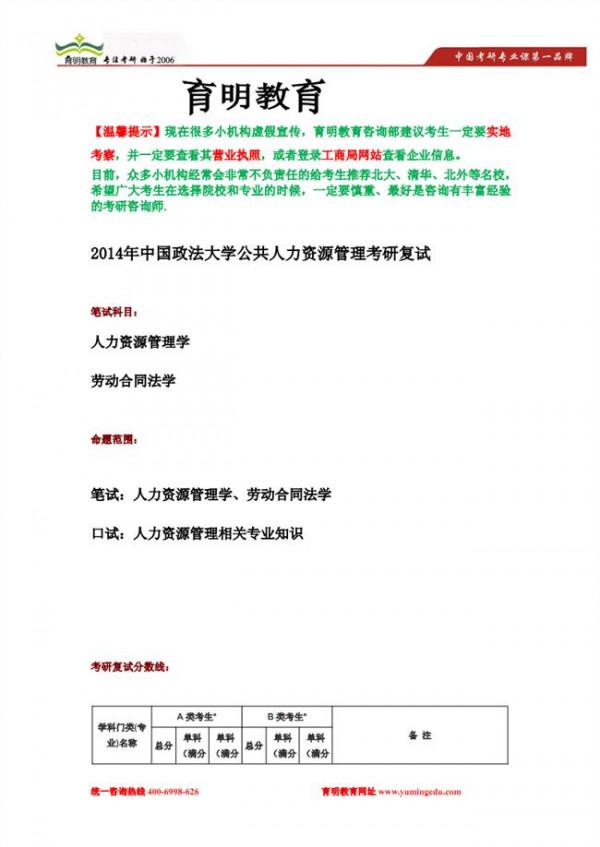







![>张树义政法大学 张树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https://pic.bilezu.com/upload/8/d6/8d631194cecdb6b313d6f328a9e58cf1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