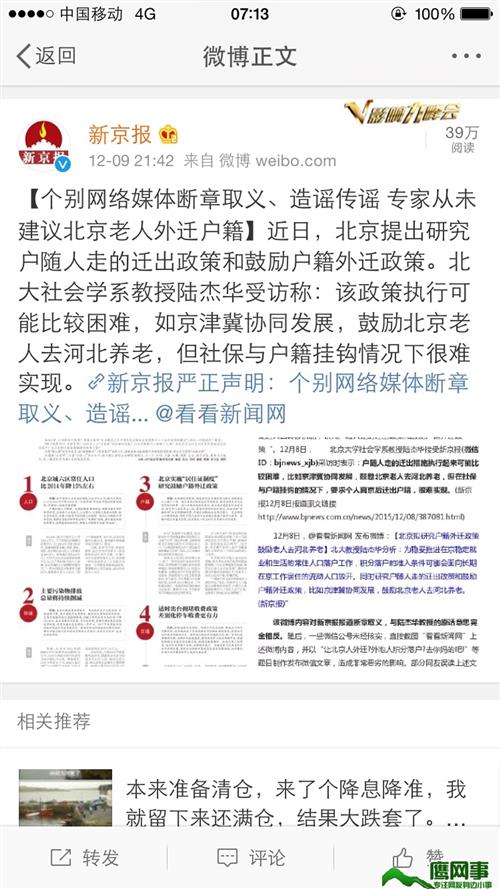(打包卖)雷洁琼学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上款信札贺卡一包
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生于1947年,1981-1984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1987年获硕士学位,1991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副主任。
他致力于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是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六五"与"七五"规划重点课题的主要成员之一。 跟雷洁琼先生学做人做事 作者:杨善华 唐红丽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是雷洁琼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后的第一个博士生,回顾与雷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给我最大的感触便是跟雷先生学做人学做事。
受益于雷先生严谨的学术风格 1983年,我第一次见到雷洁琼先生。当年7月,作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牵头成立的“五城市家庭研究”课题组的成员,我参加了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召开的关于该课题的学术讨论会。
这个课题是国家“六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雷洁琼先生是这个课题的学术指导。 在分组讨论时,其中一个议题是关于“城市家庭结构的趋势”,对城市家庭结构到底是怎样的,小组成员之间僵持不下。
此时,就有人提出,去听听雷先生的意见。我们一组几个人找到雷先生,雷先生当时就说,用资料说话、用数据说话,态度非常明确。 1987年,我硕士毕业,想考雷先生的博士。
雷先生是当时北大社会学系仅有的三个博导之一。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时的老师薛素珍是雷先生1946年回燕京大学当教授时的学生,薛老师听了我的想法后很支持,就给雷先生写了一封推荐信。考博之前我带着这封信去了雷先生家里,雷先生当时只说了一句话:“等考试完再说吧。
”后来,我考得还不错。 大概在1988年四五月份的时候,雷先生有一个“七五”国家重点项目的课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让王思斌通知我加入这个课题组。
王思斌是雷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已经是北大社会学系管教学的副主任。后来我们课题组几个成员就到雷先生家里开了一次会。她当时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可以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但她在红霞公寓的住所并不算宽敞,而且还十分简朴。
在这个课题上,雷先生给了我们很多调查方法和分析研究方向上的指导。在给我们作学术指导时,她总是鼓励多,很少批评,但一定是非常严格的。她要求问卷中的每一个问题都要经过论证才能确定,所有这些讨论都要经过她认可才能变成问卷。
在去6个地方作调查时,都是雷先生跟这些地方先联系好,或者雷先生为我们写介绍信。调查期间问卷怎么做,要注意哪些事项,雷先生都布置得很周密。这个课题其实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1990年,我博士毕业时候的博士论文也是基于这个课题,这也奠定了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之路,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农村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差不多30年了。
雷先生的学术风格很严谨,她坚持所有的观点和结论都要以实践调查和扎实的数据为基础。
1990年,我开始写毕业论文。因为时间安排的原因,我就写一章给雷先生送审一章。每次拿到送审后的稿子,雷先生都在我的稿子上写很多批注,有的地方还用铅笔画上记号。
当时我有些概念没有界定,雷先生看出来后就对我说,所有的学术论文无论大小概念都必须有严格的界定,否则就会造成歧义。这个问题,让我记了一辈子。那时候我们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见一次面,每次见面都要谈一个多小时。
这段经历现在想来真是难得。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在北大得了一个奖,一位美籍华人提供经费资助了论文出版,雷先生知道后很高兴,为我这本书写了序言。 跟雷先生学做人学做事 我自从跟了雷先生读博士之后,就是跟先生学做事学做人。
王思斌老师也说,雷先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跟雷先生学做人学做事,不徇私。 在雷先生的追悼会上,王思斌老师讲到:“我跟杨善华都没有占过雷先生的便宜,我们从来没有搭过她的便车。”相处这么多年,我们也从来没有私人的交往,见面谈的都是关于学术和工作上的事情。
要说帮雷先生办私事,我记得只有一次,那是雷先生一个亲戚到北大进修,她找我帮忙办事。事情完了之后,她半玩笑半认真地跟我说:“杨善华,我是不是该请你吃顿饭啊。
”我理解,这是帮她私人办事,所以她觉得应该向我表示她个人的谢意。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每个月会去看望她一次。我跟她讲最近的社会新闻,学校和系里最近发生的事情,她很感兴趣,听得非常专注,但很少发表评论。
她应该是有想法的,但是很少说出来。我们作调查回来,在农村看到什么现象,也会跟她汇报。 还有一个事情,让我记忆很深。1983年,我们在连云港开会时,当时一位江苏省的领导刚好去连云港视察,要和我们住同一个宾馆。
雷先生当时住在三楼唯一一间有空调的房间里。为了照顾省领导及其随行人员工作的方便,宾馆的负责人就跟负责会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沈崇麟老师商量,能不能把雷先生的房间调到二层,这样整个三层的房间可以集中给省领导及其随行人员使用。
因为二楼的房间没有空调,考虑到雷先生的身份和年龄,沈崇麟觉得很为难。但他硬着头皮跟雷先生说了之后,没想到雷先生很痛快就答应了换房。那年夏天连云港非常热,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不动都会浑身是汗,但是雷先生跟我们一样。
她平易近人和艰苦朴素的作风给参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雷先生并非对理论没有兴趣 我曾经跟雷先生讨论过一个问题。我说:“外面一些学者都说你只讲应用社会学,对社会学理论没有兴趣。”她听了后,就反问我:“谁说我对理论没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