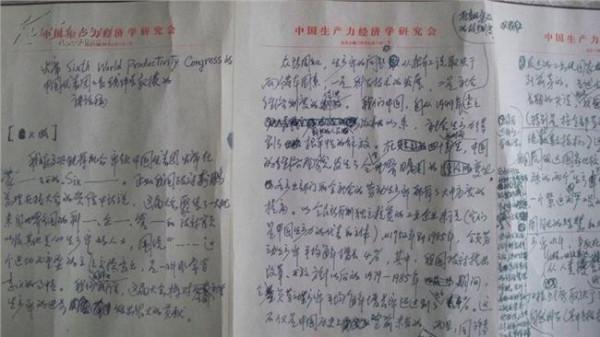雷洁琼的丈夫严景耀 雷洁琼严景耀的“政法”往事
今年同样80岁的许清教授,195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律系后,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他说:“当年我们年轻教师都去听严景耀先生讲课,他开的课程是资产阶级宪法,其中讲政党之间的斗争时,把复杂的政治关系讲得十分透彻,我们听的也很明白。他讲课没有讲稿和书,因为那时候没有教材,只有苏联的书。严先生从不拿讲稿,顺手拈来、谈笑风生,有时还举一些例子,十分生动,学生们很爱听,积极做笔记。但严先生的课不是主课,期末也不考试。”
当时学校并不让严景耀和雷洁琼讲什么法律主课,在老知识分子中间,像他们这样能讲课的不多,大多闲置起来,先改造思想去了。
今年89岁的方彦,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研室的第一任主任。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一建校他就在那工作。他年轻的时候和严景耀先生在一个教研室任教。他回忆说:“当时好像也没有什么课可以讲的,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严景耀教授提出讲课的事情,我们教研室就联合搞了一门课"世界概况"。严教授写苏联部分的讲义,因为他去过苏联。那稿子写的整整齐齐、规规矩矩的。严教授还讲过苏联宪法,讲课效果也不错。记得他从苏联考察回来,给我们做了一次报告,后来被批判说他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那时的人说话都是谨慎小心,说不准因为哪句话就会遭到批判,严景耀也没想到讲苏联的事情以后也会被说成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行为。
在国家法教研室工作的老师们都知道只要严先生来开会,都会带一些糖果、巧克力、饼干和好烟给大家享用。这些东西大家都没有见过,只有他们高级民主人士才有,一是他们出国带回来的,二是高级民主人士国家有特供,严先生总是分给大家享用,和同事们的关系很融洽。
雷洁琼:教授婚姻法课,法律的味道不浓
北京政法学院成立时雷洁琼和费青被任命副教务长,刘昂为教务长。教务处的事情大多由刘昂决定,他是党的老干部。后来苏联专家来了,教务的事情便由他们说了算。雷洁琼的社会活动虽多,但除了开会、出国,她都按时、按点来学校上班,还开设了婚姻法课程。
1952年,赵克俭(1954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在北京政法学院上学的时候,雷洁琼给他们讲授婚姻法。让他回忆60年前的情形,他还是想了几天才说:“我当时上学的时候,能够给我们讲课的老教授只有雷洁琼和严景耀,他们是高级民主人士,是统战对象,其他老教授都是所谓的旧式知识分子,所以靠边站了。
我当时是从北大调整过来的学生,1953年的上半年,雷洁琼和严景耀给我们上大课。严景耀讲国家法,雷洁琼讲婚姻法。我现在回想起来,雷洁琼讲婚姻法,法律的味道并不是很浓,因为她学的是社会学,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
解放初期社会学课停了,不让开这门课。那时候强调阶级斗争、阶级分析。这些课的阶级性不那么鲜明,而是讲人的共性的东西,如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凡是不讲阶级性的课都被打入冷宫。
雷洁琼到了北京政法学院就只得改为教授法律课了。雷教授的婚姻法课当时是在礼堂上的大课。她讲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婚姻自由的原则、一夫一妻制的原则、男女平等的原则,批判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批判封建礼教,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对于妇女的合法权益应该给予特殊照顾,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在她的讲课中很少有案例分析,因为她在这方面的实践很少,所以更多的是从促进社会进步、促进妇女解放的角度讲婚姻法。
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些其实是社会学的内容。她以前是有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学不让讲了,她就把社会学的内容放在了婚姻法里讲授。她讲得挺精彩,层次条理清楚,口齿清楚,嗓门也大,不愧是老专家。”
在谈起严景耀时,赵克俭回忆道:“严景耀教授在大礼堂也给我们上过课。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他是搞犯罪学和监狱学的。但是到了北京政法学院并没有让他开这两门课,只让他讲国家法。那个时候我国还没有宪法,只有共同纲领起着宪法的作用,唯一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他讲资产阶级宪法、讲苏维埃宪法,讲课效果很好,课堂时间掌握的非常准,分秒不差。他口才非常好,有时还穿插一些小故事,我们觉得老教授就是很有水平。可惜只有他们俩能出来讲课,别人都靠边站,改造好了再上台讲。那时没有人旷课,没人嫌课少、嫌法律的味道不浓。当时课程不多,民法刑法课请过中央党校、人民大学的教员来讲课。苏联专家讲过民法课,说几句话就要翻译一下,所以效果不太好。”
“文革”前的时候,大多数的学生都记得听过严景耀的课,交口称赞。他讲过的课有世界概况、资产阶级宪法、中国宪法、国际法等。
雷严二人相敬如宾
雷洁琼、严景耀夫妻二人的关系正像中国老话说的那样:“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再加上西方绅士的儒雅风度。
那时雷洁琼、严景耀夫妇住在南锣鼓巷,就是原来北京大学的四合院里面,院系调整后这个院子就归了北京政法学院所有。学校刚搬到学院路,住在城里的教授们都是坐公交车到当时算是郊区的学院路41号上班。那时这地方是荒郊野外,公交车也很少,交通十分不方便。
“后来学校有了一辆十个轱辘的美国大卡车作为班车,接送老教授们上下班,这样的情形差不多有一两年的时间。后来又有了一辆大鼻子斯格达大轿车,教授们上下班的状况就好多了。”吴昭明老师(1955年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留校,原党办主任,现年79岁)回忆这段时光道。
“我和雷严夫妇同住在南锣鼓巷的那个大杂院里,是多年的邻居。每天早晨雷洁琼、严景耀俩人总是形影不离地走出家门、一同去坐班车到学院路上班。”张效文老师(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留校任教,现已退休,现年79岁)说。到了学院路,“我记得有一次看见过严景耀先下车,给雷洁琼开车门,并作出一个手势,意思是LadyFirst,请雷洁琼先走,非常绅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夫妻关系,让我们颇为感慨。夫妻之间都那么彬彬有礼,实在难得。”薛梅卿教授(1954年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政法学任教,现年81岁)很有感触地说。
“每天早上到校园,严景耀一定把雷洁琼送到联合楼门口(雷洁琼的办公室在联合楼二层),二人相互摆摆手说再见。然后严景耀到自己的办公室(3号楼)上班,中午他们在6号楼250房间午休。下班的时间,严景耀也是去接雷洁琼一起坐班车回家。严景耀从来都是让雷洁琼走在前面,自己在后面走。”方彦老师还记得这些多年前的情景。
年轻的时候,为了事业,雷洁琼不要孩子,严景耀便尊重雷洁琼的决定。“我认为从这件事情看出严景耀十分尊重雷洁琼,这对于做丈夫的确是大度的表现。”薛梅卿教授这样说。“记得有一次雷洁琼和学生下基层搞运动,学生问她为什么没有孩子,雷洁琼笑着回答:"我们是先绝育,后结婚。"一点也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提出表现出不高兴。”张效文老师回忆起当年的事情。
张效文和雷洁琼做邻居好多年。他说:“从来没有听见过雷严二人在屋里吵嘴甚至大声说话。大院里只有雷老家有电话,她好多次帮我传呼电话。1976年1月严景耀先生脑溢血去世,雷洁琼先生好长时间情绪都缓不过来,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不出来。他们感情那么好,一下子一个人没有了,确实对雷洁琼打击太大了。”
雷严二人的“文革”岁月
“文革”开始,北京政法学院的校领导、老教授的日子都不好过。钱端升、刘靖西等校领导挨批斗、剃阴阳头,老教授们被关在5号楼,交代问题。雷洁琼、严景耀这次也没有因为他们是高级民主人士而逃脱。“文革”前学校对他们还是比较客气,但是到了“文革”时期就不论那套了,他们也属于反动学术权威。雷严二人在“文革”期间都写过交代材料,尤其是严景耀被认为有重大的历史问题。1930年代,严景耀研究过曾任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副典狱长。“文革”期间严景耀因此挨过批斗、剃过阴阳头,他们在南锣鼓巷的家也被抄过。
邹德慈(女,1954年毕业留校,后任司法部司法协助局局长,78岁)回忆当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雷洁琼的命运也开始转变。1969年林彪下达1号通令,全民备战,城里的人都要疏散到郊区和农村去。那年冬天,学校的教工都被疏散到延庆张家营镇的一个村子,住在老百姓家里达好几个月的时间,家属留在城里。
雷洁琼、严景耀也去了,雷洁琼和我还有军宣队的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同在一个炕上住。天已经很冷了,应该是穿棉衣的季节,雷洁琼没有棉袄穿,因为她的家给红卫兵抄了,贴了封条,不许雷洁琼、严景耀回家拿衣服。
去延庆的时候我们都穿着棉袄,雷严二人只穿着毛衣。在延庆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可做,我们就出去到镇上逛,而雷洁琼没有棉袄只能在炕上围着被子坐着。
她的家被封了,工资停发了,只给一点生活费,其实就是伙食费,还是很困难的。记得雷洁琼整天坐在炕上织线衣,就是把发的劳保线手套拆了,织线衣或者线裤,因为没钱买毛线。其实雷洁琼不是一个干家务活的人,所以她整天坐在炕上织线衣我觉得挺奇怪的,就问她,她操着广东口音说:"为了打发时间啦!
"她说是给她的外甥女的孩子织衣服。为什么把我们三个人安排在一个炕上住?就是为了监视雷洁琼。军宣队的那个女的还给我布置了任务,她不在的时候让我看着雷洁琼。
其实我是个"摘帽右派",也是被监视的对象,军宣队的那人监视我,再让我监视雷洁琼。记得隔好几天才让严景耀来看雷洁琼,军宣队的那人就让我暗自听他们都讲什么,然后向她汇报。
雷洁琼一直说话非常谨慎,从不发牢骚,他们就是互相问候,聊聊家常话,所以没有什么把柄可让军宣队抓住的。雷洁琼就是提出请求给她棉袄,后来天气太冷,军宣队就允许他们回家拿了棉衣穿。那时雷洁琼有60多岁了,也和我们一起去外面抬水,而且路也不算近。”
1971年北京政法学院的教工都去了安徽宿县五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雷洁琼、严景耀也被要求去了干校。“记得在去干校的火车上,我们这些年轻的教工安排了卧铺,而雷洁琼夫妇却被安排在硬座车厢,他们岁数已经不年轻了,但硬是坐到了安徽宿县,这是军宣队故意安排的,整他们两个人。到了干校还比较人道,让他们俩住在一个小茅屋里,其他人都是男女分开住集体宿舍。”邹德慈说。
孙炳珠教授(1952年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直到退休,81岁)说当年:“干校的时候我和雷洁琼教授一个连,我们连自己做饭,廉希圣、余书通等人烧火做饭,我和邹德慈俩人开了一个小卖部,为全连的人解决日常用品的问题。雷教授他们也去伙房打饭,然后回到小屋里吃。我记得曾问过雷教授是怎么保养身体的,她说她从来也没有刻意地保养或吃什么补药,就是长期喝牛奶,到了干校就买奶粉喝。那时候在干校净搞运动,整天让大家开会抓什么"5·16"分子,最后也没有揪出一个"5·16"来。所以干活的时间相对少一些,活不算太重。”
方彦老师追忆:“在干校的时候,雷洁琼、严景耀住的小屋又阴又潮,但他们从不发什么牢骚,也受得了。他们两人岁数比较大,干的活不算太重,也就是让他们到菜地捡捡菜叶子、间一间苗什么的。我的活是每天给大家发报纸,所以我不下地干活。1972年军宣队宣布上面的决定要解散北京政法学院,大家都各自找出路。雷洁琼、严景耀回到北京,去了北京大学教课,以后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她也没回来。”
在北京政法学院这20年,雷洁琼、严景耀经历了院系调整、经历了一切按照苏联专家的指示办事,经历了“反右”,后来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被打倒的遭遇,他们肯定有许多的委屈和痛苦憋在心里从不说出。
这20年间,他们两个人几乎没有再著书立说。早在1934年,严景耀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对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成果,但是过了50年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严景耀论文集》里面的文章截至1954年,这以后没有再看见严景耀有什么著作问世。一个最早研究中国犯罪问题的学者,后来却没有什么建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