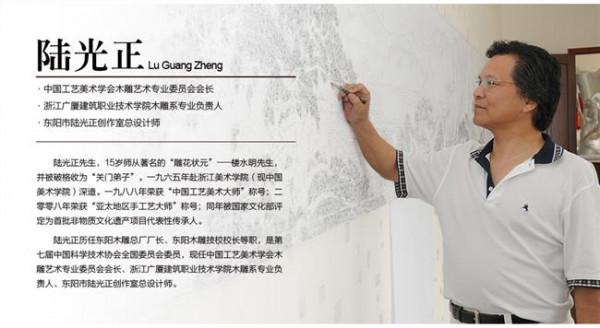陆幼青的最后一天 陆幼青:写到生命最后一刻 我要走了
8月14日,陆幼青的《死亡日记》开始在本报连载。读着这些平缓、真实的文字,我们快乐着他的快乐、痛苦着他的痛苦,然而我们仍是旁观者。直到走进他的生活,看到他是如何留下这些文字的;直到面对他的亲人,听他们诉说陪伴"死亡"的每一个日子,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在死亡面前要活得有尊严,活得有价值是多么困难!
37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年龄,而10月23日陆幼青的37岁生日,却带着更多的意味:这之前,他带着"为自己买第二套房子"的心情,亲手给自己挑选了一块墓地;这一天,他写下了2000字的日记《最后的生日》,这也是他《死亡日记》连载的最后一篇;他在日记里写道:"最后一个生日来了,我,要走了。人生总有那么多的节骨眼,当然受不了,我实在不敢在这样的时刻稍加逗留,更不敢深入地去想一些事。因为,心,会碎成片片……"
8月3日,陆幼青写第一篇《死亡日记》那天,是他10岁女儿的生日。两个多月里,这个患了绝症却依然活得精彩热烈的陆幼青,用他的笔,与步步紧逼的死神对视。如今,他的病情已经开始迅速蔓延:他的脖子、前胸已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肿瘤,有的已经有馒头大,并不时溃破;10月15日,他还能支撑着为自己选定墓地,而一周后他连坐卧这样的简单动作都需要妻子的帮助;他最后阶段的日记,都是先用录音机录下口述,再由妻子整理成文字。
推荐阅读:陆幼青给女儿写的择偶家训
陆幼青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就像他自己在告别读者和网友时说的:"我自己知道,已经到了需要向人生说再见的时候了……"推荐阅读:陆幼青离别后的10小时
陆幼青的脖子、前胸、腰腹已经满是大大小小的肿瘤,每天都有肿瘤溃破,流出的液体散发出难闻的味道
有很多次,我怎么也写不下去了,身体的痛楚是如此地强烈,我必须不停地转换姿势,而每换一个姿势,身体上各种部位的疼痛要持续十来分钟才能平静,十来分钟过后我又觉得我需要下一次新的挪动来让我的身体感觉更舒服一点。———摘自《死亡日记》
8月中旬,记者第一次采访陆幼青和他的《死亡日记》,那时候他虽然瘦得厉害,但是精神不错,每天6点就会起床写日记。
9月中旬,记者到上海采访,陆幼青说自己的身体已经比以前差了,自己每天花在写作上的三四个小时,是苦苦等来的一天中最愉快、心智心态也最正常的时刻。
10月15日,就是陆幼青为自己定下墓地那天,上海传过来的照片让人有些不忍心看。时牧言在电话里说,陆幼青的身体恶化得很快。她前一天天刚看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8月底来拍的那期节目,里面的丈夫比现在的状况好多了,那时他上下楼梯都不让人扶,现在如果一天不叫他,他也许会迷迷糊糊地在沙发里坐上一天。
陆幼青当然也感受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向出版社提出了将《死亡日记》提前出版的希望。华艺出版社副社长金丽红对记者说,她到上海取书稿的时候看到陆幼青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连吃饭都比以前困难了。
陆幼青的最后阶段,脖子、前胸、腰腹已经满是大大小小的肿瘤,每天都有肿瘤溃破,流出的液体散发出难闻的味道。麻醉剂对疼痛的减缓作用也越来越小,原来能用72小时的药,到后来过了36个小时就失效了。家里的阿姨每次和邻居说起这事都要哭,说先生看着太可怜了,要是换成别人变成那个样子真的就不活了,可他一点都不厌世,还一样和妻子女儿说说笑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伴随着肿瘤疯狂生长的,还有饥饿的感觉。由于癌细胞的生长迅速,夺走了大量能量,陆幼青经常觉得饿,而长时间的浮肿已使他的喉管及食道严重变形,吃一点东西就要呛出来。要想吃饭只有等浮肿消退,这一等长是6个小时,短的也要3个小时,陆幼青便经常在这种病态的饥饿中煎熬着。
但即使是这样,他也要坚持着写日记。满脖子的肿瘤已使颈椎不堪重荷,写不了多久头就疼得不得了。写1小时的日记,过后要按摩几个小时。后来他连电脑也敲不了了,就躺在床上,自己口述,用录音机录下来。妻子心疼地劝他,他还是那句话,这日记是要写到生命最后一刻的。
陆幼青的妻子说,原来我们对生活的想法很简单,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早晨吃了早饭就去上班,黄昏的时候下班回家,一边做家务一边聊天,孩子则在一旁安安静静地做功课
人生如一个巨大的幼儿园,早上,上帝把玩具和好吃的给你,而到了傍晚,上帝又把这一切收了回去,让你体会得而复失的痛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得而复失的痛楚远远大于得到的快乐。这就是死亡的痛苦,我只不过是那个幼儿园的早退者。———摘自《死亡日记》
陆幼青,37岁,上海人。他32岁以前的人生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1985年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上海某局职工大学培训中心任职;工作4年后下海,与朋友合作开办广告公司,并很快在广告界打出了一片自己的天空。
此时的他,事业如意,婚姻美满,女儿可爱。他的妻子,也是大学同学的时牧言说:"原来我们对生活的想法很简单,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早晨吃了早饭就去上班,黄昏的时候下班回家,一边做家务一边聊天,孩子则在一旁安安静静地做功课。"
然而生活并不像人想得那么简单。1994年圣诞节后的那天,陆幼青开始觉得胃疼,吃不下东西,开始他还以为只是老毛病胃病又犯了,哪知到医院一检查,化验单上写着的竟是"胃癌晚期"几个字!医生写的是英文,但是陆幼青和妻子还是一眼就看明白了。
正处在人生黄金阶段的陆幼青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得上绝症,而且还是晚期,而那时他的女儿还只有4岁!和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样,刚开始的惊惶过去之后,生性要强的陆幼青开始了与死神的搏斗。检查结果出来后第10天他便进行了手术,术前他希望能尽可能使用半身麻醉,以免影响以后大脑思考;手术后的10天10夜,他强忍着疼痛一声不吭;他的胃被切除了4/5,但是为了尽快康复,他强迫自己拼命多吃东西;手术后3个多月他就又开始了工作。
1998年夏天,陆幼青再次被确诊为癌症,而且是恶性腮腺肿瘤。第二次手术后医生安排了24次化疗,做到第6次的时候,由于化疗对身体的影响太大,陆幼青拒绝再接受化疗,再次转向中医求治。
那段时间是陆幼青求医最辛苦的日子,不论是大医院的医生,还是民间有点名气的大夫,哪怕对方只治好过一个病人,无论路途多远,他都会找上门去。其间还有很多热心的朋友介绍了许多偏方或者特殊疗法,陆幼青几乎都尝试过,为的只是抓住哪怕万分之一的希望。
然而,这万分之一的希望也破灭了。第二次手术后只半年,陆幼青发现脖子上长出了肿块,到医院一检查,肿瘤再次复发!这次的肿瘤来势汹汹,开始疯狂地吞噬他健康的肌体,而陆幼青却没再像以前那样到医院治疗,他选择了和妻子女儿在一起,享受着久违的平静生活,同时开始写《死亡日记》,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说如果没有这部《死亡日记》,陆幼青的故事也许只会局限于一个普通肿瘤患者艰苦求医的经历;也正是这部《死亡日记》,使得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开始正视以前所讳言的"死亡",开始思考"死亡"和"尊严"的关系,甚至可能的是,改变某种在脑海里存在已久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日记里那些生与死的纠缠、努力和放弃的转变、世俗与现代的交替,把许多平常人只能藏着掖着的话呼啦啦地就倒了出来,颇有种"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感觉。
看到一个有责任心的、追求上进的、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被癌症折磨的全过程,妻子终于同意丈夫放弃治疗的想法
我的眼泪快流出来了,但还是克制住了。这种心灵的暗潮来时几乎毫无预兆,但每次都几乎要用尽我全部的毅力。我曾经在海南凯莱大酒店的大堂里难以自持,我觉得自己是在退房,也是在向上帝退还我曾经向他预约过的、祈求过的下半生的幸福时光,以我的境遇,我如何能做到平静地向美如天堂的亚龙湾,向所有人世间世俗的快乐说再见呢?我用报纸遮住脸,让泪尽情地流,却希望别人以为我在找飞机航班。———摘自《死亡日记》
在为期不断的采访过程中,陆幼青妻子时牧言的笑容给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的笑容很灿烂,没有半点病人家属而且是癌症病人家属的悲痛和手足无措。她说,自己还能够笑是因为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折磨后,她和陆幼青已经把生死的问题看淡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办主任王焰自大学时代便一直和陆幼青夫妇保持来往。她说在大学里陆幼青便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喜欢看书,也能为喜爱的电影"逃课",在旁人看来很有生活情趣,而且和那些嘴上吵着闹着要成功的人不一样,他属于能做出点事情的那种人。
时牧言则说她和陆幼青对生活的要求比较高,是个"书虫",原来她家里有很多书,谈恋爱的时候他一来就到她家书房看书,一看就是半天。她还曾拿他来是看书还是看她开过玩笑。结婚后夫妻俩最喜欢的就是旅游,因为欣赏武夷山的灵秀,前前后后去了不下5次。
但是俩人跑得更多的路还是为了求医。时牧言形容陆幼青刚开始求医的情形说,每次都是怀着哪怕万分之一的希望去,但是每次都是带着百分之百的失望回来,因为医生要么当面就说,这个病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要么还怪陆幼青:"你开什么刀啊,你要不开刀的话找我就没有问题了。
"而这时的陆幼青居然还对医生笑着说:"那您就死马当成活马医吧。"时牧言在一旁听着心像刀绞,她渐渐明白为什么丈夫每次看了医生回来情绪会那么低落了,因为每次求医都在重复着"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过程,把治愈的信心抽丝剥茧般地一点一点变小。这对一个病人来说,的确是最残酷的。
陆幼青第二次手术之后的24次化疗只进行了6次,他觉得化疗对身体的损害太大。而时牧言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原本精神饱满的丈夫,几次化疗之后便委顿得像只猫一样,每天只能喝点稀饭吃点酱菜,人也瘦得只剩了骨架子,便同意了他的想法。
更令人恐怖的还是癌症对人意志的摧残。陆幼青复发的是腮腺肿瘤,属于外部肿瘤。瘤体长在脖颈间,越来越大,长到一定时候还会溃破,流出味道腥臭的液体,弄得人痛苦不堪。陆幼青就在这种痛苦中挣扎了很久,一方面他一直是个积极向上并且要求生活质量的人,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自己被病情折腾得疲惫不堪的精神和肉体。
他甚至可以眼看着一天天变大的瘤体逐渐挤压着自己的生命,什么才华、事业、友情、生活的情趣,等等等等,在这肿瘤的面前都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今年初,夫妻俩第一次完全没有遮掩地谈到病情。时牧言真正理解了他的感受:他要不断给自己万一奇迹发生的希望,又要不断受到无力回天的打击;他希望自己还能像平常人那样生活,但不断长大的肿瘤甚至不能让他出门参加同学聚会;这种情况下再逼他到医院做检查,检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呢,无非是逼着他再次确认这么一个事实———病情今天发展到了肺,明天发展到了肝,可又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去控制它,那这样的检查就太残酷也太没有实际意义了。
《死亡日记》刚刚开始连载的时候,网上网下曾为陆幼青放弃上医院"是怯懦还是无畏"吵得不可开交,有的报纸甚至还以此为题展开了大讨论。对此陆幼青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只说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病情,不了解这是在经历过5年多艰难的治疗之后自己做出判断的决定,在这5年中他吃足了苦头,可还是没能等到奇迹的发生。这与那些刚开始就放弃的情况完全不同。
现在看来,当时有关"怯懦还是无畏"的争论实际上没什么必要。如果陆幼青最后几个月一直坚持治疗,大概谁也无可指责了,可是那样的话他也许真的只是带着痛苦,带着遗憾,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眷恋离去的,那样的结果,比今天好吗?
就像时牧言在谈到为什么会同意丈夫放弃治疗时说的,她陪着陆幼青走过了这么多年,看到了一个有责任心的、追求上进的、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被癌症折磨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和绝望。当他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再强迫他去做什么事情都显得很残酷;如果生命的终结是逃脱不了的,那么最后时刻让他坚持打针吃药是不是就真的比精神上的关怀和心理上的抚慰来得重要呢?
《死亡日记》就像一扇门,它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走完人生里程的肿瘤患者的内心世界
在中国,得癌症是最不幸的。如果他是一个官员,仕途会就此打住,组织部门开始着手调查新的人选,而有关人士开始动作;如果,他是一个商人,他的信用会立刻贬值,签过的合同也会变得模糊;如果他是一个学生,会有人放弃学业;甚至夫妻之间也有把自己的未来重新掐算一遍的。极大多数的癌症患者都保留了清醒的意志,身边的种种变化很少能瞒过他的眼睛,这时候心中的滋味真是太……———摘自《死亡日记》
陆幼青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了一部令人感悟颇多的《死亡日记》,还在于他是个得了癌症、开了两次刀、治了五六年还没治好干脆就不治了的病人。而他的《死亡日记》,更写出了许多健康人不容易体会的癌症病人的心理感受。
在中国人看来,癌症就是不治之症,尽管有那么几种病比癌症更凶险,但它们在国人的心中只不过是偶然。在中国,癌症患者当然是不幸的,这种不幸已经不是仅仅体现在健康的层次上,更有陆幼青调侃过的无法升迁,无法再把自己当成正常人的种种现象,这是因为"癌症把死亡的过程展现得太过清晰和从容,使人将对死亡的恐惧等同了对癌症的恐惧。这种恐惧可以极大地削弱患者面对病情时的信心,有时甚至会抵消治疗的作用"。
陆幼青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在上海肿瘤医院做第二次手术时,隔壁病房收治了一个病人,其体魄之强健让人以为他是刚从运动场上下来的。那人三天前才被确诊为肺癌,陆幼青去探望他,因为他听说那位病人进了医院就没说过话。去了几次,还是没有听到他说话。两个星期后,这位病人就死了,几乎创了上海肿瘤医院的一个纪录。
还有什么例子比这更能让人体会到这种力量的可怕呢?
更让陆幼青耿耿于怀的,还是对癌症的治疗:
"……我们国家的医院似乎是在以一种流水线的模式进行癌症治疗:手术———化疗或放疗———请让出床位。
手术一般是出色的,原因是熟能生巧,中国的外科医生不比外国差,老外那个工作量根本不值一谈,中国的医生一年要在病人身上划多少刀?
我接受过几次化疗,但在我自己找到的医学书里清楚地写着,化疗对我的病的有效率只有10%,想想也是,把自己的全身灌满毒药,只因为身体里有个地方长了个病灶,从常理来推测也是一件低效率的事,我果断地把另一半化疗处方扔了。而我同室的8个病友,全部在按质按量完成了化疗一年内死去……"
陆幼青当然不是在否定现行的对癌症的治疗方法,他只不过指出了目前我国在治疗癌症方面的一些不足。西方国家对治疗癌症也普遍采取的是放疗和化疗,为什么效果要好得多,癌症的复发率也要低得多呢?一些医学专家对此给出了几个答案:一是药物对不同人种作用的差异。
我国的放化疗药物几乎全部是依照进口药物生产的,是人家的科研成果,西方人能抵抗这类药物的毒副作用,而中国人就不见得;二是医疗基础条件的差异。由于人口的原因,西方的医院和医生根本不可能面对那么多的病人,这就给了医生根据个体差异进行治疗的可能性,而我国在放化疗配合治疗方面都是以群体病人来进行的;三是辅助恢复手段的差异,它包括病人身体和心理的同步恢复。
在记者看来,也许最后一条是最难做到的。因为在西方,癌症就是一种重病而已,并不带有任何人文上的含义,可在中国不一样。癌症就等于死亡,得了癌症就差不多该算成个死人了,没人会和一个死人争什么,当然你也别和别人争什么。那你还有什么事情做吗?没有没有,只有等死了!
在陆幼青笔下,这种感受令人窒息:"……岗位没有了,老单位的领导会安慰你,再休息休息,有困难提出来;家庭生活变了,子女们倒是比以前听话了,但你再看不到他们当着你的面使小性子。我的一个同病相怜的好友有一次对我抱怨,过去他们的夫妻生活堪称完美,而现在呢,只要他不明说,这事就永远不会发生,好不容易有那么一次,妻子每过一分钟就会轻声地说:‘当心,别累着。’……"
从来没有见到过有肿瘤患者类似的表达,他们也许没来得及就被这种折磨吞噬掉了。从这个角度上说,《死亡日记》就像一扇门,它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让更多的健康人看到了一个希望按照自己方式走完人生里程的肿瘤患者的内心世界。这个人虽然要去了,但是那扇门却已经开了。
一个中学生说,《死亡日记》该被收进教科书,不是语文,而是政治,因为它能让人懂得珍惜生活
……我曾经试着写了十来篇给女儿日后阅读的文字,谈学习做人什么的,这是十岁的她还理解不了的,但写着写着,觉得写的东西像她教室里黑板报上的东西,一是爱女心切,难免说教;二是世事如烟,等她真正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谁知道她的电脑主频是多少?3.5的小盘认不认?WORD2000能打开吗?———摘自《死亡日记》
几个月的采访时间里,有很多反差强烈的场面让人记忆深刻。
先是在上海红松路陆幼青家中与他的第一次见面,真的让人大吃一惊:这是陆幼青吗?!印象中的他都是那个在报纸上在电视里那个容貌清癯,经常在思考着什么的面孔,而眼前他的脸却苍白地浮肿着,五官被挤得失去了应有的神采,整个面孔看上去比以前大了一倍。
那次是因为呼啸上海的台风"桑美",对常人并无所谓的低压让陆幼青难受得喘不过气来,脸也开始浮肿。可即使是这样,在他当天的日记《我心深处台风吹过》里也没有见他有什么抱怨,相反还打趣自己的脸被台风变成了"充气娃娃"。
就在那天,当我们坐在陆家宽敞的客厅里说话的时候,他10岁的女儿陆天又一直在旁边玩她的玩具。当时大人们讲了很多,像"死亡"、"癌症"这些词很轻松就出来了,过了一会我才意识到屋子里还有个孩子。余光里看去,小天又似乎没什么感觉,依然在被台风遮挡了多日的明媚阳光里专心致志地玩着游戏。
尽管当时我已经看到了那期《实话实说》,知道小天又实际上已经清楚了父亲的病情,但我还是忍不住担心,这么早让孩子知道这些对成人来说尚显沉重的话题,会不会对她成长不利?
陆幼青夫妇俩对这个问题也考虑过很多次,这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9岁就知道上网给家里的宠物小狗找"男朋友";这又是个非常敏感的孩子,上次同学为陆幼青组织了一次聚会,回来时大人还没怎么,她却一个人跑到自己房间里哭。
对这样一个孩子,想瞒也是瞒不住的。就在今年初夫妻俩决定不再到医院去之后,时牧言便把事情对天又讲了。她没有提"死亡"这种冷冰冰的字眼,只是告诉女儿,父亲得了很重的病,也许以后只有妈妈和她一起生活,不过妈妈保证以后的日子和父亲在的时候一样好。
"当时女儿就说她恨我。"时牧言对记者说,"她恨我为什么要让她知道这样的事。我知道,她心里很害怕,是那种孩子内心对失去父亲的天然的恐惧。"父亲的日记出来后,天又也会上网去看,一般不会说什么。而作为一位父亲,陆幼青则有太多的话要对女儿说。他在日记里用调侃的语气给女儿讲恋爱,讲留学,讲没有朋友的男人不能要,朋友太多的男人不能嫁。他说,希望女儿看这些文字时,16岁有16岁的心情,26岁有26岁的感受。
10月14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播出了采访陆幼青的节目,其中有很多以前陆家自拍的家庭生活录像片段,里面的陆幼青做鬼脸,和天又在街上嬉笑,还孩子气地在妻子头上比了个"V"。里面的人,笑靥如花。而真实生活中的他,病情已经发展到连字都不能写了。这让人想起一个中学生说的,《死亡日记》该被收进教科书,不是语文,而是政治,因为它能让人懂得珍惜生活。
他说,即使他死在癌症手里,也没有被它打败,因为他是在和癌症对抗的过程中一步步改变了生活条件和状况,包括买车、买房,以及让妻子女儿过得比以前好
我下车,走几步,突然感受到那山野之间的那种清凉,纯静的空气,秋日的阳光,和一股很神秘的桂花香向我袭来,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的情感也猛地撞向我的心头,我感受到了常人无法感受的那种深彻骨髓的悲哀:在如此一个有阳光,有青草气味的早晨,我不是来游玩的,不是来带着女儿在这片草地上奔跑的,我只是来为自己的生命找一个墓地。———摘自《死亡日记》
从8月《死亡日记》开始进入公众视野那一天起,陆幼青给人的印象便一如他的文字,平静,深刻,似乎对什么都想明白了,也似乎什么都看清楚了。采访的大半时间里,他都像那张天天在专栏上与读者见面的那张照片一样,不动声色地谈论自己,谈论人生。问他是否一直都是这么平静,他没有正对这个问题,只说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终于有一天问起时牧言:"陆幼青就真的那么平静,一点别的情绪都没有?"时牧言沉默了片刻说:"你还记得吗,你第一次来采访的时候他就对我发过脾气。"
她的话提醒了我。第一次采访陆幼青时,正逢台风"桑美"登陆,事先本已和陆幼青及妻子时牧言约好,但是后来天气突变,采访的时间改在了第二天下午。第二天记者在瓢泼大雨中如约前往,快下高架桥的时候给陆家打了个电话,哪知电话里时牧言为难地说陆幼青身体不适,无法接受采访。得知我已经快到她家时,时牧言说再和陆幼青商量一下,后来陆幼青就发了脾气。
时牧言说,那天天气突变,陆幼青脸肿得吓人,呼吸也憋得厉害,后来甚至不让她离开半步,就这么一直看着她。因为北青报是他最喜欢的报纸,也是唯一一家同步刊发《死亡日记》的报纸,他一直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让北青报的读者见到,但那天实在难受极了,有一半也是在发自己的脾气,他一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无论自己的举止还是形象,但事实上病情的发展已经使他无法再顾及这些了,这让他觉得十分无奈、着急和难过。
时牧言说,陆幼青如果不是太追求完美,也许不会那么痛苦;他要是能把这种痛苦都说出来,也许心里会好受很多。
10月15日,陆幼青在妻子的搀扶下来到上海一处叫"福寿园"的公墓,为自己选择了一块墓地。而几天后的10月23日便是他第37个生日,也是最后一个生日。那天的照片上,陆幼青在久违的阳光里闭目坐着,身旁是烂漫的鲜花和一块块墓碑。在生日前一周为自己选择墓地,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时牧言看了那天的日记后说:"开始我也很平静,但是真的看到那些墓碑时,我突然被深深的难过包围住,他实在是太年轻了啊!"
然而在回答是否有种被癌症打败了的感觉时,陆幼青摇头否认。他告诉我,当他第一次发病时,一家三口还挤在一处很小的房子里,各方面条件还不如现在。他真的是在和癌症对抗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到现在的,包括买车、买房,让妻子女儿过得比以前好。如果有那种被打败的感觉,他早就支撑不住了。癌症能夺走的,最多是他的生命,但他还有快乐,还有亲人,以及一本从死神手里抢出来的《死亡日记》。他说,他对最后的结果是真正的平静。
而时牧言则说,死亡这个结果对她而言,没有什么痛苦的;真正最痛苦的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爱的人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以及那种焦急、难受又束手无策混杂其中的情绪。她说她哭过,而且不止一次,而陆幼青对自己太自律,很少将自己心中的情绪发泄出来。
"如果,一切都结束了,我希望能从这种痛苦的煎熬中摆脱出来,和女儿一起过和别人一样的生活。就是那种正常人家的日子,平平安安普普通通的日子。我想找个自由一点的职业,可以好好陪陪女儿,交一些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的朋友,或许还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看看书,再把这些年的感受写下来,然后让生活完全恢复平静。"
陆幼青就要走了,他在走之前给我们留下了一本书,一种对待生命的方式,以及可能包括你我在内的许许多多已经无暇顾及闲暇乐趣的人的思考。网站上有这么一篇帖子颇有见地:"……陆先生在不多的岁月里,却要每天去写文章,让大家能认识生命的意义,启迪大家做人的道理。
还有更多的帖子,说是陆先生使他们认识了人生,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其实我们并非无知,而是在忙碌到极点的日子里忽略了生命的珍贵和生活的快乐!生命的意义本不是几句话、一本书就能说清的,陆先生值得我们去尊敬,但生命的意义,人生观却要我们每个人自己去理解,去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