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贺卫方 许章润 许纪霖 季卫东等:革命、立宪与国家理性
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办的现代中国与世界深度论坛,旨在就当代中国与世界重大的学术、思想、政治与社会的前沿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每次邀请一位国内外著名学者作主题演讲,随后围绕主题进行自由的、开放的多维度讨论。
首届论坛的主题为“革命、立宪与国家理性:重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议之下,最近学界和读书界出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热。
如何阅读和理解该书,如何深入阐释革命、立宪与国家理性的关系,本论坛2013年4月2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行,上午由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作主题演讲(参见共识网:许章润: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看优良政体的形成)下午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的法学、政治学、历史学者共同讨论,深入研讨。现在根据录音整理出发言稿,已经发言者审阅。
专题研讨1:革命与立宪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讨论的时间开始了。今天上午,许章润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大开大合的主题报告,可以讨论的问题非常多,我发现下午来的同学和上午来的同学差不多,这说明今天的论坛保持了吸引力。我们非常高兴,下午有幸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著名学者季卫东教授,由他先做一个开场白和评论,然后大家就上午的演讲和相关的议题展开自由讨论。下面,有请季卫东教授,大家欢迎。
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感谢许纪霖教授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跟各方面朋友交流的机会。记得我刚刚回到上海的时候,大概刚到还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纪霖兄就邀请我到这里来跟大家做过一次交流,当时讨论的是启蒙问题。
章润兄是我在中国法学界非常尊重的一位朋友。今天上午他的主题报告,我本是想来听的,只是有些行政上的庶务缠绕,最后没来成,非常遗憾。不过我事先拜读过他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访谈,还有他赠送给我的《国家理性》,这本书写得很精彩。
所以我大致可以想象章润兄所讲的内容。因为没有听到上午的演说,反而有一个好处,可以提出一些不同的视点。虽然也可能有重叠的地方,但总还是可以另外抛砖引玉以供讨论。
最近《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非常热,大家都在谈,都在议论。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更多的是在分析旧制度如何导致大革命,对大革命本身倒是没有做详尽的分析。那么旧制度如何促成大革命,根据我的解读,不一定完全准确,他主要谈了这么一个问题:如何防止在不经意间引起社会崩溃。
在当时的法国以及整个西欧,绝对王政确立之后,中央集权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各个国家都有这个倾向。在法国,最突出地表现为行政上的专制主义,或者说行政集权。而贵族在这个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被剥夺了在地方的统治权、行政权。
但是法国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些被剥夺了地方行政权的贵族没有被组织到全国的政治过程中去,他没有获得在全国政治活动中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心怀不满,却又被边缘化,甚至有学者说,这是贵族的民主化。
他们分散成这样一群人:他们既不能以人民的名义来反对国王,因为他们是贵族;也不能对抗人民来帮助国王行使权力。他们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状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贵族变得既不可爱,也不可怕,很像我们今天的地方官僚。
这样一个状况,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说,贵族的政治功能遭到了破坏,国王的统治基础被动摇了,一个原有的领导阶级被打碎了。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状况下,没有形成一个新的、立足于其他社会基础的领导阶级,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状况。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极端的行政上的专制主义造成了权力被赤裸裸地行使,引起了民众和贵族的不满。那么谁来为这种不满进行辩护呢?在法国,主要是文人和学者,尤其是文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代表了社会的良心、社会批判的声音,同时俨然成为一个虚拟的、人民想象中的领导阶级,成为已经残缺的领导阶级的替代物。
而他们本人有理念,却缺乏统治手段和平衡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满在不断地激化、累积,而平衡的力量已经失去了,最终导致一种不断激进化的话语成为社会中新的权力。
在这个由话语和符号构成的奇特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导致革命的连锁反应。而这种反应是出乎意料的。首先是贵族的抵抗,然后是士绅阶级开明派成为抵抗的中心,最后引起小市民和农民的造反。
整个国家陷入到革命的浪潮之中。关于这种机制,在弗朗索瓦·傅勒所写的两百年之后反思法国革命的书中有所触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理解的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前提条件。
反过来与它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英国和美国。
英国也确实也进入了绝对王政的时代,但是在君主的统治下,在比较早的时期就通过了“大宪章”,实现了一种身份制的自由。通过这样一种自由,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对这个自由进行控制的法治秩序的确立,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的结构、新的领导阶级、新的秩序。
“大宪章”确立了自由权的保障,就以法治主义限制了权力,成为改造权力的一个重要形式。同时法治又成为弥补权力正当性的一个权威体系。由此,法治耦合了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身份制自由使得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客观上处在一种分而治之的状态下,他们互相之间可能有沟通,但是每一个部分都有单独的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冲击的贵族和士绅阶层被纳入到了新的体制中,他们在服从君主的同时,也自主地管理地方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一种地方自治的机制。
而在国家层面,身份制自由使得教会里的圣职者、原来的贵族和骑士、新的市民阶层的代表构成了一种身份制的议会。通过这种议会与君主进行谈判和妥协,议会的功能逐步强化,议会的权威逐步提高。
最后使得绝对君主只能在议会中享有主权。显然,这是立宪主义的制度安排。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法律家推动的革命,它避免了法国的流血和动荡,所以我们称之为“光荣革命”。虽然我们过去一直批判这种革命的不彻底性、妥协性,但是回过头来看,当我们反思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动荡和破坏性,人们会觉得这种英国式革命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
在讨论革命与立宪的时候,无论法国,还是德国,都发挥着反面教师的作用。虽然德国人很理性,与法国有些不一样,但是也有类似的地方。法国是文人成为革命的推手,而德国1848年的3月革命,是教授起了主导作用,最后也遭受挫折。
无论文人还是教授,他们都对社会的启蒙曾经发生过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两场革命都遭受了挫折。而英、美两国都是法律家推动的革命,他们主要通过立宪主义的制度安排,在破坏旧制度的同时,让一种新的权威、制度框架、领导阶级逐步形成。这是两种革命类型带来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结合这个历史背景,我们讨论本节的专题“革命和立宪”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跳出这样的历史事实来看,当革命产生时,原来的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都开始分崩离析,而这个过程必然会伴随着价值观的多元化。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加强了这个趋势。多元化、民主化,是现代化过程中非常明显的倾向。
最重要的是,不同的价值观出现了互相对立,甚至发生冲突。因此,如何处理多元化的价值观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在考虑社会转型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考虑大革命的原因的时候必须追问的条件。无论在哪个国家,特别是西欧几个国家,在大革命前夜都存在着无法相互还原、也难以互相比较的根本不同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当时那样的背景下采取某种宗教的或者道德的标准,来为另外一种宗教或者道德提供正当性根据。
那么关于正义的实质性价值判断,都是具有独善性的,都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如果没有一种分而治之的安排,就很容易导致矛盾和对抗,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引起大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立宪、自由主义的宪政安排,就是以价值观的多元化为前提,正视存在的事实差异,进而探讨如何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自由,使不同的价值观能够和平共处。立宪主义给出的答案或者制度设计,就是公私两分法。
在私人领域,充分承认价值观的多元性,一个公民可以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道德标准、哲学观点、善恶观,在思想上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在公共领域,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价值取向相对化,必须重视反思理性,必须通过民主程序参与公共事务的决定,把自己的行为统一于法律。
前者就是解放,后者便是规训、纪律,这就是现代化的两个过程。没有纪律的解放,可能就会带来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政府本身不能追求特定的善,而应该尽量保持价值的中立。
只有这样,政府才能超然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价值观之上,来保障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的平等的自由,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把已经多元化的价值观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社会的公共空间进行有效的整合。
当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整合方式,它保证价值观的多元性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有这样一种整合机制。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英国的方式是通过地方自治,把旧的精英纳入到新的体制,其中法律起到了重要作用。法律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使得它能够扮演国家中立性的担保物角色。
不过,法治确立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有推手、担纲者,才能真正得到实施。这就是英美革命中,律师、法官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他们本身除了为了正义的价值理念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平衡感觉和制度操作的技巧。
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现阶段最需要重视的。我们不乏对现状的不满和价值主张,而我们缺乏的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中,使社会转型软着陆的操作技巧。这就是我对革命与立宪问题的几个观点。谢谢大家。
刘擎:现在我们就开放给大家提问、讨论、发表观点。
崇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托克维尔涉及的很多问题都很复杂,我阅读托克维尔很多年了,从来没有想到托克维尔有一天会爆红。我读托克维尔的感觉是,他的很多观点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历史是非常相关的,但是这种相关性还没有被真正理解。
《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批判中央行政集权对法国政治自由的剥夺、对法国人民的败坏。这本书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或者说高层领导的推荐而成为畅销书,多少以某种反讽的方式说明了它在中国的意义。
从这本书当中可以读出对革命的警告。革命会导致巨大的破坏,这是一种警示,或许很多人会因此认为应该维持现状。但我们也可以读出通过改革避免革命的提醒。而我特别希望的是,中国的民众或者官员能够从这本书认识到行政集权或者国家主义导致的危害。如果中国想要避免革命,就要从改革集权入手,转向更为开放的政治体制,推动宪政和政治更新。
我看过许章润教授的访谈,也听了季卫东教授的报告,两位从法学角度出发的关切与我的希望是一致的,我们都期望能够通过阅读这本书,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刚才季卫东教授讲的一点很重要,他通过英法对比,指出法国之所以没能走上比较平稳的政治转型,是因为法国的行政制度使得贵族边缘化,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阶层。
在旧制度时期,法国的国家建构通过中央集权剥夺了传统的地方自由和贵族政治权力,使得中央集权成为社会政治控制和动员的唯一手段,导致社会上各个阶层缺乏政治行动和自由的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它导致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对立,并且培养了民众依赖国家的国家主义心态。
这种中央集权并没有真正能够通过有效的权力或者组织方式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团结起来,恰恰相反,它导致了社会阶层的断裂。
因为国家的垄断取代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和领导,也取代了地方自治,使得法国人的所有问题都试图通过中央行政集权来解决,他们彼此之间也失去了联系和合作。而当时法国特有的等级体制并没有真正地被消除。
法国中央集权的建立并不是以完全取消过去的等级制度来进行的,它保留了旧的等级制度,同时建构起新的中央集权。为了使贵族接受这种变革,中央政府在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后,强化了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特权。
这导致一方面贵族失去了实质上的政治领导权,另一方面又保留了经济和社会特权,正是后者彰显了贵族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区别,这导致了贵族和第三等级之间的对立。在这种特权体制下,每个法国人都想成为特权分子。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这个特权体制,所以法国社会中充满了怨恨和对立。
中央集权的建构是一种国家主义的体现,我认为这本书实质上是对国家主义的讨论。它揭示出,国家主义试图仅仅借助国家来建构一个很强大和有效的社会动员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许纪霖辛亥革命 [讲坛]重温百年辛亥革命 许纪霖:新政是革命温床](https://pic.bilezu.com/upload/9/a0/9a03da4be1ce43d859a579f6432d4b78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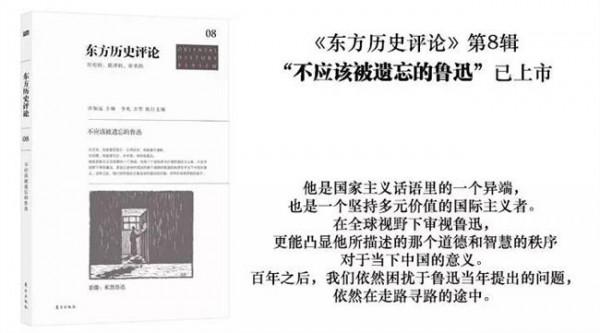



![>许纪霖反毛 [讲坛]精英等于贵族? 许纪霖:反思中西方大学教育](https://pic.bilezu.com/upload/0/f9/0f981c99e378d5a456dbcc465fadd5e4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