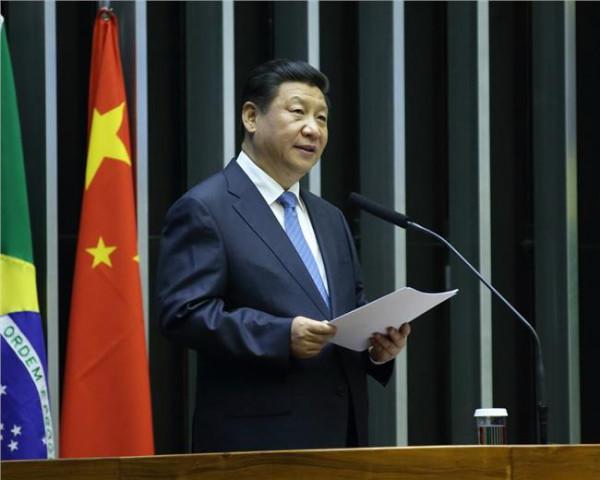高全喜讲座:《大国之道: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第三部分内容是探讨一下国家哲学问题。前面我简单地谈了多方面的问题,在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自己和几个学术朋友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思想,对于上述的中国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理解。就我个人来说或者我希望自己能逐渐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思想。
对于政治和公共问题,我们可以发表议论,但不要期望这些议论马上就要变成政策。制定政策是专门的技艺,不在相关的位置,没有掌握相应的信息,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不经过特定的程序,不可能形成方针和政策。
可以有思想和观点,自由表达出来,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能说我表达出来的东西就必须在实际的政治政策上怎么样,这就是一种幼稚,政治是一种特殊的技艺,特殊的技艺需要特殊的知识,需要特殊的程序,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名不正则言不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作为学者和思想家,我可以谈自己的想法,可以谈自己的理论,甚至可以形成一套国家哲学,但那是理论层面的东西,并不是国家政策。 现在的问题是说,《大国》丛刊办了以后,我发表了几篇文章,还有几篇文章正在写,还有其他几个朋友的文章,虽然比较多元,但还是有一条隐约的主线。
我时常问自己:中国现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建设一个自由共和宪政的现代民族国家,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当前最迫切和紧要的核心问题。
怎么理解呢?刚才说了,古典古代的西方离我们太遥远了,古希腊是很好,但跟我们与什么关系呢?太遥远了,关于这个问题在我的书里已经论述了。中国汉、宋时代的王朝政治也不错,但跟我们也相当遥远。
最现实的问题一八四零年以来面临的困难,西方自十五世纪以来,人家走了过来,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在制度上已经胜出。古典古代很好,现在在哪儿,几乎全都淹没无闻。 所以,我说建设自由共和宪政的民族国家才是我们时代最主要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建设性的,在这一点上我和思想界的一些左派朋友存在分歧,他们基本上是站在消解、批判、质疑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上的,这在西方有社会背景,没什么新鲜。
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来说,它还没有建立起来,尽管它肯定有弊端,甚至还一定会出现问题,但我们又不能绕开它,为什么我们要对一个注定会产生的东西,横加质疑、批判和消解呢?对于一个还没有发育成熟的青年谈老年衰老问题,对于一个瘦子谈营养过度问题,这有什么意义呢?那可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讨论它,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太奢侈了。
但是,我的观点和某些自由主义者也不同,他们往往满足于谈论自由主义的一般原则,强调个人权利,反对国家体制,而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忘记了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面相,因此,变成了教条主义。
在这方面,我赞成北京大学的李强教授,他指出了自由主义有一个隐秘的主题,就是国家问题,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与国家完全对立的,它反对的只是无节制的肆意的无法的国家权力。
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曾经论述,英国这个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尽管存在普通法宪政主义,从来没有忽视它的国家建设,我们不要被偏见迷惑了眼睛。例如,斯密这位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当时也还是赞同《航海条例》的,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实际上也是国家问题,英国的自由主义同样讲国家,讲大不列颠的国家利益。
只是英国、乃至美国这些民族国家历史地看比较幸运,它们的制度具有自生自发的优越性,国家利益和实惠包含在所谓普世的价值之中,由于它们的国家主权和政治、经济利益已经彰显得很厉害,大可不必再强化国家了,而且这也是外交的一个技巧,把国家利益隐藏在所谓普世的道德价值之中,这是高超的政治智慧,另外也是人家的实力和运气。
这几个国家天生运气就比较好,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古代传统、精英智慧,等等,它们处理得很好,所以胜出了。 相比之下,德国和法国就稍微不是那么幸运,这些国家的理论家们大多强调国家,比英美迫切,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没有办法把国家利益掩藏在普世的价值之中,国家建设与自由主义的一般原则并没有天然地结合在一起。
但是,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强调国家建设并不意味着与自由主义完全对立,实际上它们并不排斥自由主义,李斯特也主张自由贸易,只不过在他看来,在德国当时的特殊情况下,首先要强调关税同盟,先保证国内的自由贸易,等德国发展到英国那个阶段,在世界上占有英国的那样的政治经济位置,再和英国一样搞自由贸易。
根据德国当时的处境,如果全面搞自由贸易,德国早就完了。所以,德国问题是关键,李斯特与斯密在很多方面又是相通的,对此,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河内一男的《转折时期的经济学——斯密与李斯特》,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他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问题,不犯教条主义的毛病,很有启发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前两天有一位朋友从俄罗斯回来,他跟我说起一个事情,我感受很深。
在俄罗斯那位朋友曾经见到俄罗斯自由派的一位女士,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她跟他聊的时候感慨地流出了眼泪,她说俄国的自由派确实主张宪政,主张法治,主张自由民主,但是让他们感到痛心的是,当他们为之奋斗,并取得了现实的成果时,苏联在哪儿?他们的祖国在哪儿?现在已经退回到彼得大帝时期的疆域,甚至都还不到。
这样的自由主义是不是令人痛心?代价是不是太高。中国今天难道不也面临这样的两难吗?也许有人会说,我是纯粹个人主义,无所谓,四海为家,世界大同。
这个基本观点,从终极目标说,我也赞同,但从内心我说服不了我自己,我更觉得这种自由主义难以说服人民。我个人是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假如中国的自由政治以前苏联那样的解体为代价,这个自由主义,人民能够接受吗?对此,我没有结论,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想会有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回答。
有人可能说无所谓,在哪个地方生活无所谓,只要有个人自由就可以了,也许有人会说,要讲个人自由,还要讲国家利益,讲民族感情。
所以,我和左派思想的超前主义不一样,也和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不一样。我认为现在的核心问题,第一是建设性的,不是批判性的;第二,我们主张自由宪政的现代民族国家,不是一个王朝政治,也不是西方古典的共和国。
什么叫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形态,有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也有像拿破仑式的僭主制的民族国家,也有像前苏联的政党国家,中国国民党时期的党国,也有英国那样的联合王国,美国那样的复合式的联邦共和制的民族国家。
假如认同我们的观点,既讲个人权利,也讲国家利益,那么就会赞同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认为建设自由宪政的民族国家,才是我们现时代的基本任务。
建设民族国家,强调国家利益,是否就意味着当前我们所处的东西就是好的,就是在强化它,我并没有这个意思,从来没有。我们不要一谈国家,一谈国家利益,一谈主权问题,就认为是在为一个什么东西张目或做辩护。
究竟什么是民族国家,什么是比较理想的民族国家,需要分几个阶段走,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孙中山曾经谈到三个阶段,我们是不是考虑也需要有一个阶段性。我基本上赞成孙中山那套逻辑,当然不一定用他的词汇。
从五族共和这样的民族国家,逐渐向政党形态的民族国家,或党国的民族国家转型,然后走向联邦制或者自由共和宪政的民族国家。中国这么大的地域,特别是两岸三地,周边事态,对日对朝,还有印度,最后还必须面对美国。
大国需要联邦制,这是基本的政治学原理,当然,联邦制有不同的形态,实际上中国目前从政体形式上说就是一种联邦制的形态,有关台湾的“九二共识”,香港的基本法,以及目前的民族自治区制度等,这些都说明我们已经不是单一制的国家,而是联邦制的国家。
只是联邦制还不成熟,还没有上升到宪政形态,到底今后采取什么样的联邦制,这是可以探讨的。不过,我想特别指出一点,那就是制度建构不是从观念推导出来的,而是在现实过程中自发衍生出来的,学者可以提出一些思想观念上的途径,但现实政治完全是另外一码事,稳定的制度往往是多种搏弈的结果。
今后什么样,谁也说不好。 说到建设民族国家问题,在原则层面和制度层面我们确实面临很多严峻的问题,假如没有一套审慎的国家哲学,没有一套比较柔性而且又是比较开放的制度框架,危机是很大的,将来是很危险的。
过于绷紧的东西,一旦断裂,弥合起来是非常难的。这需要审慎的智慧,我特别强调审慎的智慧,对青年朋友的道德热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爱国主义也不能简单称之为爱国贼。
但是,单有感情是不够的,大家要理解,政治是一种专门的技艺,这个东西需要专门的知识,特别是经验。我们现在需要给各种意见提供平台,不能压制这些意见。
但是,也不能盲从大众的意见,在此,何谓“正确理解的利益”就显得十分关键。在我看来,我们目前最大的利益关怀是建设一种自由共和宪政的现代民主国家,这是我们的长远利益,它是确保我们很多眼前利益的基础。
农民问题不是不重要,腐败问题不是不关键,但它们能够在目前的政治形态下获得根本解决吗?就我来说,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最主要的任务,是探讨有关国家建设这方面的战略、观念、理想和原理,这是我主持《大国》的一个主要目标。
当然,我再次指出,这些只是理论上的东西,属于宏大叙事,而不是策论,更不是奏折。现实是另外一回事,有些人往往想当然,仿佛一谈论这个东西,就要操戈入室,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探讨的是学术,关于国家建设的学问,策论不会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高全喜上海交通大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宪法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举行[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f/da/fda0ec1996ffc6b584f82f13eadc3906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