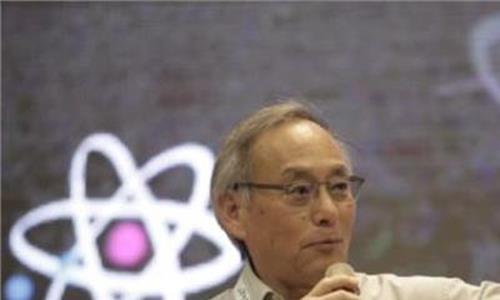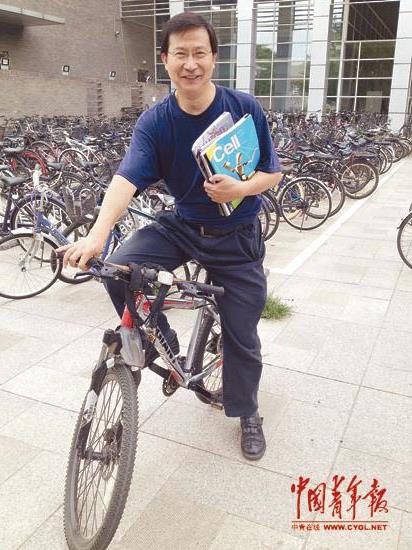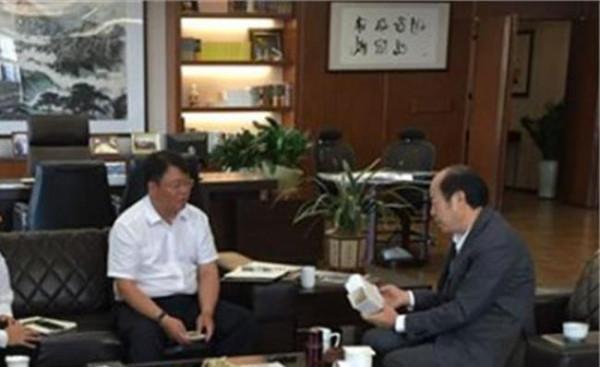董强北京大学 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北大教授董强谈法国文学
全球的新浪网友早上好,非常开心在文坛开卷遇到大家,今天让大家久等了,今天做客的嘉宾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勒·克莱齐奥,以及我们非常尊重的北大的法语教授董强老师,两位好。先从昨天12月6号傅雷翻译出版奖谈起,今天两位嘉宾,其中勒·克莱齐奥是这次的颁奖嘉宾,董强教授是这次傅雷翻译出版奖的主席,两位在这儿能否先来谈谈这个奖项?
对我来说这个奖非常重要,主要翻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没有翻译,我们就像是瞎子或者是聋子一样,我们由于文化之间没有交流,也许我们只知道自己的村庄或者自己的城市,而且对我来说文学是一个跨越国界的东西,文学绝对不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比方说我要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不会想到他是一个俄国人,我会想到这是全世界的,因为译者的工作,使得《安娜卡列尼娜》的感受我们可以一起跟他分享。
董教授,您是这次傅雷翻译出版奖的主席,这次像《蒙田随笔全集》也是获得了最佳奖项,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翻译奖?
对我来说这个奖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翻译大国,但是近年来我们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上相对薄弱,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我真的希望让大家对这个事情重视,因为我想一个民族文化的振兴和发展还是需要跟国外文化交流的。我们曾经在80年代大量翻译过外国作品,现在在我们经济发达成为经济强国的时候,我们要追求一种文化强国的姿态,在这种时候我们就需要大量的翻译外国优秀的东西,而且要有好的译者把中国优秀的文化也翻译出去。
借一个稍微小的机会,让二位再跟网友介绍一下,因为刚才很多网友向二位问好,因为这是一个向全球的直播。刚才有像“钟宜霖”等等都是您忠实的读者。
我非常高兴在这儿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网民、读者见面,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尤其平时我们的写作经历是一种很孤独的经历,在这儿可以跟成千上万的读者一起进行交流。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新浪。
董教授呢?其实董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上一次采访您是安德鲁《记忆的群岛》,他是米兰昆德拉惟一一个中国的弟子,其实他翻译了非常多优秀的作品,包括自己也有一部很好的诗集在法国出版了,您也跟大家再问候一下。
新浪的网友大家好,我今天主要是陪诺贝尔奖得主、尊贵的朋友勒·克莱齐奥来的,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提问,我一定会好好的翻译,谢谢大家。
今天特别荣幸有这么棒的北大的翻译教授作为我们现场的翻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到傅雷翻译出版奖,其实很想问一下二位,近几年二位有没有关注一些中国的作品翻译到尤其是法国?
我读很多翻译作品,我也当然很喜欢法国文学,但是我非常喜欢读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能够丰富内心和丰富经历的一个事情。比方说在读老舍作品的时候,我仅仅通过语言,因为我当时从来没有见过北京,更没有见过他描写的北京,但是语言作为一种神奇的东西,让我感受到了当时的北京,感受到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感受到一个家庭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而且能够丰富我的内心,我当时在阅读的时候就觉得我完全沉浸在里面。
董教授呢?您是法国文学的研究专家,您看近几年中国的作品翻译到法国的情况怎么样?
近几年还是有不少书翻成法文的,法国人对中国还是很感兴趣的。刚才勒·克莱齐奥先生提到老舍,像这些经典作家,很多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了法语,一般读者感兴趣,还是可以找到他喜欢的作家的。
我跟您说一个网友的反馈,他说其实您的作品并不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才这么受中国读者的欢迎,之前从您1982年那部《沙漠的女儿》,也叫《沙漠》,20多年来很多人一直读您的作品,像《沙漠》、《诉讼笔记》、《少年心事》、《战争》等等,包括最近出来的《乌拉尼亚》等等作品,大家都非常熟悉,您自己对这些被翻译过来的作品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您最喜欢哪几部?
我非常高兴中国读者最早知道我的作品就是《沙漠》,对我来说那个时期是我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我改变了我的创作方式、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期,所以中国读者最早接触我的作品是那部作品,我非常高兴。我也非常高兴《乌拉尼亚》能够得到中国人的喜欢,而且得到了外国最佳小说奖,因为《乌拉尼亚》里边我放入了自己很多个人经理,包括自己在墨西哥、南美的一些经历,同时也完成了我的宿愿,要写乌托邦,我非常喜欢《乌托邦》这部小说,我当时把这个想法实现在了我的《乌拉尼亚》里,描写现代的一种乌托邦。
说到《乌拉尼亚》,刚才有一个“游客2160”的网友想让我问您一下,这部作品是不是和中国的桃花源有关系?想问一下您看过陶渊明的桃花源的故事没有。
实在抱歉,对桃花源的故事我真是不太清楚,但是我刚刚尝了龙井茶,我知道有龙井这样同样优美的故事。
董教授,您对勒·克莱齐奥的作品非常熟悉,我看您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对于目前翻译到中国的作品来讲,您比较推崇他的什么作品?
我个人觉得勒·克莱齐奥先生的作品应该更多的在中国翻译,您刚才提到了几部,都是非常好的作品。我个人最喜欢他的《沙漠》,也喜欢他的《诉讼笔录》。我跟他认识,跟《诉讼笔录》也有关系,我当时看完《诉讼笔录》,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作品,因为他带有全新的视野,他当时很年轻,才23岁,一举成名。
法国文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学,当时正好是存在主义、新小说、超现实主义等等这些浪潮,有的是已经过去了,有的才刚刚开始兴起,就造成了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在各种浪潮之间,以一个完全独立的作家,不融入一个文学流派的全新的作家的面目出现在法国人面前。
所以,也给法国新的文学带来了非常好的开端或者是影响。所以,它是法国60、70年代以后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所以在中国才拥有这么多的读者。要谈到他的作品,其实最近出的一本是《饥饿间奏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作品可以称为您母亲的自传体小说吗?
用了我母亲给我讲的一些材料,但是这里面的人物跟我母亲也是有一定的区别,我母亲当时还年轻一点。主要是因为我写这部小说,当时我母亲跟我讲述当时战争的到来,有点像一个人发烧一样,感觉到要发烧了或者已经发烧了,但是又找不着药去治发烧这种现象,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就顺着这种印象写了小说,战争的到来怎么就找不到药方,当时这么一种无奈的感觉。
说到这样一部作品,又谈到了您的母亲,能否也说两句您母亲对您的影响?
我母亲从小就鼓励我,因为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写小孩写的小说,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她都珍藏起来,而且她还把我写的那些东西一页页缝起来,再加上一个精美的封面,她还取了一个名字,说是什么什么出版社出的,当时用的名字是“狼出版社”出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狼出版社出的,对于我写的没什么意思的东西他都鼓励我,都收藏着。
现在这些东西你还收藏着吗?
我母亲刚刚去世,我再她个人的档案资料里,发现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好好保存着,我想我会传给我的后代,他们看见以后会觉得很有意思。
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您母亲留给您这么珍贵的礼物。问几个网友的问题。
在您的作品里是主观的意识多还是客观的意识多?您更注重社会的哪个层面?
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作家很难明确区分主客观,因为作家不是做一个像科学家的事情,所以他完全应该以他个人的一些情感、记忆、感受出发,从这个角度来讲肯定是主观的。但是他创作的时候,肯定要对他创作的内容和他的题材采取一定的距离,保持一定的客观性,主客观关系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而且对社会来说,没有说哪个特别的层面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作为一个好的作家,可以说是社会的任何一个层面都应该能够写出好的作品来。我们既可以对一些所谓的上层人物,比方说一些政治家、官员、知识分子、很有钱的商人,写出好的作品。
也可以对一些很简单的小市民、老百姓、农民、渔夫等等,也可以写出好的作品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某种生活境遇来决定一部小说的好坏。
在这儿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其实您从23岁第一部作品获奖以来,这40多年期间您出了40多部作品,但其实翻译到中国只有寥寥可数十部,如果您选择愿意再被翻译到中国来的几部左近,您会推荐哪几部?
比方说我听说有的人要翻译我年轻时候的一些作品,比方说《地球上的陌生人》,或者我写的《物质的狂欢》等等,这些作品都是我早年写的,当时我还想带有点哲学家的眼光,想写出一点深度。虽然时过境迁,我觉得当时我翻译出来的作品还是挺好的,因为里边关注了很多我自己的东西。
说实话董教授,我看了您写的那篇《勒·克莱齐奥的世界视野》,您对他的作品真是非常熟悉,要是让您来给我们中国读者介绍,他有哪些作品是愿意最早翻译到中国来?
这个东西确实也很难说,从目前的几部来说,就像登山的几个点一样,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他作品的冰山一角。从目前来说,要翻译的话,我向来主张对一个伟大的作家、重要的作家的作品要全部翻译。而且我也是同意他的观点,早期作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往往一个作家最好的东西已经在早年的作品中都能看到。
一般人家请我翻译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作家的时候,我一般都是从他的第一部或者第二部作品开始翻译起,这样能够让人家感受到一个过程。我很希望中国读者能够看出脉络来,一个好的作家值得我们收藏所有的导演的DVD一样,把它所有的作品灌输起来以后能够感觉到一个更完整的勒·克莱齐奥先生的形象。
您被很多评论界誉为新预言派,不知道您是否接受这样一个说法?
我个人不认同这个说法,我早就听说这个说法,给一个作家想标上一个标签的做法有点幼稚,因为一个作家不像一个成品,成品才需要标签。所以,像作家是不断的在往前走的,我不太喜欢给作家标上标签的行为。列位斯特劳斯著名的人类学家,这次翻译奖还给了一位翻译列位斯特劳斯的人。列位斯特劳斯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奠基人,当时有人问他什么是结构主义,他回答我不知道什么是结构主义。
董强教授,在这儿我要替网友感谢您,因为很多网友在给您竖起大拇指,说您的翻译很棒。
谢谢,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回到勒·克莱齐奥先生,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网友,很多网友的问题非常踊跃。
您通常在什么时候用英语写作,您的著作会有英语版吗?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很早的时候就用英文写了两部侦探小说,我寄给伦敦的出版商后来一直没有回音,或者我的英语不够好,或者我的小说写得不够好,或者两者都不够好,当时就不了了之了,说不定有一天我再去英语写。
您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家,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您有没有受一些您前辈作家的影响?他们是谁?
我17、18岁的时候读过很多美国文学,当时美国一些好的作家的文学作品我都读过,比如斯坦贝克、塞林格等等作品,因为我当时觉得当时的美国文学要高于当时的法国文学,因为当时法国在做什么新小说,当时他们过于追求技巧,对我来说美国作家当时更关注现实,关注真实的东西。比方说当时我觉得塞林格的作品远远高于阿莱格里的作品。
对于法国作家呢?
现在我可以说的是我喜欢的法语文学更多的是来自于非法国本土的用法语写作的作家,他们很多是来自于北非,甚至来自黎巴嫩等一些国家,他们用法语写作,而且很多作品非常有意思,这些作家好多在中国甚至都没有译作,但是他们的作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说到这儿让我也想起来两个人,也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加缪,一个是西蒙,他们也是属于异乡的法国人,您的创作跟他们有没有一些共同之处?
我非常尊重而且非常崇敬加缪,我非常感兴趣是因为加缪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在北非阿尔巴尼亚度过。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法语作家,给法国带来了地中海的阳光,因为巴黎是一个多雾比较阴沉的城市,而加缪带来了地中海的阳光。从西蒙的角度来说,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描写战争,而且他有战争时候痛苦的经历,这两位作家我都非常尊重。
包括您,包括他们跟法国本土尤其是比如说像巴黎的一些作家在创作上有没有一些区别?
当然有区别,我本人是出生在毛里求斯岛,我一直对巴黎的作家圈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巴黎人到毛里求斯追求异国情调,对我来讲巴黎具有异国情调,我跟巴黎的很多作家是有区别的,巴黎好多地方有些抽象,好多人都沉浸在一种体系里,对现实不够关注,甚至有时有各个门派、各个山头,有的人也弄出一套体系,自己在里面觉得可以安安稳稳的得到保护。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作品,我个人觉得不应该在一个山头、一个体系里。
说到这儿特想问您,因为知道您常年会在英国、美国、法国、毛里求斯等,您几乎是一种游牧式的写作和生活。这种生活的方式对您本身的创作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我确实是有点不愿意在一个地方久呆,我这样的行为并不是说我一定非常好动或者是我到处去追求什么异国情调,而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以后免不了会受到各种各样程式化东西的束缚。对我来说创作需要一种全新的感受,反而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能够跳出程式化的东西,能够更好的感受大自然,感受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在脱离了各种城市化的套路的日常生活的情况下,一个作家会更加真诚。
孔帕农说“文学何用”,托多罗夫说“文学在危险中”,请问您对文学的未来有何看法?文学是否还有创新和继续发展的空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严肃的问题,但是我想如果“文学无用”,我今天也不会在中国、在新浪这个地方跟这么多网友见面,文学是一个运用了非常古老工具的表达方式,这个古老的工具是能够不断的适应新的情况的,而且因为它用的本身的材料是人最需要的,就是语言。
所以,文学家创作用语言就像一个工匠用木头去做桌子或者建房子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非常精确的、非常需要自己个人投入的像工匠般的工作。这个工作跟人是休戚相关的,它永远都不会是无用的。
“因为美丽的人生是多么的短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回答,而且我同意他的这种回答。
对于年轻的一些法国作家您有没有特别推崇的?
比方说有一个多哥的作家科夫因,他小说写得非常好,有一本《幽灵的独白》,非常好。现在法国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作家,叫玛丽·诺亚艾,她刚刚得到了文学奖,她写的《三个女人的肖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这是作家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绝不轻易写作,但是每次写出来都是非常好的作品的一位作家。
董教授您要推荐的话是什么?
要推荐就非常多了,法国文学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灿烂的文学,说出来数字很吓人,每年夏天以后,秋季我们都可以读到300—400部小说,作为一个只有6千万人口的国家,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而且是每年都有新作,而且几乎一些著名的作家每年都有新作。我经常在这个上面做比较,确实法国文学是非常灿烂的一个文学。所以,今后如果大家有需要这方面的一些,我可以做更多介绍。
在这儿还要问一个问题,您平常除了文学创作之外,您自己有一些什么特别消遣的方法吗?除了写作。
我非常喜欢独自行走我也喜欢游泳,这两天没时间游,但是我很喜欢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但是我今天特别纳闷,我告诉各位网友,上次勒·克莱齐奥先生来到北京的时候,当时就是人民文学颁这个奖的时候他穿着凉鞋,今天依然是这样,北京已经零下了,为什么啊?
很有意思,我在韩国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说,克莱齐奥先生您肯定是一个贵族,因为贵族不喜欢他的脚受到束缚。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的祖先根本不是贵族,我的祖先是农民。但是我确实是因为我在非洲呆过很长时间,我也确实很喜欢走路,我不喜欢我的脚受到束缚,穿着凉鞋我的脚不受到束缚。
因为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依然要留给我们的网友,先把刚才那句话说完。刚才那位网友说了,文化即人学。
文以载道,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已经到了巅峰,如果到了巅峰之后,您会怎样继续您的文学探索?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我很欣赏文以载道这个说法,对我来说我的文学是要表现一种人的尊严,我最关注的就是人的本身天性中的高贵和尊严的东西,最让我痛苦的就是看到一些战争或者是一些饥饿,甚至一些专政,会造成对人引起的一些严重伤害。小说和文学就有这么一种作用,比如我刚才提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描写战争的时候就是描写战争情况下人的尊严和高贵。
接下来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要做的创作将永远关注这样一种东西,在任何的环境下,包括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一些艰难的情况下人的尊严和高贵。
最后一点点时间,您亲自再对我们所有的全球的您的读者、关注您作品的朋友们再说几句话。
我想说的是,因为这种新的互动方式我非常高兴,但我同时也希望大家关注书籍,因为读书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工作,真正在书籍的交流中我们可以达到更深刻的交流。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而且向来是有非常好的文学传统。所以我希望读者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书籍,去阅读书籍。我今天真的非常高兴能够跟网友进行这次交流和联络。谢谢大家。
董教授,今天也要特别感谢您这么优秀的翻译,真正的行家。您也跟我们的网友说两句。
我确实非常高兴,尤其是这次勒·克莱齐奥先生是专程法国使馆和我本人请来的,我们就是为了他给我们这个傅雷翻译奖助阵,而且他在非常繁忙的日程当中专门找出时间来北京,我非常感谢他,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作为我们外国文学工作者或者是在国外长期工作过的人,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中国文化和外国的文明之间能够建立起真正的桥梁,我们的作用就是这样。
我还是那句话,中国文化非常强大,我们要变得真正强大的话,我们需要时刻保留跟外国之间的交流。只有真正的外国文化能够在中国得到很好的消化的情况下,我们的文化才会真正强大。谢谢大家。
也非常感谢二位,祝愿您更多的作品被我们的中国读者读到、世界读者读到,也非常感谢董教授,一定要把更好的作品翻译给我们的读者。谢谢,也谢谢所有的网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