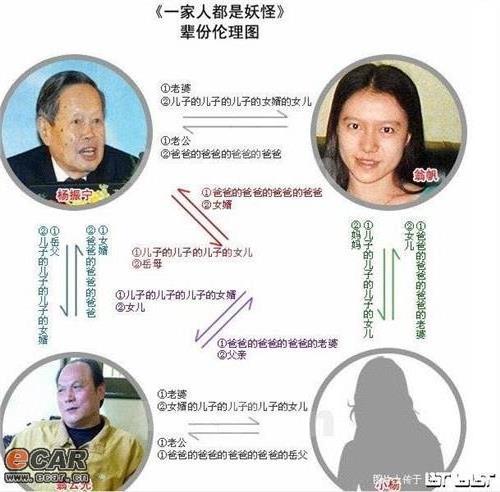张千帆的文章 张千帆: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制度与文化的百年进化
在这11种宪法书籍中,超过一半是关于美国和法国的宪政制度介绍。虽然这些介绍未必全面或深入,但是和清末立宪时期不同的是,人们似乎已经不那么关心体用之间的关系,也不太在乎这些国家的制度是否适合“国情”。虽然中国未必照搬外国的制度,但是,先进国家的经验总是值得学习并在适当的情况下借鉴的。
(二)法治实践的有限成就
法治不仅是当时的流行理念,而且也是新制度力求实施的重要内容。虽然清末的两部宪法性文件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且《钦定宪法大纲》还是坚持皇帝“总揽司法权??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但是,即便是《钦定宪法大纲》,也提到了司法和行政“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更是明确规定了司法独立原则,读起来和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颇为相似:“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第51条) ;“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第52条) 。
在以后的民国时期各部宪法或草案中,三权分立的基本架构和司法独立原则基本上被保留下来。例如,“天坛宪草”规定:“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第88条) ;“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停职或转职。
法官在任中,非依受刑罚宣告或惩戒处分,不得免职”(第89条) 。这两条被曹锟的“贿选宪法”原封不动地照搬过去(第101、102条) 。
即便“大总统??总揽统治权”的“袁记约法”,也规定了“法院依法律独立审判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第45条) ,法官终身制(第48条)则照抄《临时约法》第52条。由此可见,至少到民国时期,分权和司法独立原则已经成为普遍认同的宪法制度。
在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下,民国法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产生了一些在当时影响巨大的案例。例如,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司法总长伍廷芳坚持司法独立、公正审判原则,遏制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干涉司法和越权滥捕的行为,有力抵制了军政对司法的干预。
[46]1913年发生宋教仁命案后,上海地方检察厅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赵以健康为借口拒绝到上海出庭,但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法院竟敢传讯总理,并公布政府高官与杀人犯之间密切往来的证据,确实是“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47]堪与1974年震动美国的水门事件审判相媲美。[48]
当然,那个年代的制度实施不可能完美无缺。尤其是从清末至今,除了1923年宪法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稍有涉及之外,中国历代宪法都没有规定过类似“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所创立的司法性质的宪法审查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它说明虽然宪法条文显得很重视法治,但是,法院和法官在中国的地位并不高,至少不足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事实上,当时对司法审查制度以及“马伯里诉麦迪逊”这个里程碑式判例的讨论寥寥无几,王世杰在1923年出版的《比较宪法》中基本上没有涉及这个议题。
当然,在民国制宪过程中,也有少数议员主张最高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例如,参议员王正廷认为,由国会议员组成的宪法会议解释宪法将违反“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法治原则。
[49]但是,多数制宪议员表示反对。他们中有人认为立法机关是对宪法的更可靠保障,而法院以少数人的意志推翻立法的做法,必然侵害法律的尊严;有人认为民主国家主权在民,而国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因而司法审查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况且当时欧洲大陆各国也没有采用司法审查制度;还有人采用“谁制定,谁解释”的原则,认为宪法既然由国会制定,就应该由国会解释。
[50]这也说明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对司法在分权结构中的作用认识不足,但是,这种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
在军阀割据、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年代,恐怕很少有人会注意这个看似“技术性”的题目,更何况在民主制度还没有确立起来之前,司法审查成了无的放矢的奢谈,对于当时中国来说实在是有一点“超前”了。
三、人权———从手段成为目的?
在以义务为主导的儒家传统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显然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儒家伦理和现代人权观念格格不入;在某种意义上,我对你的义务就是你的权利。况且儒家从来高扬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因而可以被认为是“集体权利”的捍卫者。
尽管如此,不争的事实是,现代人权观念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集体权利”最终也要落实到个人身上。虽然儒家不仅强调“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而且也主张“为人君,止于仁”、“为人父,止于慈”,[51]但是臣不“敬”、“子不孝”的后果很严重,而如果君不“仁”、父不“慈”,似乎除了道德说教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相比之下,现代宪法权利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利———也就是说,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法律救济的,而这一切对儒家传统来说无疑是很陌生的。
无论在制度上还是文化上,中国对个人权利的“本土资源”实在不多,而似乎可以预料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其他领域相比将遭遇更大的阻力。[52]
一般认为,严复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将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在《原强》中主张“民之自由,天所界也”,且西方之所以强于中国,正是因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但是,事实上,严复并不是一位严格意义的自由主义者。
在骨子里,他仍然摆脱不了以集体为本位的儒家文化影响,因而他的主张实际上更接近社会功利主义者( utilitarian) 。当然,社会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发生必然的矛盾;集体利益是个体利益之和,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不仅没有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53]然而,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学说,个体或少数人的利益和多数人的利益确实是可能发生冲突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严复毫无疑问主张“两害相权:己轻,群重”;如果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发生冲突,则每个人都有义务“舍己为群”。[54]既然连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都这么认为,权利观念在中国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适应乃至吸收西方人权观念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虽然清政府显然对“臣民”的权利不感兴趣,但是《钦定宪法大纲》还是“附”上了9条“臣民权利义务”,其中有6条是关于“臣民”的权利,包括担任公职的权利、表达自由、罪行法定、获得法官审判的权利、财产权和居住权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则专门规定14条“人民”的权利,第5条和第6条还十分科学地区分了平等权和自由权。以后的“天坛宪草”、“袁记约法”、“贿选宪法”也都在国家结构条款之前规定了人民或国民的权利, 1936年的“五五宪草”和1946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则在“总纲”之后就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
到民国时期,人权在中国似乎已经从功利主义的手段转变成自身值得追求的目的。
当然,宪法规定是一回事,权利保障的具体实施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因为缺乏司法审查制度,侵犯人权的事例自然是屡见不鲜的。192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保障人权命令。胡适等人借此在自由主义杂志《新月》上发表文章,列举了许多国民党政府侵犯人权的例子,公开提出保障人权、制定约法、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进而发动了一场人权运动。
[55]胡适本人因此受到当局警告,甚至被迫辞了校长职务;杂志总编罗隆基则受到拘捕,《新月》也不断遭到查禁而无法按时出版。由此可见,民主、法治尤其是司法审查保障机制的环境下,保障人权的宪法或法令是完全空洞的。
但是,即便如此,这些事件仍然表明中国当时对自由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例如,罗隆基曾精辟地指出:“压迫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56]或许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言论自由重要性的把握基本达到了同时期美国最高法院的少数杰出法官的水平,[57]而且和美国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相比,中国少数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仍然针锋相对、直言不讳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
胡适曾将矛头直指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其对国民党鞭辟入里的批判可以说超越了当代学者的境界:一党专制“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主义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
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但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
[58]同时,他准确地预见到:“现在的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59]
国民党政府漠视人权、弹压言论的行为,使其丧失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最终丧失了政权。一个政府可以压制人民对它的批评,却不可能强行获得人民的拥戴。当然,这些尖刻的言论当时仍能公诸于世,确实表明言论自由并非完全丧失了公共空间,只是发表政治言论将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由于国民党政权对外面临日本侵略,对内受到共产党的制衡,党内也各路派系林立,因而无暇顾及所有对其不利的言论。但是,正像没有制度化的地方割据不是“联邦制”一样,没有制度保障的言论自由或其他任何权利也配不上“权利”的称号。
如同民主与法治一样,民国宪法文本中的公民基本权利只是不能兑现的“口惠”( lip service) 。事实上,在欠缺民主和法治的非常环境下,权利也不可能受到切实保障。
四、中央与地方分权———难以摆脱的集权传统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和其他宪政要素相比,中央集权可以说是中国最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固然,由于中国地域巨大、地方差异显著,在交通和交流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中央集权必然有力不能及的地方,从而为地方自治留下了有限的空间,但是,这种有限的自治只是中央恩赐或疏漏的结果,当然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制度”。
虽然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曾提倡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分工,例如,乾隆年间秦蕙田提出:“设官分职,内外相维,体统相制”,[60]但是,只有到近代才真正认识到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61]也只有到近代,有关中央和地方分权的讨论才真正展开。
(一)联邦作为制度博弈的工具
到民初制宪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成为利益集团之间较量与妥协的重要话题。[62]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主张中央集权,革命党人则大都支持地方自治和联邦制下的统一。袁世凯死后,最支持地方自治的是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
[63]1916年至1917年,北洋派军人集团害怕省长民选将削弱他们的权力,因而反对联邦分权制度。没有北洋政府和直系军人等实力派的支持,省制即使入宪也很难执行。1922年至1923年,反直的实力派维持分治的利益格局,而主张中央集权的直系北京政府最后做出妥协,同意省制入宪和地方分权。[64]
这个时期有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争论体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也就是宪法制度不仅是西法东渐的结果,而且也是中国当时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产物。在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失去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各派势力相对均衡(至少变化莫测)的情况下,政治较量和妥协有可能产生更稳定的宪法制度安排。
事实上,在1913年、1916年—1917年、1922年—1923年三次制宪会议上,国会议员就总统制与内阁制、国会立法与监督权限、行政权力结构及其与国会的关系、宪法解释权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国体与政体选择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而所有这些制度都是中国在不同时期从西方宪法引进的结果。
[65]然而,制宪议员并不是纯粹从欧美宪法制度来论争中国立宪的模式,更多的是从自己的党派或地区利益出发,力争采行对自己最有利的制度。这是一种相当可贵的能力,西方最早的宪法制度正是在相对均衡的社会权力结构的政治斗争中产生的。 [66]
当然,制度的产生和维持还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如果制宪不从国家利益的长远考虑,而是过分限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动态,也容易出现因人或因事立宪的短视倾向。例如,在1913年,国民党内部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出现争议。
胡汉民主张地方分权,希望利用各省势力来限制袁世凯的野心;宋教仁则主张中央集权,希望在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后能足以约束总统的政治权力。两人虽然主张不同,但是目的都只是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在国民党获得国会选举胜利、有望组织责任内阁时,中央集权纲领自然取代了地方分权主张;而一旦国民党在野时,地方分权的政见又成为党内主流。1914年,国民党出于反袁的需要而倾向于联邦制。1920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