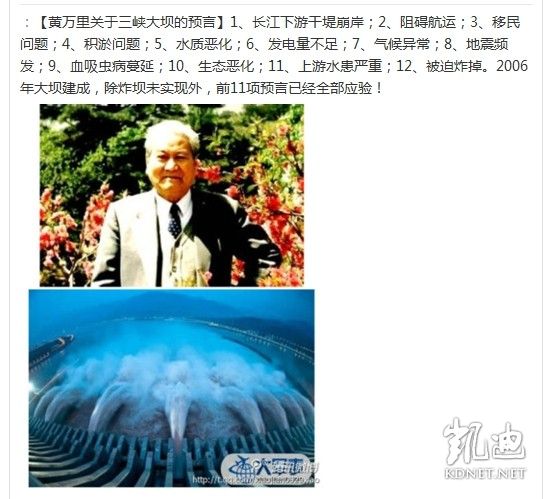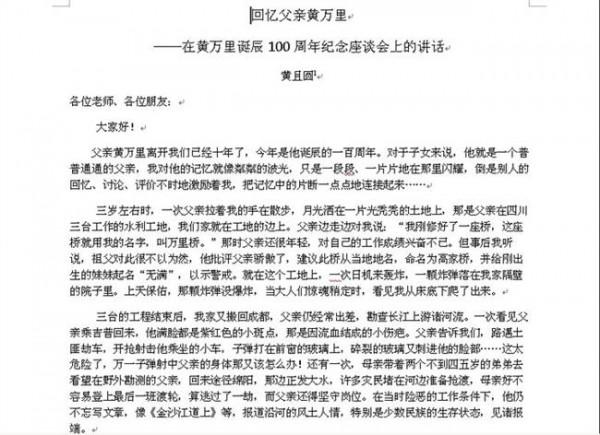黄万里不学无术 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
闻立雕 臧老仙逝,中国诗坛失去一位卓有贡献的著名诗人,我们家岁岁发贺卡的名 单上又少了一位先父生前友好的名字,呜呼!痛哉! 臧老青年时期在青岛大学求学时,师从先父闻一多学诗、学文,不仅诗文方 面收获极大,而且孕育了终生难忘的深情。
浓情从O 与 98 开始 1930年暑假后,父亲受聘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这一年新生入 学考试时,语文课父亲出了两道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另一 题是《杂感》,考生可任选其一;有一考生两题都做了,其中《杂感》只写了三 句话,即“人生永远追寻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
可能就是这红杏出墙,一枝独秀的三句杂感,打动了父亲的心,给了98 分 ,名列全体作文卷之首。
但该生的数学却考了个鸭蛋,O分。按通常情况,这个 学生不能录取,但父亲特别赏识,终于被破格录取了。 这个考生就是后来著名的诗人臧克家,臧老。 当年父亲考清华时,也是其它学科(包括算术)成绩平平,惟独作文仿梁任 公笔调,文才并茂而特别为主考教师所赏识。
录取臧老,父亲可能多少有点惺惺 惜惺惺吧。 臧老原本考的是英文系,入校后学中文的兴趣比学英文的兴趣更大,申请转 中文系。
别人转系非常难,有的就没被批准,轮到臧老,父亲一听名字就说“好 ,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的《杂感》”。 从此,臧老便成了父亲门下一名真正的嫡传弟子。 得一知己,可以无憾! 臧老转到中文系之后,除课堂上专心听课外,还经常在课余时间拿着自己的 诗作登门向父亲请教。
父亲对臧老的印象很好,很愿意倾力指点、帮助,每见他 来了,总是很热情地接待,递上烟和茶,如诗如友地亲切恳谈,或肯定长处,指 出缺点,指出哪个想象很聪明,哪个字下得太嫩;或谆谆教导,告以写诗应持的 态度,要含蓄、耐人寻味,要严肃、要多磨练;既有言传又有身教,既赠以自己 的《死水》诗集,又把臧老的诗篇推荐到《新月》杂志上发表,后来还支援经费 、写序言,帮助出版臧老的诗集,充分体现了对青年诗人无限的关怀和爱护。
经过若干次亲切恳谈,臧老的收获极大,师生感情进一步升华。臧老后来回 忆这一段情况时说:“这时室内充满了诗的空气,我们不像是师生,而是知心的 诗友在对谈了。
”闻先生慢慢地成为了自己“心灵交通的良师和亲切的忘年交了 ”。 “我跟闻先生读书学习,时间不长,也不过二年,但他给我的影响很大, 印象极深,可以说终生难忘。” “可以说,没有闻一多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
1932年夏,同学们受国内时局及校内某些复杂因素的影响,掀起了一次全校 性的学潮,矛头直指父亲,发布《驱闻宣言》,称“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不学无术的学痞”,强烈要求为了“学校前途”和“整个的教育”,把父亲 驱逐出校。
臧老当时对校内的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对父亲的处境很同情,因而 “孤雁出群,没有参加这次学生闹的风潮”。 大概是想到“忘年交”和“孤雁出群”,父亲后来愤而辞职离校时,给臧老 写了一封信,其中讲到:“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我在‘青大’交了 你这样一个朋友,也就很满意了。
” 终生遗憾——没留一张合影 父亲离开青岛大学后,接受母校之聘请回到了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臧老 毕业后到了山东临清,在临清中学教书。 1936 年6月末,7月初,臧老因事来到北平,一天,抽空到清华园看望分别 五年多的授业恩师。他来到父亲的书房,看到还是和青岛时期一样,四壁书架塞 满了图书,文房四宝及书籍纸张摆得毫无秩序,书桌,一摞一摞写满了蝇头小楷 的手稿……。
父亲见他来了,很高兴,放下书和笔,倒上茶递上烟,两人畅聊, 久久不能尽兴。 臧老大概是考虑到见一次面不容易,希望同父亲拍一张合影。
但是,那时臧 老和我们家都没有照相机。于是,约好过几天再来时到照相馆去拍照。不料,几 天之后卢沟桥响起了枪炮声,日寇发动了穷凶极恶的侵华战争。人们的正常生活 完全被打乱了,拍合影的事自然也就谈不到了。
此后,臧老和父亲天各一方,再 没有见过面,合影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两人的一个终生遗憾! 7月19日父亲与保姆带着弟弟和两个妹妹匆匆回武汉(母亲恰好已于6月下旬 带我和哥哥回武汉探望外祖母)。
当时平汉路已不通,只能走津浦路,在车站上 遇到臧老正要赶回山东临清。臧老见父亲所带行李非常简单,想到父亲的四壁图 书便问:“闻先生,您带的东西很少,那些书呢?”父亲回答说:“国家的土地 一大片一大片地丢,几本书算得了什么!
我只随身带了点重要的稿件。” 父亲一向珍爱图书如命,但是,在国家危亡之时,宁可舍弃心爱的书,也不 当亡国奴。臧老为此大受感动,更加崇敬自己的老师了。
以后,他在文章和讲话 中多次讲到这件事。1995年,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栏目摄制《闻一多和美术 》采访他时,他又突出地赞扬了父亲这一点。讲的时候“啪!啪!”拍两下掌, 把大拇指往前一伸!表现了无限钦佩与赞赏的心情,给观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火车路过德州时,臧老与父亲告别,说一声“再见!”便依依不舍地下了车。 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失而复得 臧老非常喜欢父亲的《死水》(诗集)。他一接触到《死水》就被其谨严、 精练、含蕴有味所倾倒,无限钦佩,极为热爱。
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仔细 品味,以至篇篇能够成诵。《死水》大大改变了他对诗的见解,知道应该写什么 ,不应该写什么了。为此,他把自己以往写的诗一把火烧掉了,决心走《死水》 开辟的路子,以它为榜样,努力追攀。
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不仅具有《死水 》深深的烙印,而且连封面也完全仿照《死水》,一片黑,一条印有书名的短红 签横跨书脊。 臧老说: “《死水》给予我的东西太多了”,“《死水》定我终生”。
“ 没有《死水》,可以说就不会有《烙印》”。 父亲在青岛大学时,曾应臧老的请求赠送给他一本《死水》。父亲以“多” 字落款,在扉页上题了“克家惠存”几个字,并且端端正正盖上了“一多印记” 的自刻印。
臧老欣喜若狂,后来说:“我得到它,如获拱璧,天天读它,小心翻 它,珍惜它,热爱它。把它放在宝贵的处所,把它放在心头上。虽然其中二十八 首诗我全能成诵了,还不时拿出它来,托在手上,看看它也是一种高尚的美的享 受。
” 1937年10月,日寇兵临临清,臧老与群众不得不仓皇逃难。临行前将包括《 死水》和几代家传的一部《昭明文选》在内的一架子书包好,委托给一个学生代 为保管,并且特别交代,如果出现什么情况,其它书皆可抛弃,《死水》和《昭 明文选》务必全力保存;实在万不得已,两本中只能保留一本时,那就保《死水 》。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些书竟全部遗失一光, 不知去向。
臧老扼腕痛惜却无可奈何! 1981年8月20日突然出现了奇迹!一位素昧平生的同志给臧老寄来一个包裹 ,打开一看,竟是当年丢失的《死水》和一本初版《烙印》!
一切依然如旧,连 那方印的颜色都殷红如昨。臧老喜之欲狂,泪水不觉阵阵涌出!原来寄书的是河 北农学院一位老领导(该同志做好事不留名,不愿公开自己的名字),抗战时期 在冀南一带工作,某次偶然在乱书丛中发现了这两本书,把它们保存了起来。
臧 老欣喜之余非常感谢那位同志,当即提笔借“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之典,以《 我亡书,我得之——喜〈死水〉、〈烙印〉联翩归来》为题,写了一篇短文以抒 狂喜之怀及衷心谢意。 2000年4月3日,我和夫人杜春华前去探望臧老,那年臧老已经九十五岁高龄 ,平时每天大多躺在床上,这一天可能是因为闻一多子女去了,倍感亲切和兴奋 ,在夫人郑曼同志的帮助下,起床坐在藤椅上和我们谈话。
臧老身体已经相当衰 老,但思维非常清楚,精神状态很好,讲到那本《死水》失而复得时,精神矍铄 ,嗓门不知不觉也提高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同我们拍完合影后,他专门要 我把那本《死水》拍下来,拍了封面拍父亲的题字、落款、印章,最后还要我把 载有出版年月,出版单位等项目的底页拍下来,对这本诗集之深情,至为感人。
青岛海水深千尺, 不及臧老尊师情 臧老跟随父亲读书学习的时间只有两年,但是他说闻先生给他的影响很大, 印象极深,终生难忘。
他说:“对于闻先生,几十年来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仰与感激之情。”“闻 先生的影子,经常在我心头,不论他生前还是他死后。” 这个话说的丝毫不过分 。 抗战初期,臧老在前方做抗日文化宣传工作,时常朗诵父亲的诗《一句话》 ,鼓舞将士们为“咱们的中国”奋勇杀敌;他心中常想不知道恩师现在在哪里, 情况如何?1939年3月,当他从报纸上得悉父亲与同学们一起,从长沙步行到了 昆明,立即作诗《“青天里一个霹雳”——寄一多先生》以表思念及赞扬。
1943年春,臧老将自己的《我的诗生活》一书寄给父亲,在附言里特别说道 :“我无时不在念想你!” 1944年秋,臧老从报上看到父亲在课堂上朗诵田间的诗,赞扬田间的诗是鼓 的声音,非常高兴,特地写诗称赞父亲是“擂鼓的诗人”。
社会上传说父亲被反 动派解聘了,他当即发表《文化战士——闻一多先生》表示关心,盛赞父亲是“ 老当益壮的文化战士”,说:“少数人把他推出去,多数人将打开大门欢迎他” ,呼吁人们“给他精神和物质上以援助”!
1946年7月15 日父亲被刺牺牲,臧老与全国人民一样悲痛愤怒,连续作文缅 怀、悼念,以后,父亲殉难周年,三周年,十周年,乃至1999年父亲诞辰百周年 ,他都深情缅怀,撰文纪念。
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臧老不时想到父亲,萌发感想。全国解放后,开全 国文代会,他又想到了父亲,作诗《为你空出一把椅子》;毛主席提出“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他立即想到父亲治学敢于破除迷信的精神,写了《听争鸣念一 多先生》。
直到耄耋暮年,他还在《闻一多精神》、《追念一多先生》等文中对 研究、探讨闻一多学术论著不多感到遗憾,说:“闻先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 篇,反而受到冷漠,我很不平!
……我认为,现在应该在学术界、在文坛上,以 各种方法宣传、发扬他的业绩,他的卓越成就,他的高尚品德,他的伟大的爱国 主义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他,认识他,因而受到教育。
” 总之,正如臧老所说:“闻先生人虽不在我眼前,却永远,永远在我心上!” 几十年来,他写了大量缅怀、纪念,宣传、介绍父亲,弘扬父亲精神的诗文 。初步统计,仅仅直接以闻一多为题的诗文就达三十一篇之多,这还不包括在回 忆录、自白、访谈、题词,以及《我与“新月派”》、为他的母校山东大学百年 校庆而写的《祖国万岁,母校千秋》等等文章中,涉及闻一多的难以记数的文字。
有谁为他心中所敬爱和崇拜的人,一篇接一篇,持续几十年,写出这么多诗 文? 没有。
就连我们闻一多的亲生儿女也没有。然而臧老确实是如此。 李白诗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今日对臧老也可以说:“青岛海水深千尺,不及臧老尊师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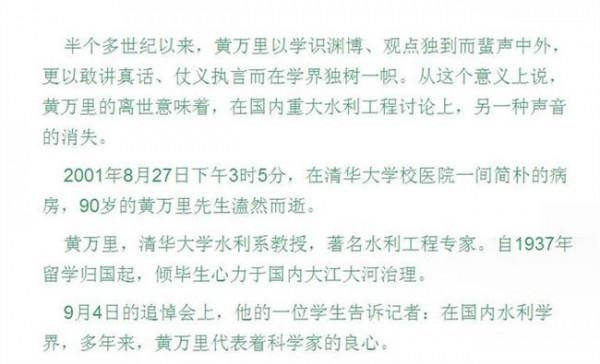

![[原创]黄万里教授预言三峡大坝终将对下游生态造成破坏](https://pic.bilezu.com/upload/f/1c/f1c6c69fe8fdb3b1d5724a487b447a23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