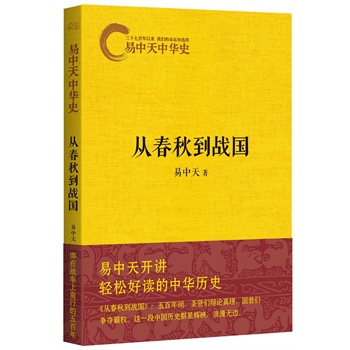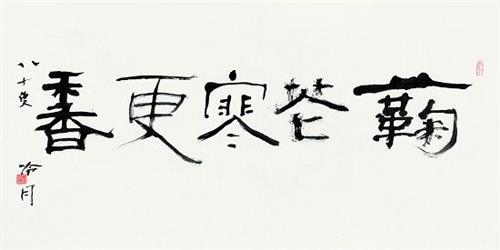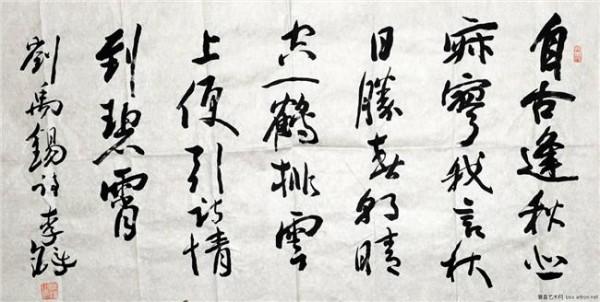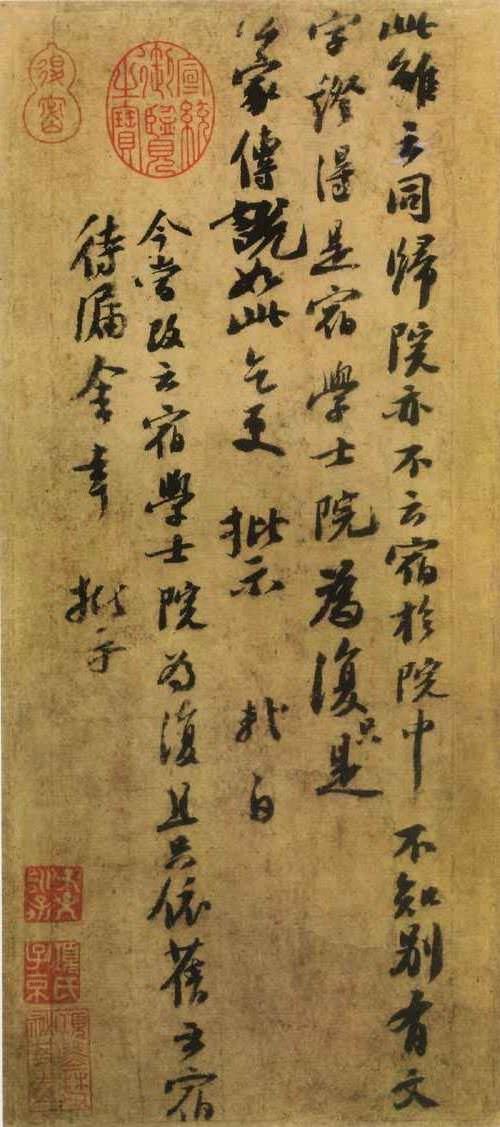赵鼎新书法 东周战争历史的图景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东周战争历史的图景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论学术上的严谨性,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的著作《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远不能被归为上类。
作者本人在序言中承认了其在学术论述上的不足,如概念定义不精确、史料引证比较粗略、对战国时期各国强大战争能力的经济基础的考证十分薄弱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提到“本书缘起于一篇本来没有想过要发表的文章或是一本书的写作提纲” ,作者所指应该是《霸权迭兴的神话:东周战争和政治发展》,发表于2006年2月的《学术月刊》。
而本书中译本出版于2006年8月,书中内容基本是文章的补充论证。因为上述原因,作者承认本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这大抵和仓促出版有关。
如此著作而成的作品,确实有失严肃,值得怀疑,但是这本书本身的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经过后期的修正,作者认为自己的根本性观点没有改变,即战争在东周的政治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霸权格局的更迭、封建制的瓦解、意识形态的选择,都无以战争为原动力。
这同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大相径庭,而且作者的一套逻辑体系总体而言能够证明这一观点,其观点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对作者研究方法的质疑 本书对核心观点的正式论述起始于第五章“西周体制及其衰落”,本章节分析阐述了东周政治发展形成的历史背景。《周礼》中对周朝的政治结构描述只是“应然”状态,而事实上,西周的政治格局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紧密相连,每一寸土地都受到统治。
相反,“野人”(即原理城邑而居的人)证明了不受统治的地域和人口的存在。这一证据从侧面证明了西周国家政权格局的破碎,国家和城邑权力的薄弱,将东周的争霸和战争在这种背景基础上加以解释,逻辑上的障碍较小,笔者认为这一章节的内容安排十分必要。
紧随第五章,作者在第六章探讨了东周的分期,这一问题的探讨毫无疑问是本书整体结构的总括,其后三章分别对作者所划分的“霸主时期”、“转型时期”和“全民战争时期”进行详细分析阐述。
作者所提出的“霸主时期-转型时期-全面战争时期”的三段分期法,对传统的“春秋-战国”二分法提出了修正,对整个东周的政治局势作了更加细化的分类描述。
笔者在这里比较感兴趣的是本书作者对“霸主时期”的政治格局的描述。霸主时期以“晋楚弭兵”为终结,作者认为,在晋楚弭兵之后,不再有强有力的霸主,整个霸主体系也渐呈瓦解之势,封建危机深化,进入转型期。
在“霸主时期”中,作者对整体政治格局形态的判断是:东周的霸主时期并不存在一个如同今天美国一样一超独强的霸主国家,而更多的是几大霸主并存的局势,战争主要发生于领国之间,并没有独霸中原的情形出现。作者将当时的中国分为东西南北四大战区,分别齐、秦、楚、晋为中心。
作者用了一个有趣的类比:四大战区的战争就像是现代体育中的小组赛,而齐、秦、楚、晋是涌现出来的小组冠军,晋楚争霸则是“半决赛”。 晋楚争霸之中,一般认为“晋强楚弱”,作者在本章中进行了批驳,结论是晋国并不占优势——这确实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作者在这里所采用的论证方法,窃难以苟同: 首先,作者以晋楚之间利益攸关的郑国为参考系判断晋楚两国的实力对比。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郑国不得不在楚国和晋国之间反复选择盟主,从齐桓公死后到弭兵大会,郑国与晋国结盟时间为48年,与楚国结盟时间为49年,以此得出结论晋国并不占优势。 然而,笔者以为,把结盟作为判断强弱的标准,其可靠性值得商榷。
借用国际政治中Walt的同盟理论,“结盟”这一行为主要分为两类:以权力均衡为目的的结盟(balance of power)和以“附势”为目的的结盟(bandwagon)。
在前一种情况中,一国倾向于同较弱的一方结盟,以平衡另一方的实力;后一种情况一般适用于较弱的国家,它们选择同相对较强的一方结盟,以寻求安全保护或者“搭便车”(free-ride)获取利益。显然,本书的作者只考虑到了后一种结盟模式,即认为郑国会倾向于和较强的一方结盟以寻求保护,争取到郑国的一方在彼时占优势地位。
但是,郑国虽然在当时实力不及晋楚,但也称得上一个二流强国,它不需要完全像弱小国家一样一味寻求庇护,“赵晋暮楚”未必是必然的附势行为,以结盟判断晋楚强弱的方法则容易失效。
作者在这里采用的分析方法简化了国家战略选择的复杂因素,恐陷入了单一逻辑的误区。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根据史书的记载,到了后期,郑国的结盟政策愈发实用主义,简而言之,谁来打郑国,就跟谁结盟(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
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 ),子驷、子展在对结盟政策的解释中说到“唯强是从”(这或许是作者结论的依据之一),但“主动进攻”这和实力强弱是否有必然联系?这就牵涉到作者采用的另一个参照变量。
作者采用的第二个变量是主动发生战争的次数。书中指出,在整个春秋史中,楚国主动发动战争的次数为111次,而晋国仅有90次,所以楚国的军事实力或许更胜一筹。
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假设是:一个国家主动进攻他国的次数越多,其军事实力则可能越大。但是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笔者这里再次借用国际关系领域知识加以类比,在国际关系历史中,一个国家的攻击性强弱往往是由战略目标、地缘因素、民族性格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所以,军事实力强未必意味着主动进攻。
比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德国挑起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的军事实力必然强于英法俄乃至美国等其他国家,德国挑起战争更多是出于地缘政治及其资源目标。
虽然国际关系历史未必适用于东周的情形,但是即使从逻辑上看,以进攻次数判断军事实力的方法也未必是站得住脚的,即使能够证明楚国发动111次主动进攻证明了其军事实力强大,也无从证明晋国没有楚国比其多出的21次战争是因为实力不足。
作者采用的第三个证明晋楚实力不相上下的变量是行军路程的对比。所依靠的前提与上条类似,即战争中的平均路程越长,这个国家的军事能力越强。
本书作者发现,齐桓公死后,在四个“小组冠军”中,楚国的行军路线是最长的。这种解释路径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楚国行军路线长也可能是因其地理位置。楚国是当时唯一的南方大国,而其欲称霸势必要向中原地区扩张,行军路程相对较远是情理之中;而晋国相较而言受敌面更多,其敌手的地理位置或许对其行军路程会造成影响。
当然,笔者的推测只是依据春秋地图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否有足够说服力,也有待进一步的阅读和研究。
其实,笔者对本书作者所得出的结论大抵是认同的,基本同意东周不存在一个单独霸主独霸中原的时期,几大霸主势均力敌不分上下。但是,对于作者偏向实证主义的论证方法,笔者表示不信任。虽然如作者所言,现有的其他学者的判断过多依靠《春秋》和《左传》,得出的“晋强楚弱”的结论很可能不符合事实。
作者的理科背景或许也促使其倾向于实证研究,但是试图通过科学性过强、过于模式化、数值化的实证研究方法证明变化莫测的列国关系、政治格局,未免有些冒险。
笔者认为史料依然比数据模型可靠,但是要更准确描绘春秋局势,则需要更多的、更全面、更具体的史料支持,而非抽象的数据统计,当然这需要更多的阅读和探索,笔者也自知以目前的知识储备,在此文中难以建立成体系的结论。
礼崩乐坏——效率驱动型文化的兴起 在霸权时期的后期,封建体系的瓦解已成必然之势。笔者还对本书中对“效率驱动型文化”的分析阐述十分感兴趣。西周王朝创建者所制定的一套复杂的礼仪体系以及背后的礼乐秩序以及濒临瓦解,最显著的表现则是在战争上。
春秋早期的战争还讲求胜之以“武”,不搞偷袭之类的行动,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像是仪式性的活动,按一套礼法规章按部就班,和我们所理解的战争大不相同。
不过随着战争的延续,尤其到了作者所分的“转型期”和“全民战争期”乃至“霸主时期”的后期,礼仪在战争中的影响就日渐减小了,所谓“不伤二毛”之类的规定不再得到遵守,号称重视礼仪的《左传》中,“曹刿论战”“子鱼论战”这样“胜之不武”的论述也受到褒扬,前文中提到的郑国“朝晋暮楚”的情形,若是遵守礼仪要求,是万不可能发生的。
作者把这一变化归因于战争的驱动,“为了在延绵的战争中存活下来” ,各国被迫改首要目标为生存,而原有的礼仪规范显然不能使得这种目标的实现达到最大化,于是在战争的驱动下,一种以战争效率为导向的理性政治文化逐渐兴起而替代原有的礼仪政治文化,作者称之为“效率驱动型的工具理性文化”。
礼崩乐坏不仅由战争的“必需”所导致,也受战争的后果所影响,这里的后果,不是简单的谁胜谁负,还牵扯到战后治理的问题。在争霸过程中,霸主国的地盘不断扩大,但是现有的管理结构并不足以支持扩大了的疆土,于是一国一般采取两种形式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将扩张的土地分封给贵族臣子,这就是所谓的“二级封建化”,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非常引人注意的一种现象。
笔者认为,这种形式的“封建化”只是形式上的分封,它只继承了封建制的“形”,而封建制背后的政治文化秩序非但没有延续,而且君臣原本的等级由于贵族军事权力的增强在实质上也受到了破坏。
从“三家分晋”的历史结局来看,“二级封建化”留下的后患是无穷的。 还有一种则是实行郡县制,当然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郡县制形态也是各不相同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很多“县长官”是有军事力量的,这无疑对诸侯国的政权构成威胁,楚国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有趣的是,在古罗马人的理念中,对占领地的人民进行武装是会巩固统治的,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提到古罗马人的治理理念就说,占领一个地区后最核心的措施应是训练军队、武装臣民,他认为这样才能维持统治,而不至于沾染被占领区的恶习。
而罗马帝国的解体似乎更多是奴隶起义和外族入侵造成,地方的武装似乎并没有威胁到中央政权。
统一源于战争? 毫无疑问的是,东周时代的二级封建化和郡县制对加速封建制的解体起着催化的作用,而究其根本,是战争在驱动着整个过程。
作者在此的分析可以说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是,作者在此书中似乎又过分地强调了战争的主导作用,将公共事业发展、国家统一的历史现象都归因于战争,却过于简单,就像朱大可把中国社会文化的种种现象都总结为“流氓文化”一样,似乎是不可取的。
比如作者在第九章之中摆出观点:“秦国统一中国是法家改革之后战争性质发生改变的直接产物”。其后作者说明了法家思想从两方面改变战争性质,成年男子及其他资源的增加及诸侯扩张欲望的膨胀。
接着,他又分析了为何不是其余六国统一中国的因素,也是从军事的角度。作者的这一系列论述,是为了驳斥“秦统一天下是由于当时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民众渴望获得一个和平的环境”的说法。这种说法确实带有史学家一厢情愿的意味,但是,因为战争性质变化导致统一的判断恐怕同样没有足够说服力。
况且,作者在书中还将诸国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行为归因于战争需要,淡化自然灾害、经济发展等因素,笔者认为这也是欠妥当的。
笔者比较信服的是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的解释。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借用地理知识,从黄河沿岸的地理气候条件着手解释政治统一的趋势。黄河裹挟着大量泥沙,经常淤塞河床引起泛滥,所以最后又一个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并有威望动员所有资源,消除灾害;而中国地区的降雨又极具季节性,锋面雨可能导致霪雨成灾,封建割据的政治局势极易造成“以邻为壑”的水利工程,所以孟子说“定于一”,只有统一,才有安定,就是遵循的这个道理。
笔者认为,黄仁宇的“自然驱动”的解释比本书作者的“战争驱动”层次更深,说服力更强,在统一的过程中,战争更多还是充当一种手段,而不是动因。 总之,赵鼎新先生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提供了一幅东周历史的图景,其战争驱动的核心思想在解释有关东周历史的很多问题上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笔者对其研究方法和解释逻辑存在一些质疑,在此略陈一二,至于更深此的探究,需要更深刻的探究,在此并无能解剖透彻,有不足之处,见谅。
参考文献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赵鼎新:《霸权迭兴的神话:东周战争和政治发展》,《学术月刊》,2006年2月。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