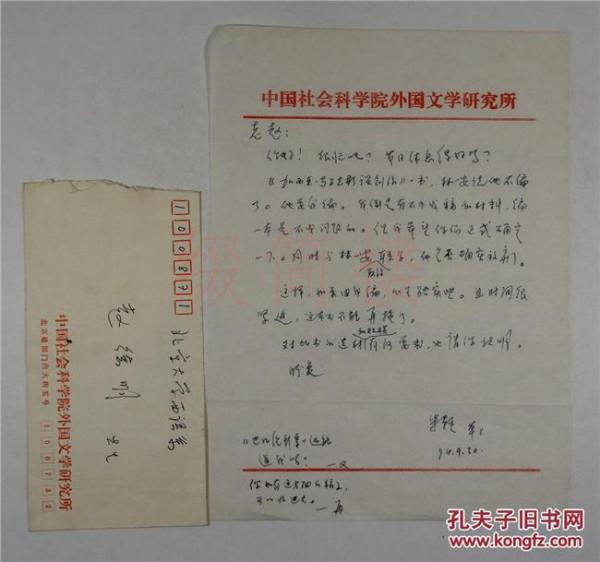赵鼎新儒法国家 赵鼎新:中国“儒法国家”的形成
东方历史评论: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关于社会运动、社会抗争等研究之外,赵老师对中国历史也有不少自己独特的看法,如曾出版过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但这个话题此前尚未进一步展开,听说最近你也在构思新的相关著作。我们的访问首先不妨从你对历史的兴趣开始,我注意到此前你在书中提到,最早对中国古代史的兴趣来自文革时参加的批林批孔小组,那是你第一次接触到法家等典籍,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
赵鼎新:其实大家在国内看到的那本小册子(即《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是我花了三个月写出来的,但是我最近整整十几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这一研究目前刚刚告一段落。英文著作题为《儒法国家:一个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今年11月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历史兴趣在我是天生具有。我小时候就不停问父母、祖父母、曾祖母他们所经历的事情。还有,我小时候特别怕死, 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社会,我也不可能从宗教中获得解脱。我于是总是想学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想从历史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
但是我有兴趣却没书看。如你所言,一直到了批林批孔的时候我才有机会接触那些典籍。最后,我们这一代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的线性史观、特别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虽然我早就不认为历史遵从着任何一个总体性的规律,但是我始终保持着寻找历史规律的兴趣。
东方历史评论:我想知道,你到宁夏之后,如何被“选”进工厂的批林批孔小组的?
赵鼎新:我所在的工厂有一个宣传干事,据说他是秦牧的学生,文革中跟着秦牧倒霉,被分到了宁夏。他蛮喜欢我,在搞批林批孔小组的时候把我也安排了进去。当时一个星期要上六天班,小组的人只用上五天,有一天可以专门看书。
而且厂里还拨了点钱用于购书。但是我马上发觉我们小组其实不是在研究历史,而在机械地把法家看作是进步力量的代表,把儒家当作落后势力,并把某些当代人物乃至厂里的某些领导写成当代的“儒家”进行批判。换言之,小组其实很容易成为他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当时我的理解并不像今天表述得这样明白。
当时除了看郭沫若、范文澜、杨国荣之外,我们还看了一些原著。原著中的内容往往会对我们接受的教条形成挑战。比如,《盐铁论》让我知道了当时支持私人商业发展的不是所谓的法家而是儒家学者。还比如,在文革儒法斗争的叙事下苏轼是个两面派,但是多看了一些材料后不难发觉当时的问题主要是党争,苏轼比较平和的性格使他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打个比方,批林批孔小组中有一个朋友很教条,文章写得像小姚文元,大家不喜欢他,但我却一点不恨他。这是因为我与他很长时间同住一个寝室,对他了解多一些,因此人家骂他我还为他说好话。假设我们的批林批孔小组也分成了两派,那我可能也会被算成两面派。
我看问题不极端,遵从常人逻辑,因此很难接受儒法斗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这种说法。在批林批孔小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篇文章都写不出来。宣传干事对我很失望,骂我不求上进。
东方历史评论:在进入“儒法国家”这个核心话题之前,让我们由儒、法进而推至诸子百家,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那是思想史上一个辉煌时代。不过你此前曾提及,诸子百家与西方思想史的先贤相比,存在很多局限,也由此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具体而言,你认为中国早期的这些思想家,其根本或共同的“局限”是什么?
赵鼎新:也不好说局限,一讲局限就好像诸子百家不如他们(西方思想家)。应该说是有显著差别。
第一,诸子百家文章的最主要对象是国君,而希腊思想家文章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每个人都想被国君看中,不管是骂还是在捧,一心都系在国君身上。这是因为国君听了你的话,你的话才有用,才会变成政策和改变社会。
第二点,希腊社会强调个人,人际关系纽带较弱,联系的紧密度相对较弱。这给希腊思想家提供了一种探索两个因子在不被其它条件干扰下它们之间因果关系的可能性,给了西方哲学一种片面深刻。这种片面深刻为理论理性和形式理性在西方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为现代科学的出现打下了契机。
在紧密的人际关系下,中国思想家看到的更多是多重事务之间的联系。他们因此很难把问题进行割裂,并且对脱离情景的因果逻辑不感兴趣。中国人的特长是系统性思维和相关思维。
比如“天人感应”理论把自然现象与社会想象看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吃红色食品能补血这类思维方式就是相关思维的体现。我年轻时觉得中国出不了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相比,孔子连定义都不会,人家问他什么是“仁”,他总是给你一个不同的具体例子。
后来我才懂得,孔子有他的深刻。 他显然认为“仁”这个东西放在不同的场景下是有不同意义的,任何事务都需要放在历史情景下加以理解,一旦给出一个超越情景的定义就片面了。
第三,与希腊哲学家相比,中国诸子百家有着很强的历史理性,或者说从历史经验中找行为准则的冲动。这点不但儒家和道家如此,就是厚今薄古的法家也喜欢用历史“先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中国思想家历史理性比较强,西方思想家理论和形式理性比较强。
文艺复兴以后,理论理性和形式理性在西方被重新找了回来,这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西方人片面看问题的方式也会给自然科学的应用、社会科学的发展,乃至世界政治带来误区甚至是灾难。
东方历史评论:我们谈谈法家。一个主流的看法是,秦国因采取了法家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改革后得以崛起并统一中国,汉代则继承了这种制度。在你的研究里,显然事情却没那么简单,我注意到你的研究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作为脉络,那就是“战争”。
从早期的争霸性战争,到后来的全民战争,你认为战争主导各国之间的互动,致使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一个长期处于二流国家的秦国最后胜出。那么,着眼于这种“战争”研究你有着怎样的考虑?说到战争如何影响诸国关系进而影响历史的走向,你能否言简意赅地描述其关键何在?
赵鼎新:战争和做生意共同的特点就在于,输赢清楚。输赢清楚的竞争一旦在社会上形成主导就会导致工具理性的增长。人类有两种本能性的指导自己行动的原则,一种是“对的我干,错的我不干”,这就是价值理性;另一种是“合算的就干,不合算的不干”,这就是工具理性。
(先前所说的历史理性、理论理性和形式理性都是辅助性工具。使人能更好地发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春秋早期,价值理性是贵族行为的主宰,以至于出现宋襄公半渡而不击这种行为,即使打仗也要讲道德。
但是在一场战争中,如果一个讲道德的对手面对的是一个同样强大的怎么合算怎么来的对手的话,恪守道德的对手往往会输掉。这结果就会导致大家慢慢都只争输赢不讲道德,工具理性成为主导。
但是先秦中国和前现代欧洲有很大不同。在欧洲,在战争越打越大的同时,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商人的权力也不断越高。商人与在战争中不断加强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合作为君主立宪、代议制民主、民主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先秦中国和前现代欧洲最大的不同是,欧洲是军事和经济竞争同时主导着社会变迁,而先秦中国主导社会变迁的动力主要是战争。先秦中国打仗,打着打着就打出了官僚体制,打出了常规军队,打出了国家更强的税收能力,打出了私有制,打出了小家庭(因为家庭越小,税收越容易且税收量可能加大),最后打出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就是法家学说。
在没有社会力量的牵制下,法家是一个最有效的战争动员理论。早期的管仲、晋文公等人都具有“法家”性质。这类思想到了战国开始系统化,出现了法家。法家改革从魏国首先开始。魏国改革的历史意义与欧洲出现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相似。它们都不代表历史进步,而代表一种同构压力(isomorphic pressure)。因为打仗输赢清楚,所以打不过人家就必须学。魏国改革之后各国纷纷效仿搞起了法家改革。
但是,秦国统一中国的背后还有其它的因素。第一,秦国的地理优势。夺取了四川后,秦国占据了长江黄河两条河流的上游。这等于控制了两条顺路的“铁路”,人家逆流,它则顺流下去,运输又便宜又快。第二,秦国面对敌人的面向较少。
当时有两个国家的地缘政治最优越,一个是秦国一个是齐国。但齐国处在一个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当时临淄已经可能有二十多万人了,日子过得不错,你让谁去打仗? 齐国虽然富有,但齐人却不是好战士。秦国人作战勇敢,地缘政治好,改革又比较成功,最后成为赢家。秦国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法家改革,所以秦国统治者对这一套很自信,认为马上能打天下,也能治天下。秦国因此垮得很快。
按照标准的说法,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并非如此简单。秦始皇怕死搞方术,相信阴阳五行。如果去看秦始皇的碑文,他也提孝道,儒家这一套也是有的。秦始皇的脑子可谓是大杂烩,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浆糊,就像现在的一些领导脑袋中装了各种浆糊一样。
但是有一点历史学家没说错,秦始皇在国家的重要政策领域采取的主要是严厉的法家方针。但是古代国家没有铁路,没有现代通讯设备,也没有现代的警察和国安部,怎么可能把人管住?我们看《史记》,在造反之前刘邦在哪儿?躲在山上。
项梁在那儿?在山上。英布在那儿?在山上。张良在那儿?在山上…… 秦朝虽然很专制,但是它能管到的地方有限。因此六国的“异议人士”大有藏身之处。当然,这些人躲着也不是专门为了以后造反。如果是在清朝,这些人就会像遗民一样在山上等死了。但是秦的暴政和宫廷内斗给了他们机会。
汉初统治者知道搞秦朝这套肯定不行,但是它们并未领略到儒学的好处。汉初精英的价值观是个大杂烩,但是国家的统治策略却是以黄老为主。黄老采取了道家的许多精神,但它也是大杂烩时代的产物。黄老强调无为而治,汉初因此形成了一个以“看不见的手”治国的局面,并出现了“文景之治”。
但是,汉统治者不得不面对两个新问题:经济繁荣带来了人口飞速增长、贫富差距加大和地方豪强并起等问题。“无为而治”并不能解决这类问题。此外,黄老是统治术层面上的东西,它不能为国家提供一个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儒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被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
需要强调的是,汉朝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是经过改造后形成的“官方儒学”。儒学是一个活的东西,其内容和社会影响在历史上始终在变化。还有,我们一般讲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集大成者。但是,董仲舒在他活着的时候是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
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同时代人物,在他的《史记》中才提过董两次。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并且在东汉才逐渐完成了所谓的圣典化(canonization)。董仲舒就是在这圣典化过程中被吹大的,在《汉书》中董的传记占了整整一章。
最后,汉武帝虽然把儒学上升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但是他用的人杂七杂八,什么样子的都有,他的大量政策也是以法家为主。汉武帝时期形成的那种以儒学作为统治意识形态,以法家手段进行统治的做法逐渐发展成了古代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并且一直延续到清末。
东方历史评论:无论如何,儒家官方意识形态一直持续到清代的终结,在漫长的历史之中虽经历了种种社会变迁和挑战,但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对此背后的原因你有着怎样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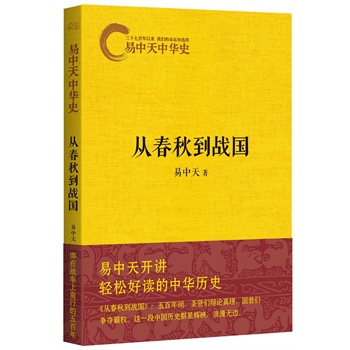













![>《“新批评”文集》(赵毅衡)扫描版[pdf]](https://pic.bilezu.com/upload/4/42/4429fbd535c4caabeed8ecf52a3bfe65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