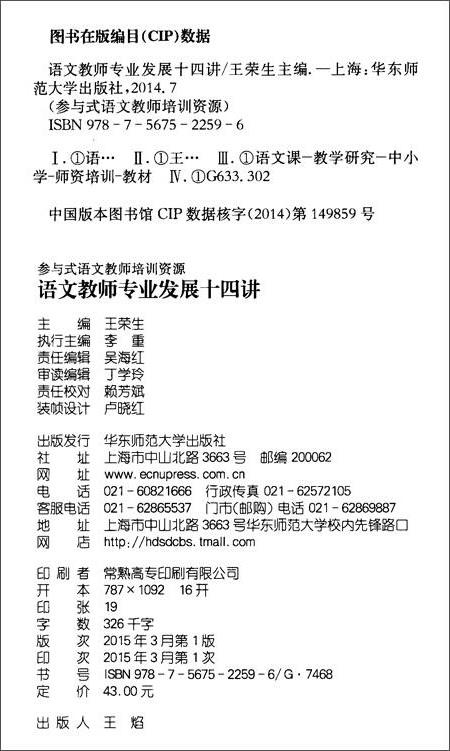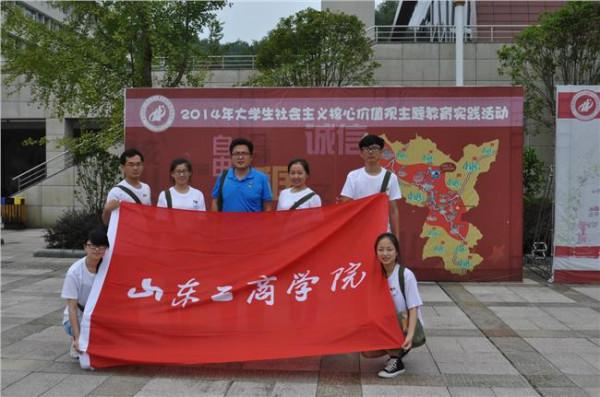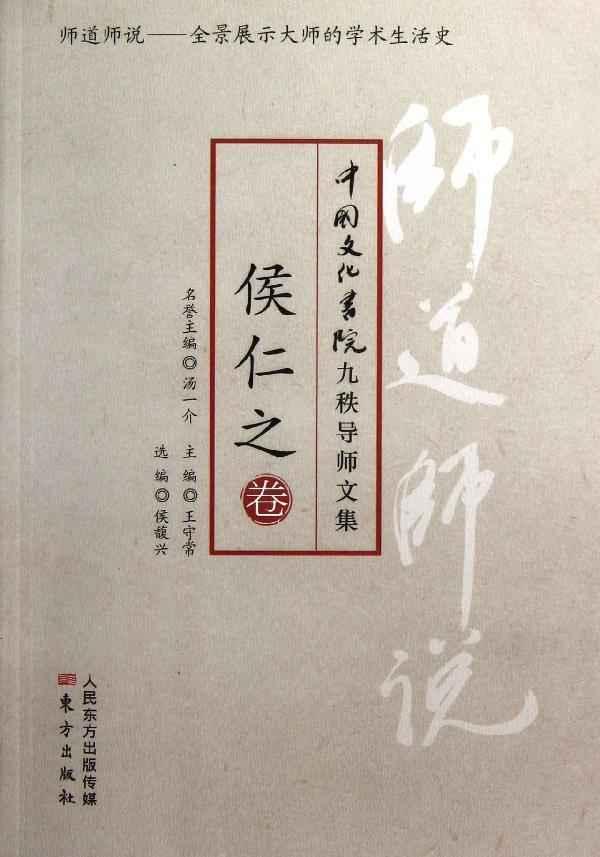费孝通的老师 费孝通的外国老师 | 共同体精选
一次,学生随派克参观中国法庭现场。他看到法官们懒洋洋的做派,回身对学生说:“要是光阴值钱的话,中国是世界上的首富了。”
派克对燕大学生的最大影响,是带他们跳出未名湖畔小圈子,进入真实、生动、丰富的社会实际生活。他启发学生把北京当成社会学实验室,鼓励大家研究活生生的实际生活。

跟随派克,学生们往永定门,去天桥,在地摊、戏棚、店铺、流浪艺人、贩夫走卒、地痞流氓辐辏一地的市井社会,现场观察实际生活;也曾到过监狱,看高墙内的囚犯生活。
费先生在监狱第一次给犯人测量体质,看到有人浑身上下一个个黑点,得知那是扎针吸毒疤痕,感到触目惊心。

面对派克为他们打开的世界,费先生领悟,不是每个人都像自己一样生活。过去寄身的生活圈子太小,实际社会生活开阔得多。
派克的开风气之举,在燕大社会学系激起一阵“派克热”。费先生当年一段文字,或能代表众人感受 —他所给予学生的印象决不单是一个诲人不倦的教授,亦不单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社会学家。……他所给予人们的不是普通的知识而是生命,一种能用以行动的知识。

他生平尚没有任何惊人的巨著行世,就是那本用以授课的《社会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还是多以参考资料汇集而成,大半又假手于他的同事伯吉斯。他所以能享受着芝加哥社会学派正宗的尊荣,实是因为他有一种魔力,能把他的学生从书本上解放出来,领到一个活的世界中去领悟人类生活的真相。这是他在社会学界树下的百年基石的工作。
费先生意识到派克的特出成就,遂留意其学术思想的师承渊源。在他为派克论述中国的文章所写按语中,曾做初步介绍。
派克在哈佛大学期间,适逢杜威(John Dewey)、桑塔亚那(Santayana)和詹姆斯(William James)几位大师同时开帐讲学。派克躬逢盛事,如沐甘霖,转益多师,兼收并蓄,从詹姆斯那里得到的精神营养尤多。
詹姆斯的思想在传播过程中,一方面被认为太难捉摸,不能成为一个学派的教义,另一方面又确曾在英语国家中广泛流传,成为主流思想。“这种哲学的作用与其说是建立了供他人模仿的标准的旧体系,不如说是向他人灌输了新的思想。”
派克更喜爱詹姆斯学说的原因,应该在这里。在华讲学期间,他曾对班上同学说:“所谓科学,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只是能讲得出来,讲了人家懂得,可以试试的一种个人经验罢了。”
这话,费先生入耳入心。他没有辜负派克点拨,此后几十年里,他写出的大量文章都有“能讲得出来,讲了人家懂得”的特点,众多读者衷心喜爱。
一九九一年,费先生为《行行重行行》写前言,从中可见派克主张的深刻影响:“我所看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我所体会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我所写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而且,又习惯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下笔很快,不多修饰,……至多不过起些破题和开路的作用罢了。”
派克的主张,来自他在詹姆斯那里呼吸到的自由空气。他懂得这种空气对于学术的重要性,把这空气从西方带到东方,从美国带到中国,从芝加哥大学带到燕京大学,从自己的课堂带到吴文藻的课堂,为正在寻找出路的学生启发了思路,为“社会学中国化”启发了现实方法和具体途径。对此,费先生心领神会。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燕京大学临湖轩中,众人欢送派克离华返美。
这位美国名教授的答词中,屡次提到他的老师詹姆斯的话,希望同学们展开生动活泼的社会学研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社会学对国家进步应能作出的贡献寄予厚望。
派克说:“我在中国的时候,的确认识了很多学生。……我在他们中间所见的,不是昨日的中国,也不是今日的中国,而是明日的中国,是将来的中国。”“中国已经生活在它过去中这样的长久了,现在可以开始生活在将来之中了。”
外国老师(二)
俄国学者史禄国
史禄国是个杰出的俄国学者。他大学毕业之年,费先生出生。
作为俄罗斯帝国科学院的后起之秀,史禄国二十六岁上当选院士,三次参加国家直接资助的人类学实地考察队。
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他多次到西伯利亚、蒙古和满洲地区做实地考察,是研究通古斯人的权威。
一九一七年,革命大潮汹涌,在俄罗斯国家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安排下,仍有机会赴西伯利亚进行科学研究。
此后,因政治因素,其命运突然逆转。过去一路上地方官员的殷勤相助,变成冷眼相向,且处处与他为难。
旅程艰辛,行李遗失,资料被窃,心境凄凉。最后无奈远走海参崴,别离祖国,漂泊异乡……
特殊经历,加上天才人物异于常人的性情,使史禄国流露出一种需要他人更多地予以理解的落寞寡合。
据费先生说,俄国十月革命时,史禄国正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研究通古斯人。他不愿回到革命后的俄国,在中国留了下来 , 进了中央研究院。后来因为与同事们合不来,转到清华大学任教。
清华园里,史禄国孤僻难近,遗世独立。每星期到教室讲一两堂课之外,整日闭门写作。傍晚出门,与夫人携手散步,绕清华园一周即返。每天如此,极少与人交往。
费先生能被他收作弟子,并非容易。为促成这对师徒之缘,吴文藻下了一番功夫。费先生后来回忆说:“人类学在中国当时还少为人知,我投入他的门下,成了他所指导的唯一的研究生。”
《清华大学史料汇编》第二卷下册第五百九十五页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社会学部于一九三三年度成立,录取研究生费孝通一名,在校研究两年,于一九三五年研究期满。该部于一九三五年暂停招生。
“暂停招生”显然与当时唯一能指导人类学训练的史禄国在当年离开清华大学有关。
表面孤僻冷漠的史禄国,对学生有高度负责的热忱。他为费先生制订了六年训练计划: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各两年。
费先生由东吴转学燕京时,告别了研究医学所需的生物实验室;师从史禄国之后,又回到研究人类学所需的生物学实验室。沿着这个螺旋式轨迹上升,他进入了体质人类学堂奥。
在教材《人体的历史》中,费先生要去熟悉其中对从单细胞生物发展到人类的过程中各类动物进行的典型解剖,理解生物演化;熟习有关理论的同时,还须花很多时间解剖多种大小动物;然后学习测量人体,接受进一步训练。
训练固然严格,史禄国却从不把着手教,他是要培养学生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本领。费先生在《人不知而不愠》一文谈到当时情况:“他从来不扶着我走,而只提出目标和创造条件让我自己去闯,在错路上拉我一把。他在体质人类学这一课程上从没有做过一次有系统的讲解。”
史禄国专门为此借了一间实验室。该室钥匙有两把,老师一把,学生一把,以利费先生独自工作。当然,任何时间,史禄国都能开门,看费先生的工作实况。
事实上,师生俩在工作室里见面不多。那两年,史禄国主要工作是编写、刊印其巨著《通古斯人的心态》。
每天的多数时间是在他自己书斋里。只是因每天傍晚总要和夫人一起散步,经过生物馆时,即可进入工作室,考察费先生的作业。此时,费先生大多已回宿舍。
费先生说:“他正好可以独自查阅我堆在桌上的统计纸,看到错误时就留下‘重做’的批语。我一看到这字条,就明白一个星期的劳动又得重来了。”
其时,费先生整天埋头工作室,借助算盘和算尺进行计算,对数据资料做分析。史禄国只准许他用这两件工具进行工作。
费先生曾问史禄国,为什么不可以用比较先进而省时的计算工具。俄国老师正色答道:“你得准备在最艰难的条件下 , 还能进行你的工作。”
这句话给费先生留下极深印象。从以后历史看,可以说这是对他一生坎坷中坚持学术研究先见之明及其预嘱。
随着时间的延伸,费先生发现,这位俄国老师孤僻、抑郁的外表下,是多才多艺、丰富浩瀚的精神世界。史禄国学养深厚,善于绘画。在其《北方通古斯》一书中,有两幅他自己绘制的彩色插图。
他曾特意告诉费先生,用绘画来写生,比用摄影手段更能突出主题。
二十多年后,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至九日,费先生在《云南日报》连载《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长文,配有他自己临摹的剑川石宝山石钟寺石刻像两幅素描。
其中可见史禄国的影响。
史禄国的夫人善弹钢琴。费先生在史禄国书房里同他谈话时,常能听到隔室琴声。偶尔,史禄国会停住话头,侧耳倾听流泻的旋律,流露一种难得一见的神采。
一九三五年,费先生结束了史禄国为他安排的首期训练计划。
依清华惯例,教授工作五年后有休假出国一年的权利。当年正逢史禄国休假期,也许其处境又有变化,他决定这次欧洲休假后不再回清华任教,因此为费先生做出了新的安排 — 一九三五年暑假后,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年调查,翌年由清华公费出国留学,直接到欧洲去进修文化人类学。
费先生的两位外国业师中,马林诺斯基予其荣誉极大,史禄国予其影响极深。费先生晚年写文章说,两位老师的东西,他都没能学到家。
外国老师(三)
马林诺斯基
费先生出生当年,马林诺斯基进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费先生开始读小学之年,马林诺斯基获得该院博士学位。费先生进该院其门下读书时,马林诺斯基已是人类学界功能学派大师级人物。
师徒见面之前,马林诺斯基先从吴文藻口中听到了“费孝通”的名字。
一九三六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马林诺斯基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主任名义出席庆典,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也在现场。马林诺斯基特意与吴文藻联系、晤谈,见到吴文藻带的一份中国社会学界开展社区研究的计划文本,其中包括费先生已在推进中的课题。
马林诺斯基记录与吴文藻会谈的心情:“我接待了燕京大学杰出的中国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来访,感到极大的欣慰,从他那里得知,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的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进攻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梦寐以求的愿望”说来话长。
马林诺斯基原籍波兰,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语言学家。马林诺斯基读取大学博士学位后,偶然读到人类学经典著述《金枝》(TheGolden Bough),受到强烈吸引,开始热切钻研,为此留学德、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又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从事人类学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马林诺斯基正在太平洋一个英属岛上做调查。战争起,波兰与英国敌对,他不能离开该岛。无奈中,他学当地语言,融入土著生活,观察岛民举止、风俗,留下记录。
活动受限,不能远游,成全了马林诺斯基长期在 一个小部落做研究的机遇。
“一战”结束,马林诺斯基回到英国,以大量一手资料著述、出版《西太平洋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轰动人类学界,一举成名。
费先生说,英国人对外籍学者偏见很深,马林诺斯基一跃而为教授,享盛誉,入英籍,在英国学界很少有。
英国各大学设立社会人类学教授讲座,也是从马林诺斯基开始。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培养的门生,多成为各大学人类学系的台柱,且受英国殖民部和美国洛氏基金会直接支持,每年掌握大笔调查经费,调度大批调查工作者,到非洲各地进行研究。
不到十年,功能学派的声势压倒了人类学里其他派别。
此后,“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提问题,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学学术常识的一部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马林诺斯基的成就,感召众多学者走出书斋,躬身田野,为人类学注入生机,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收获一项项成果。
斗转星移。不到十年,当初富于开创性和发现意义的田野调查,逐渐演变为日益娴熟的职业化操作;当初研究成果中由发现带来的惊喜和思考,逐渐变为程式化调查和程序化描述时的漫不经心。马林诺斯基不满地说:“我们中间绝大多数向前看的人类学者,对我们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我们厌烦它的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
在这种心情中,听吴文藻一席话,马林诺斯基从中国学者的学术攻关中看到了摆脱“厌烦”的现实途径。
尤其让他欣喜的是,处在这一学术进攻前沿的费先生已抵达他主持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专攻社会人类学。马林诺斯基即向吴文藻表示,有兴趣培养一名中国人类学者。
马林诺斯基从美国回到系里时,费先生已开课月余。
费先生很快见到了这位人类学界的大人物。“一个高度近视、光头、瘦削、感觉很敏锐、六十开外的老头。”
“老头”约费先生喝茶,询问到校后的情况,确定师徒关系。
费先生如吴文藻所愿,正式登堂入室,成为马林诺斯基及门弟子。
两年留学生涯,费先生的主要学习方式是参加马林诺斯基每星期五下午主持的研讨会,当时的通行名称是Anthropology Today,一般译为“今天的人类学”。
费先生一般也用这个说法,但他更喜欢用“人类学的前沿”或“赶上时代的人类学”去理解这个名称。
如此译法并不通行,却表达出对马林诺斯基用意更贴切的理解。
研讨会进行过程中,马林诺斯基不多话。主讲人宣读准备的文章,或是调查报告,或是对某个问题的系统意见。马林诺斯基借其所讲内容提出问题,把握方向,推动讨论。他不喜欢讲空洞理论,要求每人都围绕调查到的事实说话,不空谈,自己当然也不例外。听到高兴处,他会即兴插上一席话。这样的插话就是学生希望、珍视的“指导”了。
马林诺斯基对费先生的培养,不光是在研讨会上,其他地方也多有用心之处。他介绍费先生住进伦敦下栖道一位朋友家,以利其接受中上层社会气息的熏陶。他还把这位中国学生请进自家,耳提面命。
费先生也喜欢到导师家去,那里有他倾心的学术气氛,有导师著书立说的工作现场,有“老头”的谈笑风生和大发雷霆,有师徒之间慢慢滋生出来的叔侄般亲情……费先生的博士论文通过当晚,马林诺斯基留他在家中吃饭,并把刚获通过的博士论文推荐给伦敦劳特利奇书局出版。书局老板希望马林诺斯基能写序言,得其爽快回答。
本文选自《书生去——杂忆费孝通》一书,为“共同体别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