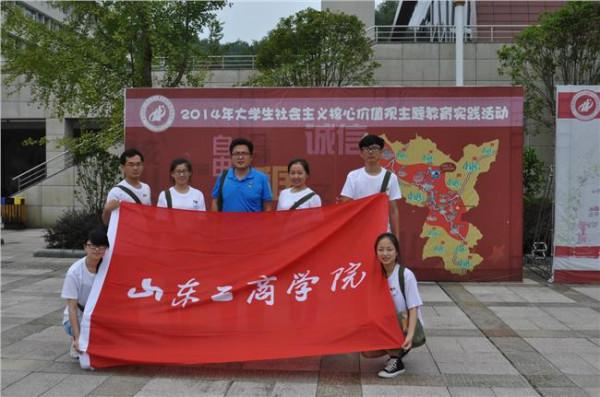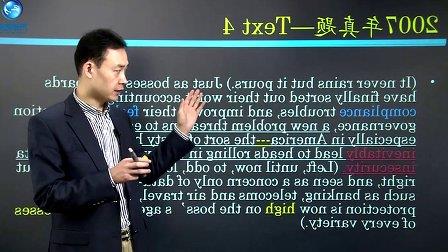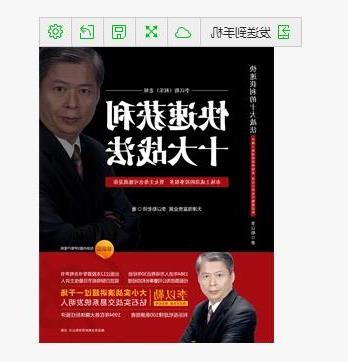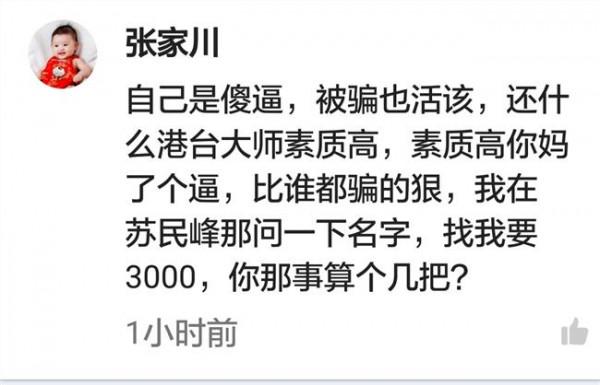我眼中的张大文老师以及张老师对我的影响
我眼中的张大文老师以及张老师对我的影响
华东师大 周宏
张大文老师不苟言笑是公认的。有一次,林老师在诧异中带着兴奋说:“远远地在马路对面看到张老师,便点头招呼。哪里知道,张老师高举手臂,满脸灿烂朗声道——“嗨”。
学生向我抱怨说:“张老师真怪,我们看到他问张老师好,他答曰——好个屁!”
太反常了!其实这正是张老师的常态。我知道,张老师此时此刻一定眼中没有看到任何人,因为他正与他思考中的某个人、某件事、某个场景相逢。——张老师的专注是雷人的。
班上出现失窃现象,我抓住机会想对学生进行系统教育:对行窃人,要明白占有不该占有的东西,看到它只会眼烫心慌寝食难安,它将成为一辈子的伤疤;对于失窃人,要懂得珍惜和责任,要学会养成一丝不苟、井然有序的生活习惯;对于周围人,要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义”,保护和善良要用对场合,否则就是助纣为虐。
每一件事发生后,要学会换位思考,从中获得人生的成长。就这事在与张老师的讨论中,张老师教导我:“假如我有钱要放到抽屉里,办公室只有你我俩人,我一定会当着你的面把抽屉锁好。
你不要因为我在提防你而不高兴,其实我是在保护你!而且,即便真的遗失,我也不会让自己心生半点怀疑你的理由和可能。”有谁对朋友会这么赤诚,不容怀有芥蒂,哪怕一丝的念头也无可能。我把这道理告诉我的学生,学生们若有所悟!我相信,这将在他们的人生中成为格言,引领他们做人。——张老师对朋友的感情是深沉的。
已故的曹天任校长在位时,从来没有听到过张老师与他有任何的私交。只听张老师有过一两次这样的评价:“曹天任看人是准的。”退休后的曹校长罹患癌症,并与病魔苦苦斗争长达十年。期间我偶尔听说,曹校长化疗每周一针,价格昂贵,为节省开支,去医院是坐公交的。闲谈之中跟张老师说起这事。没过几天,张老师要我赔他去看曹校长。
张老师让女儿买了女儿才送了他的一台一模一样的DVD机,让我陪他到福州路音像店买了几乎全套的京剧名家的光碟,然后来到了曹校长家。张老师说曹校长爱听京戏,他觉得女儿的DVD很好,就想着让曹校长也能享用。临走时,张老师放下了壹万元,说看病时就用它打出租车。曹校长断不肯收,张老师说:“我比你大,我拿你当兄弟!”
“兄弟”这词,平时听来总觉得有一些江湖气,那次听来却特别有分量,我看到曹校长眼中的泪光。
张老师眼见得兰生复旦中学在周校长接任后的变化,他更加乐意能为兰生做点事。他顾问兰生的语文组,对后辈关爱有加。手把手教不够,就亲自示范,就与青年教师一起上课,对比得失,一个个细节打磨。
周校长去年住院动了手术,张老师知道后心痛地说:“太辛苦了!”过了些日子,他让我告诉周校长:“周是余姚人,我来请客,到我余姚老家住五星级宾馆休养几天。”他伸出拇指,神气而带着保证似地说:“五星级,不差的。”我答:“周校长是不肯受人恩惠的,不然,就要成为负担,她一定会想方设法加倍奉还的。”
张老师其实是极其节俭的,烟酒不沾,一季两套换洗衣服,夏天衬衫洗到变成薄纱,他说穿着凉快。张老师对生活几乎没有要求。他常说:“泡饭过花生酱在我也是有滋有味的。”朋友送的拎包,他用到已经完全没了正型,而且我也早注意到皮包的破旧又送了一个新包,但张老师说:“这包皮质很好的,把手修修还可以用很久哩。”
张老师对自己几近到苛刻,但他对自己认定的好人是慷慨的。就我知道的,早年他去云南讲学,看到那里孩子上学的艰苦,就捐了叁万。在曹校长住院期间,有一次是我陪张老师探病,张老师在枕下放了壹万。——张老师待人是真诚的。
复旦附中45周年校庆,语文组出了一本历届学生优秀作文选。当时是张大文、王德宏任语文教研组长。作文选是由东北的某家出版社出版,大概是沟通上出现了疏漏,出版社责任编辑想当然地就把此前作为联络方的语文教研组作为了主编,写上了张大文、王德宏的名字。
不想惹来了轩然大波。老先生勃然大怒,兴师问责到张大文。不明就里的张大文既感到无辜,又无法改变已成的事实,面对老先生的愤怒也只有愤怒了!
那天大概是张老师晚自修值班。已经是九点多了,怒火难平的张老师把我从家里喊出来,一通火全撒到我这儿。听着听着,我大概听出了原委。一个潜心于自己钻研,不愿意“嚼自己嚼过的馍”的张老师,一个追求不断突破自我的张老师,哪里能够容忍别人对他施加“剽掠侵占”的罪名,更何况是一本学生的作文选!
一个把名誉和清白看成生命的张老师,哪里能忍受这样的羞辱!震怒与咆哮声回荡在我家小区门口的马路上。这一骂就骂了近一个小时。围观者不能明白,只是看到这等的愤怒,大概明白了什么叫冤屈。
那次出版的作文选,除了学校校庆时用去的一部分,大捆大捆地堆积着,作为语文教研组长的张老师,大概看到它便会戳心境,深锁在大柜子里。几次搬办公室时,会看到上面厚厚的积灰在一次次增加。——张老师的生命里是不容污点的。
刚进复旦附中不久,我把语文教育看得很轻,以为随便就可以对付一节课的。记得有一次要上公开课《守财奴》,头天晚上一伙人还在聚餐凑热闹,待说明天要开公开课了,朋友说聚好回去再一起帮我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拿到朋友对课文的近二三十个推敲提问,灵机一动:不就是小说吗?梳理出小说的情节结构,做好人物性格分析,贯穿以问题推敲。这样就算是搞定了。当天的课也没出任何状况,按部就班地完成了。
当晚正值我和张老师排在同一天晚值班,临要结束前,照例打扫办公室。我从办公室这头扫起,张老师从办公室另一头扫起,扫到办公室中间会合,来到附中才三年的张老师第一次开口跟我说话:“葛朗台的性格是一锤定音的,用情节发展来分析人物性格是没有意义的。
在整个情节中,每一处提问——表现了葛朗台怎样的性格?答案无非是——守财,守财,守财。这有意义吗?你应该想:这个守财的葛朗台,随着情节的发展,他的守财表现形式是各个不同的。
比如:他捧来金子,撒在床上,对欧也妮说,拿去吧,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表面看大方得很,并不守财,其实本质上是守了更大的财。这是你要真正解决的问题。”
就这一段话,可以说有一语点醒梦中人的感觉,当时就让我无地自容。
从此我开始了对自己浑浑噩噩的语文教学的思考。
也是这一次,我开始对张老师有了一份敬畏和恐惧。
但直到又过了两年多,我才真正有了与张老师在同一个备课组的机会,连续听了张老师三年的课。——张老师的一席话,改变了我的语文教学生活。
张老师其实是极爱学生的;可是他表现出来的却是对学生近乎苛刻的严厉。在教学上他对学生不会有丝毫的马虎,他也绝不允许学生对学习有丝毫的马虎。在附中,张老师发脾气是出了名的,每每把脾气发得震天动地,在有些老师看来几乎失了体统;可每一次的脾气到底都是为了学生学习得不认真,学习作风的不踏实。
在一次早读课上,张老师发现学生没能认真阅读,再一查作业,又没按要求很好完成,于是怒从心头起,一通脾气爆炸开来。
张老师的本领在于在发脾气数落训斥的时候,他能把犯事人的陈芝麻烂谷子的档案全部调用出来,一并算账。发火表征是骂,骂不够还要借助道具,于是拿起桌上的搪瓷碗就往地上摔。
那时刚领教张老师的脾气,吓得大气不敢出,只能小心将张老师摔在地下的碗捡起来;张老师拿起碗再摔,以解心头之恨;我再捡,他再摔。终于我明白捡起来只是促进他的摔,于是任由那个滚落到墙角的碗打着转扣地而卧,碎搪瓷掉落一地,千疮百孔的碗裸露出黑乎乎的生铁,张老师骂够了,摔够了,一场暴风雨才结束。
但是奇怪的是,被骂过的学生待长大离开学校一样会和张老师成为朋友。这大概有学生走出高考考场高呼“张大文万岁”为证,大概可以以张老师虽不做班主任却对学生进行家访,能说出学生的爱好的事实为证,大概可以就张老师每个假期坚持和每一位在读学生通信为证。——张老师对学生是赤诚相待的。
和张老师相逢、相识到现在的相知,算来有29年了。但是前六年,除了关于《守财奴》的公开课,几乎没有对话和交集,对张老师的认知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直到1990年,也是和张老师认识的第六年,我和张老师分到了同一个备课组。
那时同组的还有三位新近分配来的小老师。我们几个年轻人自然热络投机得很,课余时间会买些零食分着吃。记得有一次,买的是黄瓜和番茄,张老师独自向隅而坐。
我们几个在他背后暗自讨论要不要给他吃——因为大家都莫名地对张老师一贯的不苟言笑有些怕。终于我鼓起了勇气,请张老师一同吃黄瓜番茄。张老师爽然接受,而且立马吃得津津有味——原来张老师也是人!这就是我们当时天真的想法。
一天,我看杂志,当读到记载着高僧表述人生的两大快事时,不禁哑然失笑。我便问组里的小青年:“你们知道人生的两大快事是什么吗?”洞房花烛、金榜题名、老来得子、升官发财转了一大圈,全不是正确答案。
张老师起身把什么垃圾扔到门后的纸篓里,便突然插话,同时打着手势说:“这快事,是是挖耳朵!”我“噗嗤”一下笑出了声“对。正确答案就是挖耳朵和打喷嚏。”是的,不要以为高僧就能说出道行多么深奥的话来,他们的高明就在于能一语中的,看尽人世真相。在张老师给出答案时,我以为张老师也是高僧。
至此,张老师在我的眼中,褪去了所有的神秘感,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正常人。
也是在那一年,上级主管第一次开始给教师定职级。我没有被评为一级教师,当时给我的理由是师德这一栏目零分。后来我知道所谓的师德零分是指我在班主任的任职年限上远没有达标。
基本要求是5年,我统共工作六年,第一学期是做班主任的,后来因为家离学校很远,在春节的领导家访后,校领导深深体验到了我每天长途来回的劳顿,便免了我的班主任差事,成了有课就来无课就可以回家的“大学老师”。
后来虽然我家搬到了虹口,离学校近多了,但是在安排工作时,因为有了定势思维:我是不能安排做班主任的,而我也落得自由,享受着“大学老师“的待遇,这样我便在班主任的年限上几乎为零。但毕竟人是要面子的,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看到与我差不多时间进校的被评上一级,而我没有,脸面是挂不住的。总要闹他一闹的。
我每天到学校上班,但是即便有课也不进教室上课,美其名曰“我的师德问题一天不解决,就一天不能进教室上课——你想,师德不好可以进课堂毒害青少年吗?”张老师是教研组长,我也见过他到我的班上张望,看我在不在上课。
这样一连过了三天。终于张老师找我谈话了,问为什么不上课。我如此这般地说了原委。没有想到堂堂教研组长没有批评我,还说因为这个理由,我这么做是对的。这份困境中得到的支持是多么可贵!
虽然很快学校就解释了所谓的“师德”问题,而且说明了由于名额的限制,学校的种种为难,我总算宣泄掉了心中的块垒;但是,这份在落难时的理解与同情甚或支持,让我对张老师的认识从“是人”上升到了“有人情味”。
从那以后,我学习要做一个像张老师一样的人。
说到张老师的“人味”,让我想起了张老师跃动的童心。
我姐第一次去新加坡带回了一个玩具——是给大人玩的。那是一坨仿真度极高的塑料大便。说是给大人玩的,是因为在这个“乌龙事件”里很可以看到各色人等的表现,反映一个人的性格。
我把它带到学校,乘人不注意时,悄悄放到了办公室的门后。待众人汇聚的时候,故作偶然发现似的惊呼:“这是什么?”商老师马上联想到自己年幼的女儿,说“我没带咪咪来过。”这是要撇清责任;郑老师说:“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恶作剧!不能动!要向校长室汇报的。”这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主。张大文老师说:“怪不得那么臭!”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
当真相大白后当然是哈哈一笑咯。
张老师却饶有兴味地研究起了这坨便便,而且感慨地说这个创意和设计真是绝好绝好。他要我把它借给他,回去考查老婆、孙子。据张老师后来绘声绘色地讲述,过程是这样的。
张老师晚上回到家,去卫生间。突然火冒三丈,厉声喊道:“张XX(老婆),侬看看,格是啥么事啊?”张师母看了又看,又回屋里拿了老花镜戴上再看,百思不得其解,“哪能会有格东西?一定是只小鬼(上海话ju)。
”于是到房里,揪着小孙子的耳朵:“来来来,侬特我看看,哪能会得柴出来格!”小孙子蹲在地上,对这坨坨,看了再看,摇摆着脑袋,又挠了半天头“我是没有大便过呀!”张师母生气道:“伐是侬是啥宁?是阿爷?是阿娘?”“我好像没有柴过么。
”小孙子自认倒霉地吃进了。“好了好了,快点弄特,臭塞了!”张老师发调头了。于是张师母伸手去取厚厚的手纸,说时迟那时快,张老师徒手操起那坨便便就丢向师母。师母惊吓得跳起避让,待看到应声落地的那坨便便突突地弹跳了几下倒地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假的!
张老师在描述整个过程时,满脸灿烂,全是坏笑。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张老师跃动的童心。
张老师是很喜欢孩子的。私底下,张老师和他的小孙子约定,就他们两人时,他叫孙子“老张”,孙子叫他“小张”。每每这样互相称呼一下,爷孙俩就偷偷地开怀大笑。
这样的称呼甚至张老师早在同事间就已经在用 了,比如:刚分进来的姚,才二十三四岁,张老师便称他“老姚”,而且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问张老师这是为什么?答曰:表示尊重;因为他自己也是在二十五六时便被老校长唤作“老张”的。据说还是老校长带来的部队里的亲切称呼。
说张老师爱孩子是有依据的。其实张老师的孙子并不是嫡亲的。张老师跟我说,他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血缘,只要孩子听话、爱学习,他都喜欢。张老师甚至说:假如有一天他的家门口有人放着一个弃婴,他一定要抱回来,养起来,好好培养。报不上户口,没关系,给孩子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就叫“张黑黑”,目的就是要让他知道他是黑户口,黑户口一样可以长大成才。
张老师的理想家庭,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各自安静地看自己的书。
终于有一天,他的孙子回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家,养了近10年的孙子要离开了。张老师对孩子妈妈说,只要孩子肯读书,钱,我来供;哪怕出国深造,钱,也由我来出!
学生是张老师的孩子,孩子也是张老师的学生。
张老师对我的要求是很高的,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浪费时间。张老师退休后,电话的联系中,张老师问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周末在干啥?如果回答是三五好友聚会、打牌,张老师一定会发火:怎么这么不珍惜时间!
在闲聊时我曾经告诉张老师,我学习中文其实是阴差阳错的结果。在我读中学时,精神食粮是极度贫乏的,曾经如饥似渴地读一本《孤女飘零记》而忽略了批判四人帮的报告被罚站办公室一下午。我告诉张老师,当我考上华师大中文系时,一看周边的同学,我觉得我看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懂的东西实在太有限了,于是我狂补:暑假两个月几乎都是泡在寝室里看书。
早晨,食堂里喝碗粥,再带两只二两的白馒头和一些酱菜,就权当是一天的口粮。不是因为家境不好吃不起饭菜,只为躲避夏日的日晒和节省奔波食堂花费的时间。所以,张老师每每批评我时,就说:“你现在哪里还有一点点当年在华师大的奋苦精神!”
张老师自己是十分重视和珍惜时间的。现在张老师早已退休了,有时我有事想约张老师,常常被告知没有时间,而且张老师也最不能容忍这种突如其来的约见,因为他的时间表几乎是以小时为单位排得满满的。
2003年,我开始了教导处的的工作。从那时起,张老师就一有机会便讽刺挖苦,批评我不务正业。在张老师的眼中,凡是远离语文教学的都是旁门左道,都是追逐名利的浮躁病。
其实张老师的话极对!这被后来的实践证明了。从2003年到2011年,这九年我的业务是停滞不前的;这也是张老师跟我的矛盾最突出的九年。由于有行政职务在身,我只教学一个班,三年一轮,往往课上过就成了过去式。
几乎在教学上就没有停下脚步细细钻研过,得过且过,任务式的应对成了我教学的常态。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做教师的无趣。因为不是班主任,每周四节课能与同学接触,拉大了和学生的距离,师生的感情淡了,教学上抱残守缺,看似驾轻就熟,实则止步不前,很快专业瓶颈出现了,于是职业倦怠也滋生了。
每每张老师不满于我的现状,对我的不思进取严厉批评,攻击我已经开始主动接受安逸和享乐时,我嘴上在顶撞,心里早就缴械投降了。
在我给郑校长的请调信中,我是这样说的:“做教务工作原本就不是因为喜欢,而是碍于面子; 而一旦做了,为之牺牲的却是我的业务。为不喜欢的事付出喜欢做的事作代价,我觉得太不值,迷途知返,倦鸟知归。”
我的回归,张老师欣喜不已。张老师以极大的投入给予我工作的支持:开讲座,亲自给同学上提高课;以他的影响力招募到上海市语文教育卓有成效、又志同道合的同好们开展沙龙活动。大家剥离了一切的功利,纯粹是因为对语文教学的热爱,互相上课、听课、评课。在这样的教学氛围中,我仿佛重回到当初对语文教学新发现的美好时光,开始了新一轮的学习、实践、思考。
可以说是张老师用不懈的敲打和痛斥把我骂醒的。
在语文教学上张大文老师对我的帮助非同一般,而且在对人生的思考上张老师也同样给我以启迪。张老师讲的文革中挨批斗的他领受工友在他碗底放着的肉圆,他动容了;人间最可贵的就是真情,就是无需言语的默默的支持。
张老师讲他初登讲台不久所写的话剧剧本发表在《文汇报》上,并在市工人文化宫上演,他的激情和活力以及在讲述时强调的对每一处细节的关注,每一个细部问题的重视,都让我感受到做一件事一定要严谨、细致甚而至于苛刻,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
张老师在下班路上与我一起散步,夏日沿路棚户人家搬出小桌椅赤膊喝酒小酌,张老师感慨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幸福的权利,棚户区的贫困一样也有欢乐的笑语,真切的人情和丰富多彩的生活。
他让我懂得精神的快乐是最重要的。张老师会回忆他的大家庭的没落与根源,他说“共产党没有共张家的一分钱财产;张家的破落全是因为一帮没有追求,成天吃喝嫖赌的先人作的孽。
”他说:“有谁能想象,三伯父一家雇佣了几个佣人,每天要忙三桌饭菜供那些前来的赌徒吃喝。三伯母怎么能承受终日这样的胡闹,于是精神失常,终于有一天投河自尽。”张老师说,一个家庭和一个人一样,没有了追求,贪图安逸就必然暮气沉沉,死路一条。
张大文老师是主张和而不同的。志趣的相投很重要,但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他希望我们能独立思考,坚持己见。而且往往在学术问题上有了争论,张老师的兴奋是异乎寻常的;他会穷追不舍,把各自的观点要最大化地充分表达出来;他要努力说服你,又希望你能说服他。这种时候,张老师的脾气是极坏又极好的。
石钟山的《雁》我和薛亦舒老师分别进行了课堂教学展示,张老师也带上自己的文本解读前来听课。围绕这节课,我与张老师的“战争”持续了几乎有三个多月。说张老师的坏脾气,是他不能容忍我犯错,张老师一遍遍数落,我一次次辩解。
脾气坏到几近伤人;说他脾气好,一旦他终于明白我的道理,他又会不但鼓励你,而且会沿着你的思路给出更加合乎逻辑的解说。张老师和高杨分别上《生命的舞蹈》,我带来了我的课文解读前往听课,张老师十分高兴我能以这样的认真态度对待上课的老师,并推崇今后的听课,只有自己做好案头工作,才是对上课老师的极大支持和尊重。
但过了几天,他认为我的文本解读有问题时,便又将我骂得狗血淋头,仿佛我的文字一文不值。于是在解说与争执中又经过了几个月。
这样的争论在张老师是乐此不疲的,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理智,当他认为我有问题时,他可以数落我与他相识以后的所有的不是,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他都可以拿来作为宣泄他不满的理由;当他认为我有几分自己的道理,马上就又沿着我的思维走一遍我的思路轨迹,哪里是他认为需要作出说明的,他沉下心去细细推敲琢磨,同时鼓励我进行新一轮的探究。
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凡是我的文字必定要经过张老师的过目,得到张老师的意见后,我才有自信拿给别人看。
张老师对我的要求极其高,我怎样的努力都达不到张老师对我的要求。虽然理智上讲,我能够理解这是张老师认为我是可造之才,但是在感情上对张老师的批评意见,我总是怀有强烈的反感,似乎我再怎样的努力也是徒劳。
《五十年》的复印件放在我的桌上,我认真读了;随后我短信说了我的读后感,并谈了我的两点困惑。张老师在沉寂了几天后,新的《五十年》复印稿又放在我的面前了。他说你的困惑其实就是意见,很好。
他已经修改作了补充。于是,张老师要求我全面评价《五十年》。我自知我没有能力在张老师的学术领域说三道四,我只能仰望和学习。我就在想,我究竟能对《五十年》作出怎样的回应呢?我想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回顾、总结我从张老师那儿学到了什么,张老师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在我的人生成长轨迹中张老师的意义是什么。
这样想着,张老师之于我的学习、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便跃然眼前。我想我可以回应《五十年》了,我有内容了。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给张老师,得到了首肯。
没过多久,张老师就问我的写作进程,我说不着急,又不发表;张老师说,可以在兰生20周年校庆校刊上和《五十年》配套发表,我说那还有一年的时间,早着呢!张老师严厉地数落道:你以为什么都是那么简单到一挥而就的么?你以为在交稿前三四天突击一下就写出上万字的文章能够显示你的才气吗?醒醒吧!这种浮夸是要害死你的。
话难听,但是还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便着手写,也希望写出后,能够一遍一遍改,一点一点充实。以最谨慎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文字,也对得起与《五十年》张老师一生对待语文教学的严谨,更对得起张老师对我一路成长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