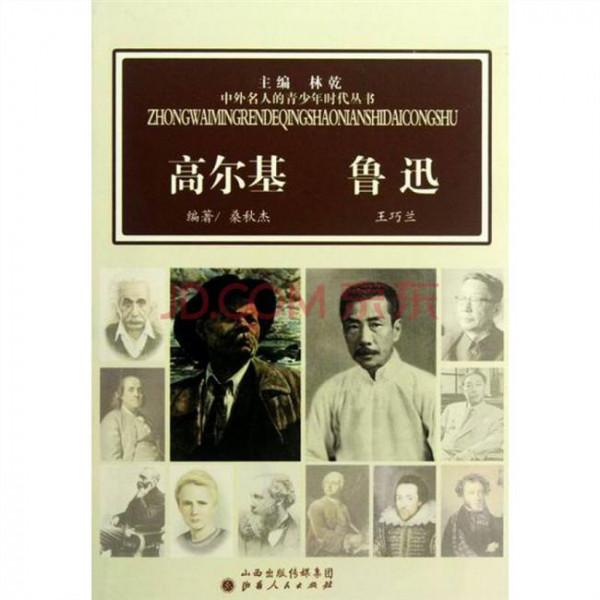曹聚仁的夫人王春翠 曹聚仁:矢志不渝的“灯台守”
异乡的浴室里,父亲手持毛巾,从孩子的背脊擦下去,反反复复说着这句话。这是1956年7月,曹景行随母亲到首都,与从香港赴京、分别6年的父亲曹聚仁见面。此行进京,曹聚仁将参加周恩来在颐和园举办的晚宴,向外传递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但在浴室的这个时刻,曹聚仁只是一位普通父亲,心怀歉疚地为久别的幼子洗澡。

从3岁时与父离别,到25岁时为父送葬,此间漫漫成长岁月里,曹景行与曹聚仁的相处加起来不足一月。父亲声语温存低唤乳名、掌心柔软拥之入怀的形象,也几乎全止于新侨饭店浴室的吉光片羽中。
但日后这位长期缺席的父亲,却始终以书信文字的方式陪伴着家人,并于冥冥之中,一直影响着幼子的成长。直到自己过了而立之年后,曹景行再次翻阅这些书信,从字里行间开始真正懂得,父亲一生的抗争与矛盾、追求与无奈。

曹聚仁
出生于1900年,字挺岫,浙江浦江人。现代作家、学者、记者。1921年到上海教书,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1937年抗战开始,他从书斋走向战场,采访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及东南战场。1950年到香港,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1956年后曾数次回大陆采访,并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一生著述逾四千万字。

家信落款里的父亲
在夏衍的回忆里,曹聚仁这位国学功底甚好的同龄人,“自称接受了老庄的影响,但我看,他对世事并不‘逍遥’,他没有出世,他始终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1920年以后,我们都到了上海,我们都穿上了中山装和西装,他却一直穿着那一件蓝布长衫”。

倘若炮火未至,曹聚仁也许将一生致力于做一名伏处书斋的作家、学者。然而,“一·二八事变”震荡华夏后,始终穿着长衫的曹聚仁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战场做记者。“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 战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他这样写道。
曹聚仁初上战场采访前,摄于1937年。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曹聚仁进入了著名的“四行仓库”,目睹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当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他又受聘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逐日往西往北。1938年4月7日,台儿庄大捷,消息首发者就是曹聚仁。稿件见报后,举国若狂。而与国共两党都有交集的曹聚仁的个人际遇,从此也为政治的走势所裹挟。
1950年,曹聚仁离开妻儿,只身从上海去香港定居,除了谋生,他更希望寻找做另一份事业的机会。临行前,邵力子也建议他等待时局的变化。
曹聚仁对孩子们的爱,更多体现在一封封家书里。
留在儿子曹景行模糊印象里的,是随长辈到上海北站为父送行的画面:父亲挥别的手渐行渐远。从此以后,这位父亲,就更多体现为一封封家信最后的落款:父字。
站在热闹斗争的边缘
酷爱读书的父亲,虽然不常在身边,但留在上海一屋子的书籍,与同样酷爱读书写作的母亲,依旧以不动声色的浸润,影响着曹景行的成长。
父亲在家中留下的和舒宗侨合著的《中国抗战画史》,曹景行小时候就当连环画来翻。及略识字,曹景行就开始在父母兄姐的书架中抽取阅读,一开始的启蒙,就未曾读过多少童书。
1956年7月,曹景行随母亲赴京,与分别6年的父亲见面。在得知9岁的曹景行已经看过《水浒传》后,父亲非常高兴,就去北京的东安市场购买了《水浒后传》作为生日礼物相赠,又补偿一般地允集邮的曹景行把新侨饭店大厅内的邮电门市部里出售的所有中国邮票悉数买下。
一天吃早饭的时候,父亲又与曹景行谈论墨子的《非攻》,交流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看到孩子好学,父亲十分欣慰。北京一别后,父亲又陆续带给曹景行《说岳全传》《三侠五义》《红楼梦》,鼓励儿子阅读。
但事实上,曹聚仁在香港的最初几年生活并不顺遂。夏衍写过1950年曹聚仁刚由上海到香港的境遇,“发表 《南来篇》,写了一句‘我从光明中来’,于是右派骂他。后来他把新中国和蒋经国当年的‘新赣南’相比,又以《门外谈兵》评说朝鲜战争,又挨了左派的骂。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曹聚仁偶发怪论,但是他的用心是好的。据我所知,第一个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是曹聚仁。”
那样的苦闷里,曹聚仁在家书里向孩子中年纪最大、当时初中毕业的女儿曹雷流露矛盾心绪:
“将来,你们长大了,记住我的话……什么行当都可以自食其力,千万莫要做文人……我曾叫你抄下了《儒林外史》最后的四个人,我最爱的是荆元。他有着做裁缝的一套本领,不必依人为生,做那些达官贵人的清客;他吟诗作诗,只是写出自己的心怀,并不是附庸风雅,他也写文章,并不替什么圣人立言。
这样,一个独立自尊、有完全人格的人,才算得真正的‘人’,堂堂的一个人。你的弟弟们,年纪还很小,等他们长大了,你可把我的话说给他们听……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父亲,只是一个不好不坏,可好可坏,有时好有时坏的人……他一生是孤独的,但他站在热闹的斗争的边缘上……”
这种既以书生傲骨自诩,又不愿被归类文人的矛盾心态,其实贯穿了曹聚仁一生。早在1938年,曹聚仁曾对陈独秀说“我是个没有勇气的人,我是罗亭。”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是一个虽然向往真理但又行动力不足的人,这是许多文人身上的通病。曹聚仁自比罗亭,也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认知和自省,并最终,选择独自去海外。
但这样的决定,也决定了离别。他与家人的见面,从此只能短到以天、小时,甚至以分钟计。
1958年,曹聚仁返港途中在南京下关车站停留,与夜半即到此守候的老母相见,见面的时间仅有8分钟。他后来感赋一律道:
“迷茫夜色出长栏,白发慈亲相对看; 话绪开端环如茧,泪澜初溢急于酒。抚肩小语问肥瘦,捻袖轻呼计暖寒;长笛一声车去也,四百八秒历辛酸。”
曹聚仁与夫人邓珂云、女儿曹雷、曹霆在赣州,摄于抗战时期。
并没有走错的棋
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离别的辛酸,开始变为彻骨之痛。
曹聚仁隐秘而敏感的“海外身份”,招致造反派到曹家和曹雷工作的单位贴大字报,还抄走了曹聚仁的大量文字稿和其他物品。曹景行亲手用榔头将父亲抗战结束时所得的“胜利勋章”敲烂,因为上面有蒋介石的头像。
当时,全家的账户被冻结,几乎难以度日,为了替即将赴皖南农场的曹景行添置衣物,母亲不得不去长女曹雷所在的单位开证明,方能取出一笔款项。但这一切的事情,母亲都极力承担下来,全家都尽量不在书信中对父亲提及。
虽在困顿之中,但女儿曹雷却收获一段患难真情。1967年的7月,在母亲的陪伴下,曹雷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去和爱人李德铭结婚。远在香港的父亲不能亲临爱女婚礼,只能写了三首诗相送:
“其一:一缘一劫缀花枝,缘劫相寻总是痴,旧梦仙霞今记取,橙黄橘绿放翁诗。其二:理之所无情乃有,不知所起往而深,玉茗堂外汤汤水,如月一星证素心。其三:四梦由来一梦赊,灶儿巷口夕阳斜,阿爷掌里明珠在,万籁无声起暮鸦。”
1968年,在得知曹景行要去皖南山区时,曹聚仁特意从香港寄来四卷合订本的《毛泽东选集》。此时距离曹聚仁离开上海,已经过了18年。
除了这些文字、诗和书籍,身在千里之外,父亲也实在不再能为儿女做什么了。漫漫岁月流逝,昔日伏在膝头的女儿嫁人,抱在手里的稚子要下乡,而自己竟不能送一送,于常人都是不可言说的憾事,但回望自己当初的决定,曹聚仁初心不悔。
1969年12月4日,曹聚仁写信回家,信中写道:
“天下事,不可想得太天真的。雷女,你的毛病,就是太天真,天真是可爱的,但处世并不只是谈恋爱呢!范长江兄告诉我一段人生经验:‘做人不能不摆好防守的棋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结了婚,该明白这一种做人的道理了吧?……十九年前,我应不应该到海外来闯天下呢?在当时,你妈真有千个万个不情愿,但,这一家的担子谁来挑呢?我不能说一句空口漂亮话,说大家一齐挨苦就是了。
我咬下牙关,决定到海外来做事,找钱养家,闷声不响,自己多吃点苦。
那时,你们年轻,是不懂这番道理的。别人以为我到了海外,一定会远走高飞了。我一心向往北京,而且慢慢走上为祖国效力的路子,和别人的想法绝不相同。我的文章,在海外造成了权威地位,这便是我生存下来的基本条件。
社会革命,乃是我们年轻(时)的理想,我为祖国效命,也就是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虽违背了对你妈的‘永不离别’的诺言,但处在这么伟大的时代,我能天真地开自己的玩笑(吗)?到了今天,你们也该明白我十九年前的决志南来,并不是走错了棋了吧?”
老年再遭折指之痛
但有一件事,终究瞒不过去了。
1970年,曹景行的哥哥曹景仲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派在河北省张家口沽源县农机厂,不幸在战备工作引发的爆炸事故中身亡,年仅25岁。
担心曹聚仁受不了打击,母亲邓珂云托香港 《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徐徐告之。曹聚仁后来在《哭平儿》一文中写道:
“平儿(景仲)已经在张家口外沽源工厂遇难殉职了。云怕我会太伤感,年老吃不住,才托F兄(费彝民)转告我!F 兄还引了司马迁所说的‘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的话,为国家建设而殉职,当然是光荣的。当时,我并不太激动,只是木然惘然而已。不过,我最懂得吴敬梓所写王玉辉从徽州经杭州到苏州,看见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那一刻的心情。一切都是一言难尽的;今天,我对万兄也就说了这样的话。
四十多年前,便是一·二八战争那一年,我第一回折了自己的指头。(注:曹聚仁第一个女儿曹雯幼年夭折)我仿佛到了世界末日,也不知怎么活下去才是。四十多天,晚上总是流涕,毕竟是‘日子’劝人,也慢慢淡忘下去了。第二回,正当抗战胜利那一年,我已从上饶回到了上海,霆女(注:曹聚仁的第三个女儿曹霆)却在乐平病死了。
那一个月中,云几乎老了十年似了,我呢,真正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万念俱灰。这回是第三回折断了自己的指头!在平儿自己,正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人生原不过为一大事出世。在生者,尤其是云,她一定像火灼那样刺痛,而她只是怕我吃不住呢!
半年之前,平儿在沽源铁厂炼钢(注:应为在沽源县农机厂做战备工作),炸伤了双眼,他回上海医治,休假期未满,又赶回工地上去,这回毕竟遇难了。我原说我的双眼很好,待机会留给他去换上。最近我的双眼突然昏花,心中不安,想不到他已遇难,用不着我的双眼了。
今天情绪很乱,就说说我此刻的感想!
平儿的性子很憨直。他这回殉职,组织上用的考语,说他公而忘私,不怕苦,不怕死。这都是青年一代的美德。这美德,一半该说是先父梦岐公的德性。我一生交往的朝野人士,数以千计,真正能奋不顾身,公而忘私的如先父的,并不很多。
先父直性子,是非分明,想不到平儿遗传了这份美德了。另一半,那是珂云之力,她把一生心力都放在几个儿女身上。过去二十年间,我大半时间在海外,不曾尽过什么父职。她是恰如其分地把儿女教养成为新时代的孩子。在思想觉悟上,我的儿女都比我进步得多。我知道她要多大的勇气,才能顶得住这样的遭遇!
对着平儿的遗影,我来检讨我自己的一生。我是虚无主义者,虽说在社会革命雏形时期,已经和前驱战士们很熟识,往来很密切;但我一直是看革命,站在革命洪流边上,不曾投入战斗中去过。我以唐代李泌自许,如张良那样,一直不想亲手去做过什么。
只有奔走抗日,参加救国会;中日战争发生,作了战地记者,上过战场。但我上了战场,也还是一只凤凰,成了各战区的‘贵宾’,不曾受过什么辛苦。连萧同兹社长(当时中央通讯社社长)也另眼相看,一直是风云际会,比范长江兄还幸运些。在社会革命有了结局的今日,我的儿女在生产建设上有了贡献,也可以说替我减轻了对社会国家负疚之心呢!
三年前,我从广华医院动了手术回来,珂云来信,勉嘱我再替国家做十年工夫。哪知三年后的今天,实在暮境迫人,怕的不能再做什么了。不过,在平儿殉职的今日,我倒该下了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义无反顾的海外哨兵
也许旁人能比本人看得更清楚些,这份“鞠躬尽瘁”的心意味着什么。
夏衍曾在1990年代写文谈到曹聚仁,“说到新闻工作以外的事,有一个时期他很有兴趣于促成海峡两岸和解,祖国和平统一······他是书生,但毕竟是有志报国的书生。我曾在《懒寻旧梦录》中替他说过几句公道话,认为他骨头是硬的,晚节是好的。”
书生的本色,其实才是曹聚仁一生真正的底色。在曹聚仁的遗作《书卷长留伴一生》中,他将法国传记作家莫罗亚引为知己。莫氏曾引洛斯丹的话,说“印刷品是我们进入真理之国的通行证”。又引法国思想家蒙田的话,认为我们有和爱情、友谊和书卷三种东西神交的必要。
“这三种东西,都是很相同的。我们能够爱书,因为书永远是我们忠实的朋友。”曹聚仁在文中感慨道:“我这一生,并无什么嗜好,连香港人这么发疯似的看马看球,我也一点不动心。有一天,什么骑师跌死了,某报出了号外,我连看都不看一眼。一位朋友说我不可救药,我只是笑笑。可是有一天,我身边只留了二十块钱,却花了十七元六角买了一部 《中国文学史》。我和莫罗亚是同路人。”
在香港最后的岁月里,他于贫病相交中挣扎。当时,他住在一幢四层危楼顶部搭建出的50平方米左右的陋室内。居所中并无长物,唯四壁皆书。病重之际,他独自上楼而力不能逮,要上4楼但爬了一半阶梯竟瘫坐在楼梯道中,直到前来看望他的友人发现,才惊痛地把他搀扶上楼。
1971年7月28日,曹聚仁在家书中写道:
“国际局面变化很大,我这个灯台守,只能痴汉等婆娘似的,等他们送媚眼来,只不知何日好事能成双。最近几年,怕的还得工作下去。我精神这么不济,双方都不让我走呢!”
1972年1月12日,已经病重的曹聚仁给香港 《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去信。信的第一段说:
“弟老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了,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不大不小的事……于今陈先生(陈毅)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近于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系,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
1月31日,他用已经歪斜的字勉强给孩子们写信:
“雷女,閒儿,我实在没有工夫生病,偏偏要生拖长的病,真是急不得、哭不得、笑不得。我已经无法在尼克松到北京之前回北京了。一般情况也还不错,只是坐不得、立不得、行不得,三不得,连神仙也没办法了呢。你们不要急,你们的一切想法,都是于事无补的。”
这一年7月,始终期盼着两岸统一的曹聚仁在澳门去世。正在皖南农场的曹景行获准去送葬,从安徽用了三天三夜赶去,最终见到的,只是追悼会上父亲的遗容。
化作南海“灯台守”
上世纪80年代末,曹景行移居香港,先在中文《亚洲周刊》工作八年,后在 《凤凰卫视》任职。这无形之中子承父业的关系,为在港曾与曹聚仁共事的人所知,便有人感慨曹景行必定“常受教于令尊”。
每听到这个说法,曹景行唯有苦笑:三岁一别后,父子所有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一月,何谈受教?他倒常常反过来羡慕那些曾在父亲生前与之共事的人。他也曾试图去寻访父亲在港的足迹。但城市建设变化速度之快,早已物是人非。
在一次活动中,曹景行与导演王家卫相识。闲谈之中说起,曹聚仁生前居住在九龙金巴利道地区,是彼时上海来港文化人聚集区,也正是王家卫幼时居处。曹景行后来依言去寻旧,父亲居住过的诺士佛台7号所在位置,如今已是酒吧街中的一家,隐匿在天文台侧的小山丘上。
太平世界里,夜来青年男女来这里娱乐休闲,好不热闹,而沿着如今铺设吧台桌椅的小道行走时,曹聚仁眼前浮现的,是台海局势大变的岁月里,父亲在此独行的背影。叠加着的,是他三岁时在上海车站站台送别的父亲,是在京城旅馆里为自己洗浴的父亲,也是后来在书报文稿里,成年的自己不断重逢、不断重识的父亲。
在最早的关于父亲的记忆里,曹景行还保留了这样一幅画面。那是父亲赴港前,在上海家中书房写稿,一手紧抱着自己的小身体,一手依旧运笔不止,间歇时还会给自己一枚金币巧克力。
这个一生伏案的书生形象,最终用自己的方式燃笔为炬,在特殊的年代里,于南海的一角,做过矢志不渝的“灯台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