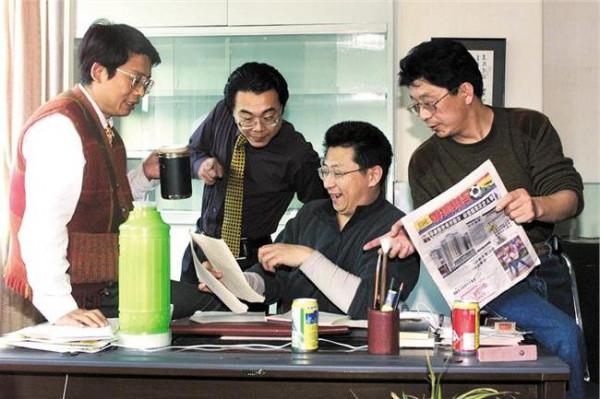陈岱孙文革 【陈岱孙】巩献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们应该向陈岱孙先生学什么?
——我们应该向陈岱孙先生学什么?回忆听陈老师谈话有感
北京大学巩献田
内容提示:本文作者亲自聆听陈岱孙先生的几次讲话,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在北京大学1991年新年团拜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社会出现的“一些不良的风气,存在着一些扭曲的价值判断”的警告。
“表现为对物质刺激的欣赏,对一切往钱看行为的认可。”他说:“扩大商品化的极端就会变为歌德在其诗剧《浮士德》中所描绘的浮士德,把自己的灵魂都当做商品卖给了魔鬼。”第二次。是在1994年春西方经济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言中,他反对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他认为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会带来2个方面的危险,“一是毒害青年学生,二是误导改革开放。”
作者认为,陈岱孙先生是谦虚谨慎、治学严谨的学者的表率,是敢于大胆揭露社会危险倾向、秉持正义的教授的榜样,是反对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毒害青年学生、误导改革开放”、导向及时、正确的导师的典范,是一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学界宗师。
我们向陈岱孙先生学习,就要学习他的上述品质和精神。
在北京大学网站看到一则消息:5月5日,纪念陈岱孙先生诞辰115周年大型图片与文献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展览厅开幕。对此,笔者甚为高兴,同时在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陈老师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回忆起亲自聆听他谈话时的情景。北京大学没有忘记这位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学者表率、教授榜样、导师典范和一代学界宗师。
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北京大学法律学与经济系办公的位置,都是在如今北大图书馆西面的四院。当时四院只开1个南门,法律系在前排,经济系在后排,经济系教职员工到系里去必须通过法律系那排的门口,这种状况直到1993年3月法律系(不久改为学院)搬到逸夫一楼去才改变。
作为恢复研究生制度后首届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的我(即1978级),按规定应在1981年7月毕业,可是系里研究生秘书职务一直由系办公室老主任徐卓世教授兼任,当学校决定我留校任教之后,4月初就担任了法律系研究生秘书。因此之故,我就每天到系办公室去上班了。当时,陈岱孙老师是经济系主任,于是在四院门口碰见陈老师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
有人讲,往往1个动作就能反映1个人的素质,这话一点也不假。
陈老师,我是从他作为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1900年生)在四院门口相逢认识的。他年龄这么大了,竟然有时要让我这个不满40岁的中年人先走1步。当然,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先走的,这是最基本的礼貌。每次,当我把手扶住门框让他先走1步之际,他总是点头表示谢意!
对照当今社会,有的人,尤其是某些青年人,连基本的礼貌不讲、礼仪不顾,尊让精神全然丧失,只要自己舒服就行的做法,陈老师这种礼貌待人的举动,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作为真正的学者、学问家的陈岱孙教授,其治学态度的严谨是出了名的。建国前,他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时候的治学严谨情况,至今都还在广泛流传,只要上网一搜“陈岱孙”3个字,便可以知道的,此处不予赘述。建国后,陈老师的主要专业是经济学说史,他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卓越的观点。
先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反杜林论》课程的教学为例来说吧!陈老师首先要查阅原文、弄清原意,然后科学地加以讲解,绝不依靠通行的中译本(须知,这里是指文革前的中译本。而改革开放以后的某些译文,更是糟糕得很!有的时候,看中文译文不懂,而看外文原文反倒明白了。
甚至翻译也“与时俱进”,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歪曲原文固有的意思,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中。)相反,在讲课之前,要将有关中译文的主要错误,一一指出,并加以更正。
在文革期间,按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学习马列的六本书,其中就有《反杜林论》。但是,对该书中马克思亲自写的第二篇第十章《“批判史”论述》,读懂的人很少。在全国各种版本的《反杜林论》辅导材料中,对于该章都没有解释。
陈老师凭借经济学说史的高深造诣和多种外文知识,读懂了本章,弄清了原意,把它讲解得有条有理、十分清楚。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编印的《<反杜林论>学习辅导材料》一书中,他破天荒第一次写出了本章的学习辅导材料,填补了空缺,解决了人们学习这一章的困难。
同时,他对《反杜林论》一书的评价,绝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敢于“反潮流”,见解独特,且非常公允。他认为,《反杜林论》虽然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但是它毕竟是一本论战之作,“不能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3个组成部分第一次所作的全面系统的总结”。这种不同于当时普遍流行观点的独立见解,不仅反映了陈老师严谨的治学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其过人胆识,与那些看风使舵、墙头草、随风倒的学者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