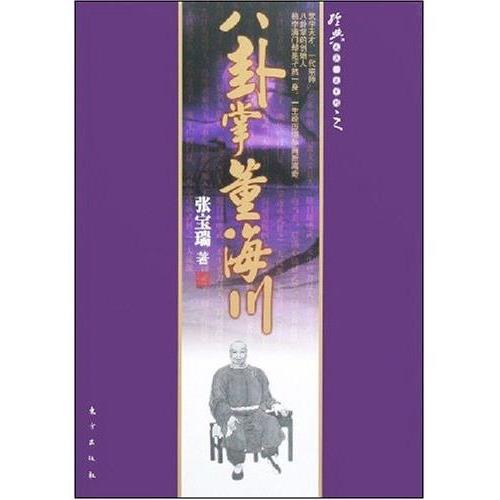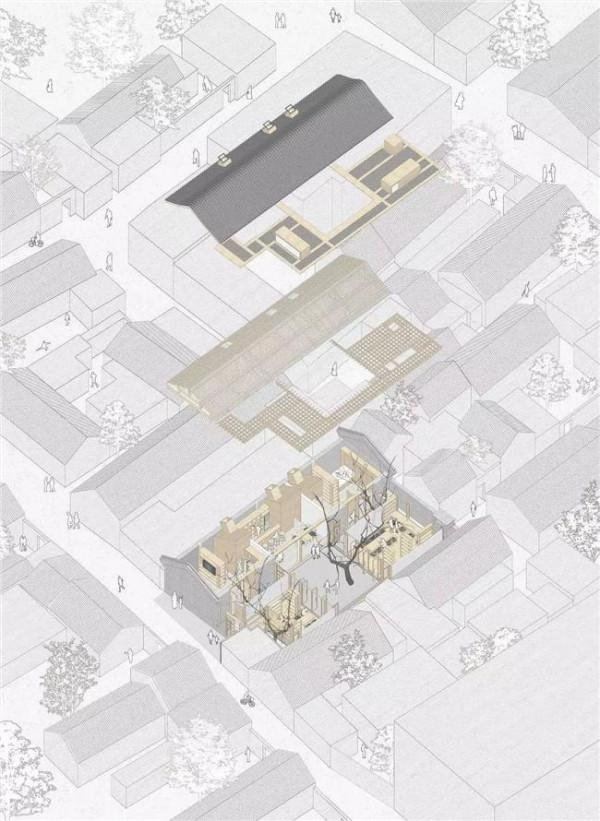李辉董乐山 请问:董乐山与董鼎山有何关系吗?
编选《董乐山文集》,使我有机会系统阅读董先生的全部作品:小说、诗歌、剧评、杂文、随笔、书评、论文、词典、译文……不同文体构成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的创作全貌。我称他为“文人”,而不是一般而言的翻译家、作家,乃是觉得像他这样一个一生中涉猎广泛的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打破了文体的界限这带来编选归类的困难、甚至职业的界限,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体,显露出了与众不同的才华。
无论有意而为或者不得不为,在他那里,最终都成为学识的积累和思想的深化,成为对自己意志的磨炼。
也就是说,不管处在何种状态何种环境,他最终都能找到一种寄寓思想和才华的方式。他坚定地走在漫长的精神之旅上,以知识与思想破解迷惘,以了解世界、了解历史的热望支撑信念。
尽管他并非豁达爽快之人,也从不以阿Q精神而自娱,但他绝对排斥委琐,反对碌碌无为。有这样的状态,他就不至于总是陷在怀才不遇、自怨自艾的情绪之中,而是能摆脱一时的委屈,一步步扎实地往前走去。可以说,他的生命从未停滞,从不苍白,最终以综合素质的积累,在翻译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成为新一代翻译家的一个堪称典范的代表人物。
董乐山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他在大学的专业是学习英国文学,但较之研究,文学创作对他更有吸引力。四十年代他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飘逝》写那种常见的男女之间的“三角关系”,于戏剧性巧合中渲染出年轻人的哀怨,走那种常见的爱情小说的路子。
《裁员》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颇有讽刺、冷涩的韵味。面对裁员时不同科员的表现,小公务员身在上海大漩涡之中的委琐性格,官场的冷酷与人际的无聊与无奈,被作者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
看得出,作者从俄罗斯文学中“小人物形象”的描写那里得到启发,同时,对上海现实生活有着敏锐观察和体验。他在《裁员》中表现出来的风格,在中断几十年后,又在“文革”后创作的《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等小说中呈现出来。仍保持着一种对生活的敏感和对命运的嘲讽意味,只是显得更为老到辛辣,这自然得益于他当右派多年的磨砺体验,得益于他对奥威尔作品的熟稔。
当年在四十年代的上海,董乐山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麦耶剧评”。他以“麦耶”笔名崭露头角时,还不到二十岁。初生牛犊,锐气十足,评点名家与明星,毫不心慈手软。然而,他绝非仅仅凭一股火气在那里闯荡天下,相反,他的剧评颇具创见,分析透彻而到位,笔锋犀利,读来如同行家里手的老到之作。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麦耶”一时成为上海影剧界风头出尽的人物。
描写秋瑾、徐锡麟的话剧《党人魂》作为历史剧,在麦耶看来并不成功:“所谓教育意义,决非化妆演讲,而是通过戏剧的发展影响观众的。《党人魂》自始至终,慷慨激烈的演讲太多,以至全剧演员无戏可演,观众无戏可看。”
曹禺改编的《家》,麦耶认为尽管作为剧本本身是“罕见的好剧本”,但由于曹禺在创作《北京人》之后,学习契诃夫而导致过多应用许多小事件和小细节,结果与吴天的改编本相比,曹禺的《家》舞台效果就不免显得沉闷。
唐若青名列上海话剧界“四大名旦”,麦耶并不否认她的演戏天才,她所扮演的繁漪、金子、陈白露,无不才华横溢。可是,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唐若青的明星派和腐化恶习。他甚至用相当激烈而尖锐的言辞这样说:“我们承认唐若青过去的功勋与成绩,可是就目前而论,她不仅自己个人是在堕落中,而且,她对话剧界所留下的恶劣影响是罪不可恕的,必然地,她将为中国话剧的发展而毫无姑息地撇弃!”
年轻的董乐山便是以这样的批评风格出现在上海文化舞台上,这是他的精彩亮相。收在文集里的“麦耶剧评”尚不齐全,但在半个世纪过后,仅仅这些汇聚一起的剧评,也足以把老上海舞台的种种风情生动地展现出来,读它们,仍可以感到一股虎虎生气卷着文化余香扑面而来。细细品味它们,从中不难看出后来的董乐山文化性格的最初形态。
五十年代开始,董乐山一步一步远离了文学。最终,翻译成了他的职业,这实在是他不得已的选择。
不能成为一个小说家、艺术评论家,董乐山可能是引为终身遗憾。然而,这却是当代中国翻译界的万幸。他以稳健的步履向译坛走来。早年所接受的中西文化的熏陶,从事过小说写作和剧评的语言锤炼,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思想深度,诸如此类的综合修养,无形中奠定了他成为一代翻译大家的坚实基础。他注定要在这个领域大展身手,傲然而立。
在我看来,从性格素质的组合来讲,董乐山具有成为一个优秀翻译家的充分条件。一方面他才华超人,思路敏捷,精神一直处在活跃状态,显得生机勃勃,有时甚至给人以恃才傲物的印象。另一方面,他却耐得住寂寞,不爱交际,能够屏气凝神倘佯在枯燥、劳累的翻译之中自寻安慰和满足。
卷帙浩繁的译著虽能说明这一点,但最令人感叹的则是《英汉美国翻译社会知识辞典》。这本辞典费时十多年,倾一人之力编撰而成,涉及美国社会生活知识的各个方面:书刊上常见的典故或典故性专名,如人名、地名、街名、商店名、商标名,而人名中又包括真人和小说、电影中的虚构人物;带有典故色彩的短语,但不见于一般词典;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很熟悉,但还算不上是成语的词语;一些英语新词层面。
能够不急不躁地编撰出一本辞典,充分体现出董乐山严谨、扎实的学风和渊博的知识,而这,正是他之所以轻车熟路地走在翻译之路上的保证。我们可以从他撰写的大量“译余废墨”文章感受到这一点。
读董乐山的翻译,实在是一种享受。在他之前的翻译家中,我很欣赏巴金和萧乾的译文,觉得那是将“信达雅”结合得较为出色的译文。董乐山的翻译达到了同样的境界,而且更为中国化,但又不失英美著作应有的味道。这就难怪在他去世之后,一些翻译家呼吁应该好好总结董乐山的翻译经验,并把他誉为新一代翻译家的代表人物。
然而,董乐山对读者的冲击不只是限于在翻译的信达雅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更在于他把翻译的选择,作为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历史责任的方式。岁月的磨砺,早早地让他变得成熟而深沉。他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弱者——虽然他许多年里一直是弱者,他也不是思想浅薄随遇而安的庸碌之辈。
他知道智慧与知识对一个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意义,他更知道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放飞无限的思想和情感。他并不是随意地走在翻译的路上,漫不经心地顺手拿起一本书就动手翻译,仅仅把这作为打发时光消磨生命的一个过程。恰恰相反,他把翻译的选择,与对命运的感触、对历史的关照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他可以在里面自由呼吸。
1960年,已经身处逆境的董乐山,在图书馆无意中看到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英文原著。作者对希特勒纳粹帝国形成与灭亡的全景式描述,以及在描述中的严谨历史态度和生动文笔,使董乐山马上意识到这是值得翻译过来向国人介绍的巨著。
野蛮与文明的对峙,兽性对人性的蹂躏,诸多主题集中呈现在这一著作中,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人类史上的黑暗。于是,他忘记了自己的带罪之身,当即向世界知识出版社推荐出版,随后他和李慎之、郑德芳等人开始了翻译,并由他三次通校全书。也许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翻译选择,实际上是为自己后半生确定了一个最好选择。他所酿就的知识与思想的诗意,在告别文学之后,重又在翻译这个园地里漫溢开来。
可以说,当董乐山最初决定动手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时,这种翻译与人生的关系便开始形成。从那时起,一直到他生前最后出版几本译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苏格拉底的审判》,他所翻译的各种不同的史著、回忆录、小说、理论著作,与他的所有书评和杂文,构成了一个整体,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现得美丽无比。
他的思想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他的文章和他的译著便具备了持久的生命力,而且不会因他去世而为人淡忘。相反,人们在阅读他的文集和译文集时,会时时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那么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当人们倾听之时,坚毅、执着、慈祥的董乐山在美妙回声中微笑。
这便是一个编选者在完成工作之后的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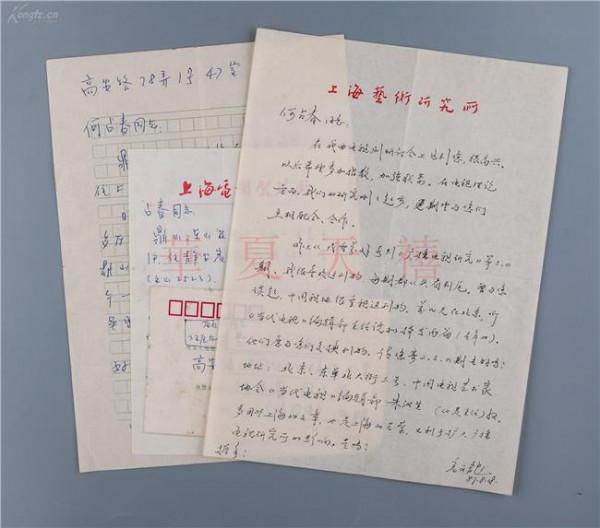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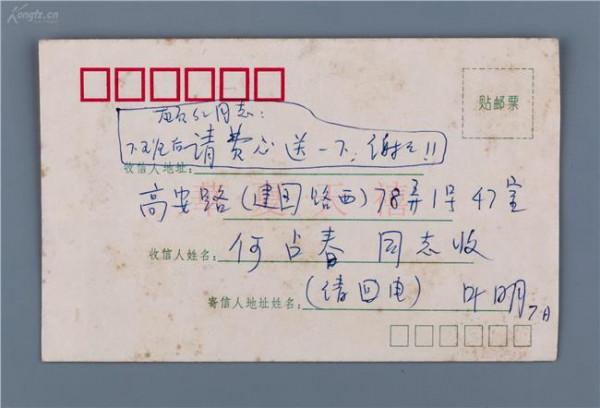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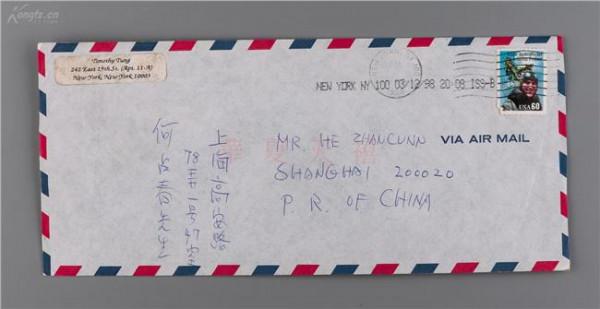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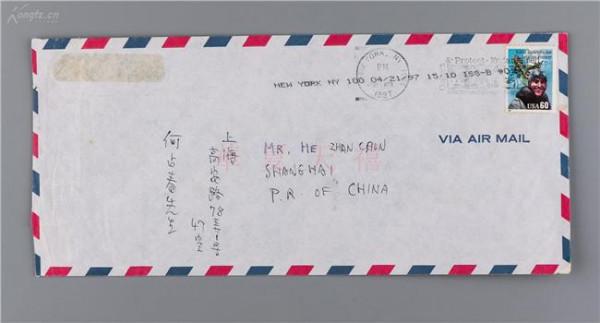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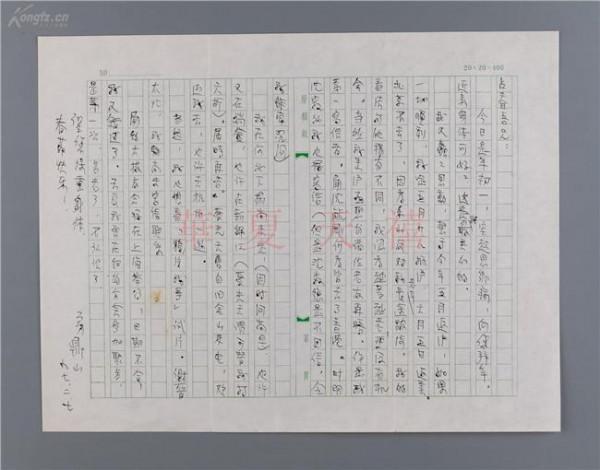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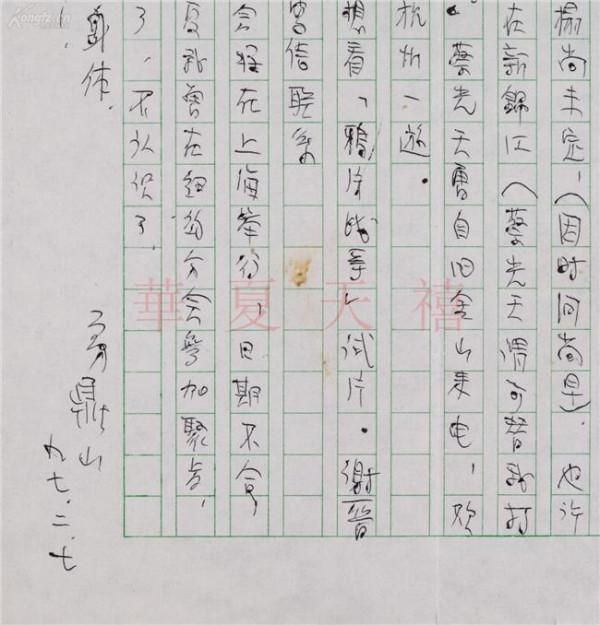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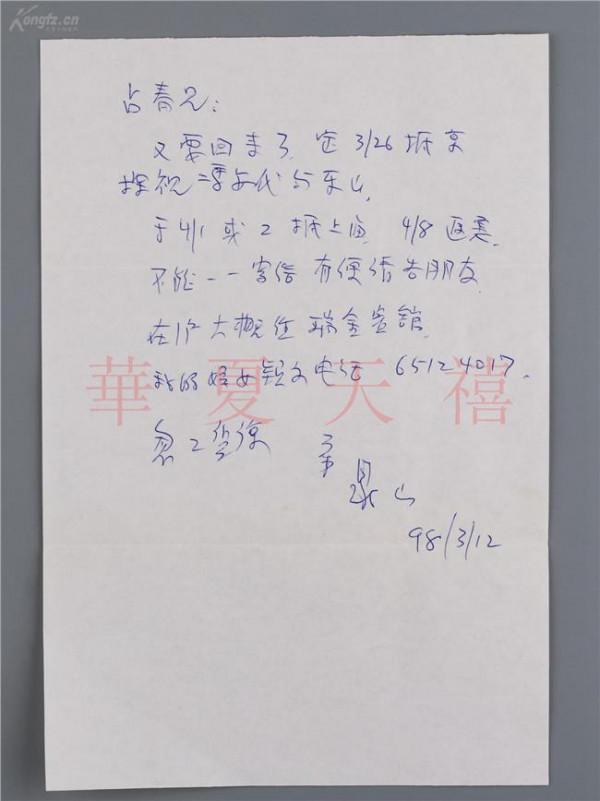


![胡小明上海 胡法光、胡晓明受聘上海交大名誉校董、校董[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4/03/40310efc950564458707e0f04898b42d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