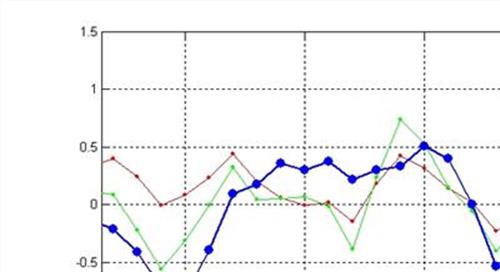张季鸾知日派 一个日本名医眼中的张季鸾
张季鸾研究近年不断向前推进,论文、专著成批涌现,大公报旧人的回忆也相继整理出版。透过这些文字,张季鸾作为报业巨人的风采,在湮灭了半个多世纪后渐渐被今人所了解。
不过,这些回忆文字,因为基本上出自张季鸾同事的笔下,所以多突出其伟大的人格、下笔千言的言论风采,以及爱国忧民的情操。
随便举一个例子即可作为代表。张季鸾去世后的第二天,即1941年9月7日,重庆《中央日报》即刊登许君远的悼念文章《敬悼张季鸾先生》,文中说:“在国家的立场上说,他是一员勇猛的斗士;在《大公报》的立场上说,他是整个事业的灵魂;在朋友的立场上说,他又是一个指路的灯塔,航海的指南针。
”许君远1928年毕业于北大英国文学系,属《大公报》第二代高层决策人。写作此文时,他已加入《中央日报》任副总编辑。他的这段话,基本能代表大公报人回忆、评价张季鸾的调子。
总括起来,同事眼中的张季鸾,属于那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贤者,有庄重的一面,也有亲切的一面。关于后一面,许君远还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只要你是他的一个忠实的同志,他全一律地把你看成他的最知己的朋友。吃喝玩在他面前用不着拘泥,用不着扭捏,尽管大方,尽管放肆。他高兴这样,他不以为忤。”
以往读这段话,想象不到这里所指的“吃喝玩”、“放肆”的具体含义,最近读《谦庐随笔》一书,对此恍然有悟。原来,它们指代旧式文人那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态度与方式,这种旧式文人的生活态度与方式,也很典型地存在于张季鸾身上。而这一点,是从以往回忆张季鸾的文字中看不到的。
《谦庐随笔》的作者矢原谦吉,是民国时期在北平行医的日本人。他出身于武士之家,留学德国多年,医学专业毕业后来中国。由于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矢原谦吉成为闻名华北的名医,连当时内蒙的德王都悄悄到北平请其看病。
矢原谦吉与当时华北军政界及文化、报界的知名人士往来密切。身为值得信赖的医生,一些人在找矢原看病的同时,也乐于向其讲述“心病”。此外,矢原同当时报界的风云人物如张季鸾、管翼贤、张恨水是好朋友,这些人不但经常与矢原餐会,且常向其讲述各类掌故逸闻,矢原遂得以掌握大量内幕。
1938年,由于被日军怀疑帮助中国朋友逃离占领区,矢原在日军逼迫下离开中国,逃往美国。二战结束前,矢原谦吉去世,《谦庐随笔》为其去世前写成。矢原汉语造诣很高,文笔生动,叙事详实,由于其为外国人,所以一般认为,这本主要记录当时中国华北军政要人秘闻的书,比较客观,史料价值甚高。
《谦庐随笔》中,有两篇专门记述张季鸾,此外还多有提到张季鸾之处。矢原谦吉对张季鸾充满敬意,但并不为尊者讳,在他笔下,张季鸾鲜为人知的放浪形骸一面得以呈现。
矢原谦吉是“九一八”前夕来到中国的,前后待了近8年。这期间,他与大公报的几位高层如张季鸾、曹谷冰过往频繁。张季鸾每次从天津到北平,都必于深夜打电话给矢原,邀其到“都一处”、“砂锅居”,或“东来顺”等名饭庄痛饮,而“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也是张季鸾最常去的地方。根据矢原谦吉的记载:
“是时也,张有红袖为枕,间亦略以阿芙蓉助兴,而其谈锋遂愈晚愈健。余尝婉劝其保重之道,首先与吞云吐雾绝缘。张闻语顾左右而言他,曰:阿芙蓉亦如老七,余仅为逢场作戏耳。”
所谓老七,是一名雏妓。“常为楚楚依人之态,张甚嬖之。”如果老七偶尔不在,张季鸾则为之不欢。有时兴起,张季鸾干脆就在老七处伏案挥毫,顷刻千言,写就《大公报》的社评。
《大公报》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报,其社评更执舆论界之牛耳,深为国共两党领袖所器重。张季鸾笔扫千军,是当之无愧的报界宗师。不过,其社评文章,有的是在妓女身边写成,这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此外,张季鸾有阿芙蓉之癖,即吸食鸦片,也是从未见诸披露的。事实上,当时有人因为张季鸾面色黑黄,曾猜测其为瘾君子,但没有确凿的证据。矢原谦吉的记载,虽系孤证,但通观《谦庐随笔》涉及张季鸾之处,多甚为正面,且语带不掩饰的敬意,而矢原谦吉公认是宅心仁厚之君子,没必要去厚污张季鸾,所以我认为这一记述应可靠。
新记《大公报》曾数次就鸦片问题刊发过社评,如仅1928年,就先后于2月7日与4月17日两次刊发以禁烟为主题的社评。其中一篇题为《烟禁与足禁》,将裹小脚与吸食鸦片列为陋俗之列。社评没有简单谴责各种陋俗,而是做了区别对待,认为“各国之改革风俗,惟去其有害者。
至虽陋而无害,则不以法律禁之。盖人性守旧,世界皆然。”社评认为,禁烟为国民保健之本,所以最为重要,相比小脚、留辫子,是应该首先去除的陋习。我手头没有《季鸾文存》,但猜想这篇社评应该出自其手。知易行难,一代报界宗师如张季鸾,其也不免乎!
与大公报旧人笔下温文君子的张季鸾形象不同,与张季鸾有私交的矢原谦吉能看到同事视角中看不到的张季鸾的另一面,也即谐谑、辛辣的一面。对此矢原说:“惟读张氏社评,而不识张氏于笑谈中者,定以其人为一不苟言笑之大师,实则张亦与张恨水同,恃才使气,玩世不恭。倘遇彼所不屑之人与不怿之事,则舌如利刃,尖刻入骨。”而被张所不屑者,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时的国民党人中,除了蒋介石与汪精卫,鲜有能获得张季鸾好评者。
对于蒋介石甚为赏识的将领刘峙,张季鸾在大讲其怕老婆的故事之余,常说:“中央军之有‘峙’者,犹人之有痔也。”这话,当取痔疮虽然不是大病,但却令人难堪、难受之意。刘峙身为黄埔军校教官,在北伐、中原大战时屡建战功,但抗战以后则屡败屡战,被讥为“长腿将军”。张季鸾对其不感冒,未始没有原因。
何应钦也是张季鸾不屑之人。何梅协定签订后,舆论哗然,张季鸾对矢原说:“此何应钦之所以为‘何应轻’也。”
张季鸾是见过大世面大阵仗的人,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参与《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起草工作,因报道坐过两次牢,写社评骂过蒋介石,其胸襟与局面,绝非谦谦君子与恂恂儒者所能框架,这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他的不计荤素、大雅大俗的谐谑风格,还是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三十年代,北平的纨绔子弟多枉法胡为者,为此一家报纸以“养不教,父之过”为题,撰文抨击。张季鸾与张恨水看到这个标题后,大加嘲笑。笑过之后,张季鸾忽然对矢原等人说:“读此标题,使我得一联矣。上联曰‘父之过’,你们能对下联否?”
有人对以“子不语”,张季鸾摇头说:“欠妥,欠工。实未如‘妈的×’之恰当也。”这一联语,虽然沦于不文,但从联艺角度衡量,应属佳对。它不但对得工,也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纨绔子弟不法行径的愤怒。
从矢原谦吉的叙述中,可知其与张季鸾关系确系非同一般。不但张季鸾每到北平必与矢原相约,从他们彼此间的随性与随意,更可佐证这一点。
矢原说,每次与张季鸾、张恨水一起出游时,就会产生严重的自卑感,因为二张在一起或议论,或笑谑,或关白(通报之意),都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是以引用诗词,或引用四六文的游戏方式来交流、沟通,因此往往弄得矢原瞠目不解。
有一次,二张与矢原一起见了美国人福开森,座中西方男女杂坐,二张谈片刻即辞出。出门之后,张恨水对张季鸾说:“盍往访老七乎?此辈西方佳丽,见之徒增‘西望长安’之感,惟其‘玉钩斜’尚差强人意耳。”说完,二人相视大笑,而矢原却不解“西望长安”与“玉钩斜”之意,于是再三请教。二张说,只有当晚在老七那里做一“花头”,才能告诉你。
“花头”即在妓院设宴打麻将之意。矢原好奇心切,遂如二张所请,做了“花头”,知道了“西望长安”即是不见佳之意,而“玉钩斜”即是曲线美之意。二张的对话,原来是指那些西方女人脸蛋长得不怎么样,但身材却很好。
其实,矢原的汉语水平已经相当了得,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也很丰富,这一点,相信读过《谦庐随笔》的人都有体会。只是,在张季鸾与张恨水的渊博面前,矢原汉语再好,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上述细节,都增加了《谦庐随笔》的可读性与可信度。相信作为日本人的矢原,无论如何都虚构不出这么生动有趣的情节与细节。也因此,矢原谦吉笔下放浪、谐谑的张季鸾是可信的。
这个张季鸾,带有旧时文士的习性与气质,逛妓院,吃花酒,吸鸦片,善谐谑,与德高望重的经典张季鸾形象大为不同。它是张季鸾的另一面,与忧国忧民、笔含风雷的张季鸾同样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