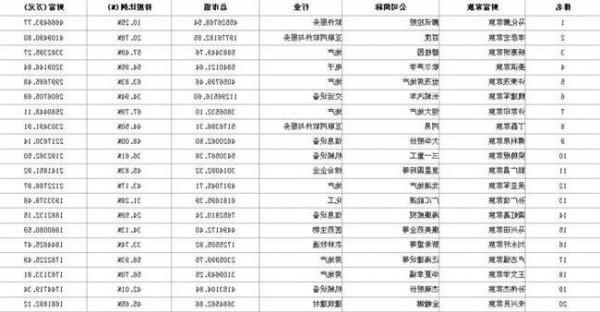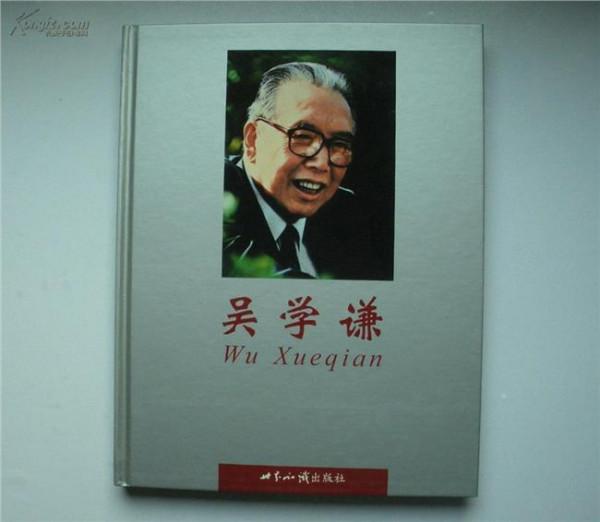吴悦石国画 吴悦石:再论中国书画之关系
被问及近来写字愈多的情况时,吴悦石盘腿、坐在椅子上,淡淡地笑道:"老了嘛,越来越归于写字这条道上了。起于书法归于书法,很多人都是这样,比如启功先生,年轻时候画画多,到了晚年了,写字却成为主业,这就颠倒过来了。"
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关系自古便有论述,上可追溯到河图洛书,说得是汉字之孕育本起于图像,是故书画不能分家。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作"叙画之源流"常为后世引用、被人视作"书画同源"这一范畴的最早论述:"颉有四目,仰观垂象。
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而后元人赵孟頫在《窠木竹石图》上的跋文更成为千古流传的经典言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对此,吴悦石评价道,赵孟頫的论断,大约是从形式上最早明确论及书画关系的内容。书法的成熟早于绘画,而将用笔的技巧融入其中——画木用籀书(大篆)笔法,画叶子的时候要用八分书(隶书),这在当时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但是放到今天来看,也有着一定的问题。首先就是太过于具体,"不应从形式上做出严格区分,而应是意会的。
将运笔的精髓了然于胸,而后在画竹木山水时打通运用,不拘泥于偏锋、逆锋正侧等讲究。正所谓以书意用笔,追求的是一种境界。书法中的用笔程式,直接运用到画上的说法,显然过时了。如果仍然执意依循,那就刻板了,实际上会扼杀笔意在画中的体现。"
而论及以书入画、书画兼修的大家,吴悦石推举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三位。相比书印,吴昌硕学画较晚。坊间相传他30多岁开始学画,经高邕介绍至任伯年处求教。任伯年要他试作一幅画来看看,吴昌硕畏难道,我还没有学过,怎么能画?任伯年则说,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随便画几笔看看。
于是吴昌硕只得画了几笔。任伯年看他落笔用墨浑厚挺拔,不同凡响,有超越自己的气象,不禁拍案叫绝,当即便下了定论,认为他将来在绘画上一定成名。
后来,吴昌硕喜画兰竹,墨笔纷披、藤条老劲,吴悦石谈道,"吴昌硕酷爱临《石鼓文》,能把行草写出《石鼓文》的味道,而在绘画中用的也是这种篆籀笔意。他曾自谓生平得力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至今,我们仍能见到吴昌硕在绘画上题写的跋文,印证了这一点:"草书作葡萄,笔动走蛟龙。"(题《葡萄》图)又有"离奇作画偏爱我,谓是篆籀非丹青。"(题《荷花图》)奔放雄健,气势磅礴,一开以金石法作画先河。
白石老人在绘画上有"衰年变法"之说,而其时,篆刻亦在变化,摆脱摹袭、出新自造,大抵便是在赏鉴《祀三公山碑》的过程中。《祀三公山碑》是名垂书史的汉代碑刻,其字体在篆隶之间,翁方纲云其"错落古劲,是兼篆之古隶也"(《两汉金石记》)。
方朔评云:"作阅之有似《石鼓文》,有似《泰山》《琅琊台刻石》……仅能作隶者,不能为此书也;仅能作篆也,亦不能为此书也;必两体兼通,乃能一家独擅。"(《枕经金石跋》)这一变秦篆之圆转为汉隶之方折的古劲碑刻为齐白石的创新提供重要依据,更使其兼容于书画印之中。
吴悦石评价道:"(写此碑)白石老人多用方笔,而《祀三公山碑》其实并不方,只是体势方。旁人用圆笔,而他用方笔,这就是本事和气魄的显现。
书法外,在绘画、篆刻中也多有体现:画叶子枝干,执笔如刀,仿佛砍下来一般;而篆刻上也是一样,拿刀铲下去,都是一路。是谓软锋薄纸,力量很大,含而不露,意都在含蓄之中。"
以山水画闻名于世的黄宾虹曾在幼时与邻居一老画师请教画法,后者答曰:"当如做字法,笔笔宜分明,方不至为画匠。再叩以作书法,故难之,强而后可。"多年后,黄宾虹对其学生说道:"我的书法胜于绘画。"不知那时,他是否感念那个将书法播种在他心里的老画师。
从懵懂未开至后来"吾尝以山水作字,而以字作画"的自述,又及"五笔"与"书法入画"等概念的提出,黄宾虹终生于书艺上探索,并尤为推崇金石家。"他写钟鼎,主要写金文,金文用笔很圆,他提倡笔意的厚重。故而,我们从这三家每一个人的书学经历入手,就可以循迹到他的专攻和糅合,书法在绘画上就有所体现了。"吴悦石道。
在吴悦石看来,历史上有成就、成大名者都是书画兼修的,二者之间互相促进的,"书家的字有时不如画家生动,因为画家与纯粹书家不同,不太拘泥于‘清规戒律’,比如何时该出锋、使转,反而拓宽了书法的境界,从这个角度而言,画家的胆比书家大"。
但他同时也强调创新有法,在反观书中有画意、以画入书等问题时,提出要区别于"画字"(指把字用画画的形式来写出),要遵从书法的边界和原则。他说道:"吴昌硕70岁自谓临《石鼓文》,‘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30余岁得《石鼓文》的藏刻本,40余岁得到潘瘦羊相赠的手拓本,终日挥毫临习,心摹手追。
反观我们自身,如今可以借助各种手段把魏晋以来的名迹都看到,但是心大眼杂,心手不专,故而学不好。所以关键的,还在于沉静下来、默默体悟,才可觅得蹊径,悟其境界之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