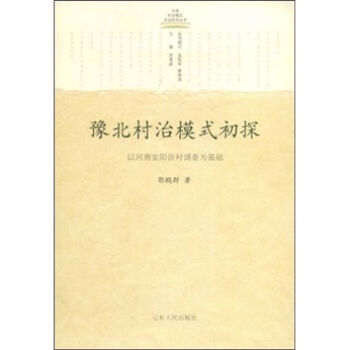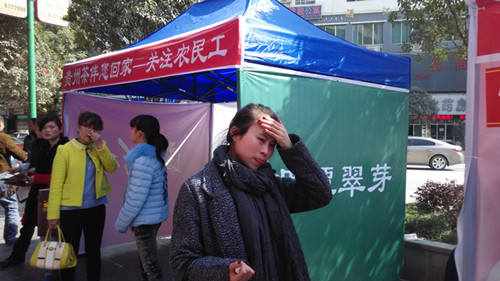贺雪峰村治模式 贺雪峰:论村治模式
讨论自上而下的政策在农村实际执行的过程与结果,离不开对农村社会本身的讨论。农村社会具有相当不同的结构,不同结构的农村社会,会对同样的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作出不同的反应,并因此制成不同的政治社会后果。我们可以将特定的村庄结构及其对政策反应的特殊过程与后果,称为村治模式。因为村庄社会结构不同,而致使同样的自上而下农村政策有不同的反应,从而有不同的村治模式。本文拟对村治模式作初步讨论。
一、村治模式构成要素
从前述对村治模式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提取出村治模式的三个构成要素,一是特定的农村社会结构尤其是村庄社会结构;二是特定村庄社会结构对政策反应的过程与机制;三是后果即自上而下政策在特定结构的村庄社会制成的特定政治社会后果。以下分别讨论之。
村庄社会结构,当然不只是指村庄社会层面的结构,而且包括构成村庄特质的各个方面,比如特定的种植结构及文化传统,都是构成村庄特质的一个部分,并可能对自上而下的政策产生不同的反应。不同的村庄特质之间具有复杂的因果关系及相关关系,如果我们不是要展开对村庄特质本身的讨论,而仅是讨论村治模式,则我们可以将各种可能对政策作出反应的村庄特质归总称为村庄社会结构,或者叫做村庄结构。
对不同的政策,村庄结构中的不同特质会凸显出来作出不同的反应,或者说,因为研究村治模式的侧重点不同,而需要对村庄结构中的不同方面(特质)进行凸显并因此对村庄结构作出定义.
村庄结构的另一种说法,即我们此前一直研究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核心不是要讨论一个具体的乡村社会是什么,而是要讨论不同的乡村社会差异,尤其是村庄类型的差异。村庄类型的说法强调了从理想型视角来进行简化的学术比较,因为研究侧重点不同,而可以凸显村庄不同方面的差异,从而可以构造出相当不同的村庄类型来。我们曾着重从社区记忆与社会政治分化两个层面来定义村庄类型 [1]。
村庄社会结构这一要素的核心要义是,中国农村是非均衡的,不同村庄社会的结构具有巨大而丰富的差异,只有我们对村庄社会结构中的这种差异有了清晰的研究,我们才可能对不同的村治模式作出有益的定义与比较。
村治模式第二个构成要素,是村庄社会结构对政策反应的过程与机制,不同政策所针对的社会结构是不同的,因此,不同政策在村庄遭遇到的反应过程和机制可能会有所不同,且这种不同政策因为在不同村庄遭遇到的村庄结构因素的差异,而会有不同的反应过程与机制。
先具体考察不同村庄的不同结构因素对一些特定政策作出反应的过程与机制,由此凸显出特定村庄类型的差异及其对具体政策反应的特殊过程和机制,再更抽象一些考察不同类型村庄对不同政策作出反应过程与机制的倾向,而在村庄类型与一般性的政策实践之间建立联系,比如,中国南方村庄总体来讲更具内聚性,因此,自上而下的政策在村庄层面的实践时,更加可能作出有利于村庄而偏离政策本意的调整,而北方村庄总体来讲内聚力较弱,自上而下的政策因此容易在村庄层面贯彻到底。
换句话说,在南方村庄,中央权力往往显得遥远,而北方村庄中,中央权力则容易渗透进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南方离中央政权较远而北方离中央政权较近 [2],而是村庄内聚力的差异。
村治模式的第三个构成要素是自上而下农村政策在特定村庄制成的政治社会后果,这种政治社会后果构成了村治的现象,也即我们讨论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也具有复杂而丰富的结构,正是呈现出来的十分不同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使我们可以感受到村治模式的差异,并因此探求构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尤其是探求村庄社会结构及其与农村政策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和过程。
举例来说,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同样的农民负担政策,在不同地区却造成了相当不同的农民实际负担的状况。
有些地区,农民负担超乎寻常地沉重,还有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多,农民负担却相对较轻。对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农民负担轻重不同,学术界大都倾向认为是地方政府作为不同所致。
这个意见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所有地方政府都有追求扩大财政收入的冲动,那些农民负担轻的地区,地方政府为何会抑制住扩大财政收入的冲动?如果我们考虑了村庄社会结构,即在村庄层面农民组织起来利用政策维护自己利益能力的差异,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在那些农民组织能力较强的地区,农民可以凭借于己有利的中央政策与地方政府抗争,从而使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些政策落到实处,而在那些农民组织能力很差,不能凭借于己有利的中央政策来与地方政府抗争的地区,地方政府就成功地扩大自己的财政收入,农民负担也因此变得沉重。
村治的核心是村庄维护和再生秩序的状况和能力,村庄秩序是由两种力量建构的,一是村庄内生的力量,二是外来的行政性的及其他的(如法律规定)力量。外来力量要在村庄发生作用,也要与村庄社会结构中的一些侧面发生作用,并因此制成特定的村庄秩序状况。在村庄维护和再生其秩序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殊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构成了特定的村治模式,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来定义村治模式。以下举两个层面的例子来予以说明。
二、村治模式的两种类型
如果我们注意到了不同地区农民行动单位的差异,我们就能够对相当多不同地区农村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差异作出较好解释。比如上述农民负担,在同样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央政策下面,农民的行动单位越大,组织能力越强,则农民越是可以利用中央政策中于己有利的方面,抵制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收入,增加农民税费负担的能力。
在宗族组织较为健全的村庄,村干部一定不会(也不敢)充当县乡两级政府加重农民负担的“代理人”。县乡两级违反中央政策加重农民负担,农民就可能在宗族范围内组织起来,抗议县乡政府,这种抗议的声势很大,一次抗议,足以使县乡政府牢牢记住扩大财政收入所要承担的风险,从而在相当范围和时间保证农民负担不至超过中央规定太多。
而在一些地区,农民组织能力解体,面对远远超出中央规定的农民负担,却难以组织起来进行抗议。
当农民负担太重以至无法负担得起,当县乡政府扩大财政收入的冲动永无休止,而不断地到农民家牵牛扒粮时,农民的极端反应却是一死了之,以死抗争 [3]。
农民的行动单位,在不同地区确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江西、福建的相当部分地区,宗族组织还比较强有力地存在;在河南、皖北,小亲族组织(尤以兄弟、堂兄弟为主)多强有力地存在;在山西、陕西关中地区,较宗族规模小、较小亲族规模大的以办理红白事为主的户族(门子、房)广泛存在;在湖北、东北等地区,农民的行动单位则往往以户为单位,兄弟之间的一致行动能力也大部丧失,农民成为原子化的个体。
农民的行动单位不同,就会导致农民作起来维护共同利益的一致行动能力不同,也就会对诸多政策及现实的公共事务要求的反应不同,由此制成了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不同。
从农民行动单位的角度,可以发现,不同农民行动单位的村庄,村民政治社会现象的产生具有规律性,比如,在宗族村庄,一般不会发生针对村干部的群体上访,因为没有这个必要;而在原子化的村庄,一般不会有农民无论是针对村干部还是针对县乡干部的群体上访,因为群体性的行动难以组织起来。
而在小亲族组织发达的村庄,农民频频针对村干部进行群体上访,一个群体将在任村干部告下来,被告下来村干部所在群体又会上访,以将新上访的村干部告下去。
农民上访可能性及针对对象的差异,就构造了诸如农民负担、村级债务、村庄内部的公共事业以及乡村关系的差异,这些差异总起来,就构成了不同村治模式的外观差异。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以农民行动单位作为关键的变量,来构造出不同的村治模式,这样就有了以江西、福建宗族农村为代表的大规模行动群体的村治模式,以湖北荆门农村为代表的以农户为主要行动单位的村治模式,以安徽阜阳为代表的以小亲族为主要行动单位的村治模式,以及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代表的以户族为主要行动单位的村治模式,这些村治模式,如果加以典型冠名,也许我们可以分别冠之以宗族模式、荆门村治模式、阜阳村治模式和关中村治模式。
以农民行动单位的差异为关键变量,来考虑村治状况的不同,并以此来界定不同的村治模式,是村治模式研究的基本方法。同一类型的关键变量还可以取诸如:种植结构差异,尤其是水稻作物与旱作物的差异,经济结构的差异,尤其是工业化程度的差异及收入构成的差异;聚居方式的差异,尤其是集中聚居村庄和分散居住村庄的差异;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等等。
这种区分村治模式的办法,是选取村庄内生变量作为确定村治模式的关键变量,并由此对一系列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区域或类型差异进行讨论,最终确立起不同的村治模式。
注意,构成以上确立村治模式关键变量的村庄内生变量本身,又是由一系列村庄其他内生变量来确定的,或与其他村庄内生变量有密切关系。
确立村治模式的另外一种办法不是仅仅依从村庄内生因素作为关键变量,而是选取一个主要的村治制度作为确立村治模式的主要变量,并以这一维度的村治要素为核心,来清理相关各种村治现象与之的相关关系,并由此构造出不同的村治模式。
例如,可以根据村治资源基础的不同,区分出动员型村治和分配型村治 [4],所谓动员型村治,即村庄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动员村民将资源集中起来,以应对村庄公共事务之需要,比如集资架桥,出工修路等。围绕村庄资源的集中,村治会表现出诸多的特征出来,比如,在动员型村级治理中,往往存在少数人决定的问题,即只要少数村民反对,有利于全村的公共事业便难以建设成功。
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大多以一致通过的方式产生决议,而少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强制性措施。
而在分配型村级治理中,因为村集体已经有较为充裕的资源,尤其是资金,而使村治变成如何将村集体占有的资源有效分配到村庄不同的利益群体之中,这样的村治,往往会变成多数人专制,即多数人可以不顾及少数人的强烈抗议,就能够将村治实施下去。
这种以村治中的一个主要制度来构造村治模式的办法,对于理解和区分村庄的治理现象,具有现实意义。不过,进一步讨论就会发现,构成动员型村治和分配型村治的关键,往往是村集体经济的状况不同。在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村集体不用向村民筹集资源,即可以将村中公共事业办成。
村干部为了在办理村庄公共事业中不致不合制度,他们就要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将他们使用村集体资源办理村公共事务的行动,变成全体村民的集体行为,是村民同意的行动。
而在村集体经济不发达的村,办理任何公共事业都需要向村民筹集资源,因为缺乏控制强制措施,如果有村民反对,这个资源的筹集过程就无法完成,村集体的公共事业也就会因为少数村民的反对而进行不下去。
如果制度安排允许村庄办公共事业时,可以以多数人决定的办法征税(即筹集公共事业资源的办法具有强制性),则动员型村治与分配型村治的主要差异就会消失。或者国家可以将较多的资源转移支付给村集体而非村民,由村民集体来进行“人民预算” [5],则这两种村治模式的大多数差异也会消失。
以上两种确定村治模式办法的核心,都是选择一个可以建立区分村治模式的主要变量,然后以此展开相关变量与之的关系,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村治类型及村治模式。如前已述,村治模式应该是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特定的村庄社会结构,二是特定村庄社会结构对政策反应的过程与机制,三是自上而下政策在特定结构的村庄社会所形成的政治社会后果。
其中第一种确定村治模式的办法是选取特定的村庄社会结构因素作为区分村治类型,建立村治模式的主要变量,而第二种办法则试图从村庄社会结构对政策的反应机制中抽取一个主要变量,以建立不同的村治模式。以下我们举例说明如何建立起村治模式。
三、以农民主要行动单位为基础的村治模式
如果以农民主要行动单位为基础来确定村治模式,我们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所谓农民的主要行动单位,即农民生活中,可以在何种规模、何种程度及何种事务上组织起来的单位,因为农民在不同事务上组织起来的规模和程度可能会有不同,农民的行动单位就会有所差异。不过,只要我们足够仔细(或者足够粗疏,这要从那个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不同地区农民的主要行动单位仍然明显不同并可以比较的,或者说我们仍然可以从不同地区农村区分出一种主要的(当然也是相对于其他地区农村的)行动单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