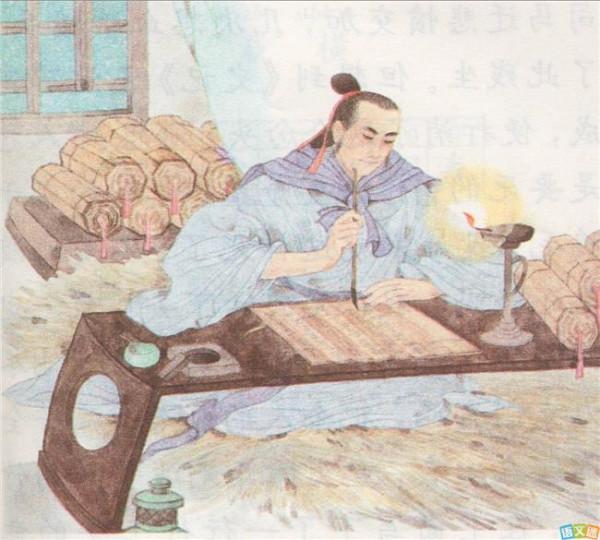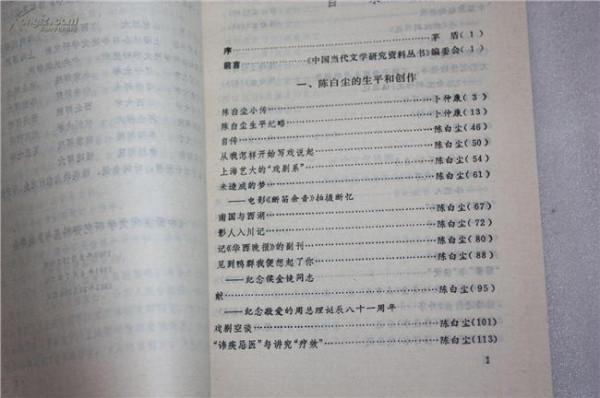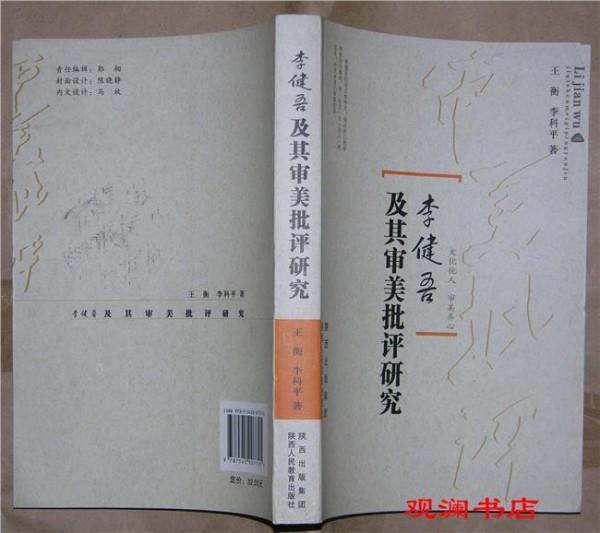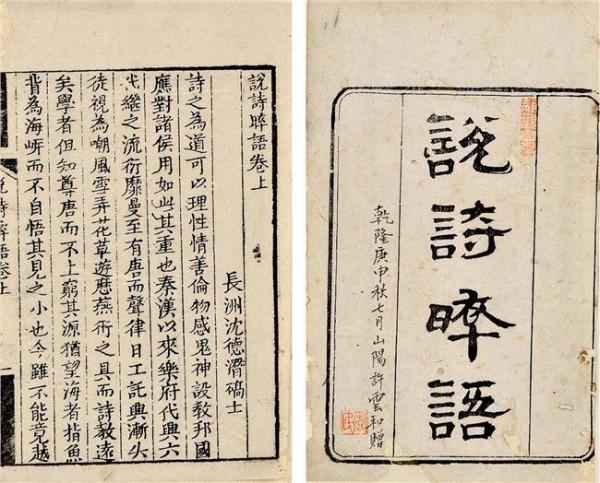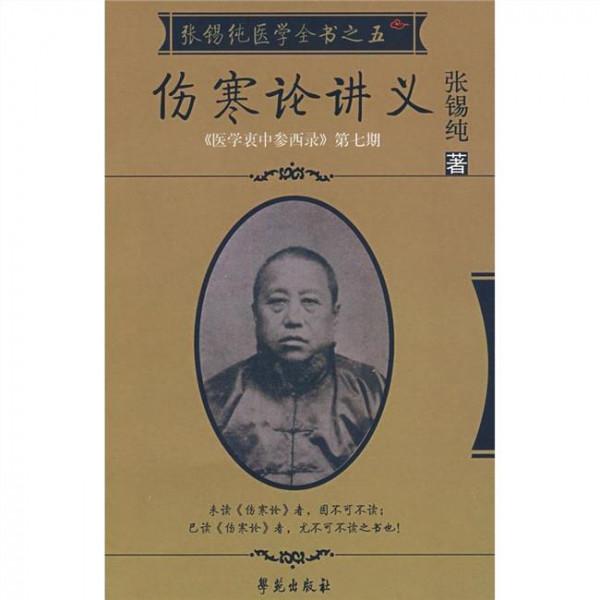司马迁的生死观新论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他写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韶”。由此故,古人与今人论述司马迁与《史记》的文章特别多,可谓汗牛充栋。笔者不揣浅陋,仅就司马迁生死观的三个方面作一下探求。
1.司马迁的人性论对生死观的影响。“汉代人普遍认为人性本恶,倾向于荀子的人性观。 司马迁也不例外,他对人性的看法主要受黄老和荀子的影响,认为人性本恶,认是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
人的自然本性和生存本能,在生活中往往超出道德因素的制约,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儒家说父子恩情出自“天性”。司马迁很怀疑这种说法,在《史记·卫康叔世家》中感慨地说:“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相让……然卒死亡,何其悲也!
或父子向杀,兄弟向灭,亦独何哉?”他自己在遭李陵之祸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饱尝了世态炎凉的苦楚,对人性的冷酷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在对世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后,他指出:“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 ,“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司马迁的这种人性论不仅对其历史观、人生观等许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在其生死观众也有明显的反映。他在《伯夷列传》众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这段话既是对天道的质疑,对善人不得志,恶人横行的不满,也是对人应当怎样活着的思考:人应当为善还是为恶呢?人应当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呢?同时司马迁还对大人物的死和受辱做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在《报人安书》中列举了西伯、李斯、淮阴侯、彭越等人受囚的例子后说:“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并进一部分析说:“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这就打破了大人物身上附加的光环,洞悉了这些历史人物的真相与本来面目,他们并不像书中记载的那么崇高神圣,处于劣势时他们同样忍受着卑贱屈辱。甚至他们的慷慨一死,有时也是出于“不得一也”。当然,司马迁揭示的是一种普遍现象,他并不否认,甚至激情地赞扬、提倡那些“弃小义,雪大耻”的人物。
2.注重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生死观。诚然,司马迁的生死观有着丰富的内涵,但注重人生价值实现,扬名于后世,成就大我,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司马迁赞扬忍辱含垢,以就大业的生,反对苟且偷生和随意轻生。
为此,他赞成韩信的忍受胯下之辱;伍子胥的弃小节,背父兄,去国远逃;勾践的卧薪尝胆。他在《伍子胥列传》中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
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热情讴歌了那些忍辱负重,以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司马迁自己又何尝不是这种人呢?他受宫刑之后,“肠一日而九回”,“局则乎乎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他最终选择了活着,因为“恨私心有所未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司马迁既赞扬“弃小义,雪大耻”的生,也赞成不甘屈辱,保持名节的死。为此,他饱含深情地描写田横耻于降汉的自刎,李广不堪面对刀笔吏的自杀,项羽愧对江东父老的自杀,栾布为尽臣子之义,“哭彭越,趋汤如归”。
他赞美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圣贤”,“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像屈原那样“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洁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自投汨罗江,虽令才人志士痛心丧气,但这种死却激起人们对于昏君佞臣的痛恨,引起人们对于更广泛、更深层的许多问题的思考,树立起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人格。
关于生死观问题,有时确实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古往今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对此进行了自己的解答。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发出了“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的千古疑问。对这一问题,司马迁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那就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认为是生还是死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是否有意义,是否能实现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
3.司马迁生死观中的道家倾向。前人对于司马迁生死观的论述多从其含垢忍辱,发愤著书着眼,认为其生死观体现了儒家向上奋发的精神,而对其生死观中的道家倾向论述不足。
司马迁道家家学深厚,其父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并著有《论六家要旨》极力称赞道家。司马迁本人也是儒道俱重,因此其生死观不可能不受道家影响。此现有材料来看,司马迁生死观中的道家倾向在其晚年表现得很明显。
据王国维先生的观点,司马迁(前145—前86)因李陵之祸受宫刑在公元前98年,于次年升任中书令一职,在公元前93年基本上完成《史记》的撰述。中书令侍从皇帝左右,出纳奏章,位卑而权重,被朝野目为“尊崇任职”。
此时司马迁又深得武帝信任,可以说这段时间是司马迁权重而少事的时期。由此故,任安才写信给司马迁要求其以“推贤进士为务”,并希望他能在皇帝面前为其求情,以免除其罪。
司马迁却以刑余之人,扫除之隶不足以“论列是非”来推却,并且说“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指谬乎。”可见司马迁内心深处是不愿再参与世事的,希望老于林泉,只等一死。这种做法的对与错今且不论,但这种做法本身却反映了其思想的消极,对政治的冷淡和世事的不关心。
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 完全是道家的行为与处世方式。这与其以前的积极入世截然相反。前者,他“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李陵之事时,还“不自料其卑贱”为其求情。
如今尊崇任职,却不愿多发一言,这反映了司马迁在生死观上更趋于道家的无为。这种生死观中的道家倾向,在其晚年写的《悲士不遇赋》中说得明白。
他说:“委之自然、终归一矣”,“无造福先,无触祸始”,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积极行事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听之自然。从以上论述可见,晚年司马迁生死观中的道家倾向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