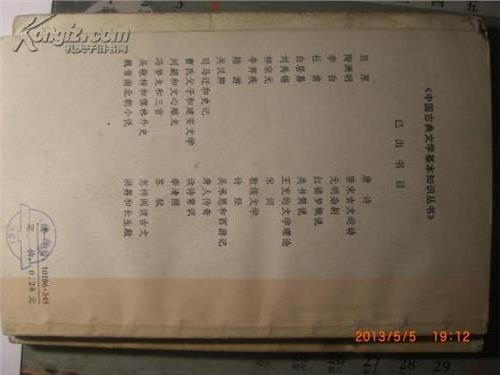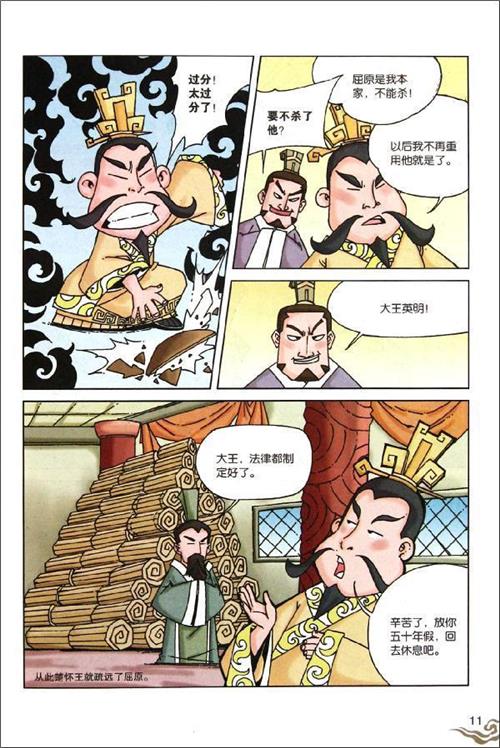司马迁与屈原的共鸣
【内容摘要】: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入狱受宫刑,忍辱负重写下文史巨著《史记》。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部52万多字的纪传体史书与一篇2490字的长诗,在文学抒情的意义上相媲美,表明司马迁与屈原的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共鸣。这种共鸣主要表现在两人的身世经历、价值取向、创作观、生死观四个方面,司马迁在这四个方面对屈原有着深层的心理认同感。
【关键词】:司马迁 屈原 政治经历 价值观 创作观 生死观
【正文】: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入狱受宫刑,忍辱负重写下文史巨著《史记》。正如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样,《史记》不仅是历史巨著,而且在其文学意义上及地位上也是可以和屈原的《离骚》相媲美的。鲁迅把二者放在一起是源于他们各自的巨著,那么,司马迁和屈原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否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共鸣呢?换句话说:司马迁是否对屈原有一种心理认同感?这便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本文主要以《史记》为主要材料从二者的身世经历,价值观取向,创作观以及生死观四个方面的比较来探讨司马迁和屈原的共鸣。
一、身世经历同病相怜
考察二人的身世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司马迁与屈原两人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但其经历有相似的部分。屈原在其巨著《离骚》中描述自己的身世如下: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1]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描写屈原的身世也说道: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彊志,明於治乱,嫺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2]
无论是屈原自己的描述,还是司马迁的描述,我们都可以看出,屈原的出生是极其高贵的,是楚国皇族。从屈原自己的描述也可以看出,他并不是跟其他皇族一样,整天闲情度日,而是把自己跟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相比而言,司马迁的出生就没有屈原这样显贵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如此描述自己的身世: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適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適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後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於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於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3]
司马迁祖上世代任史官,同时自己也继承父志做了史官。同屈原相比,司马迁的身世要卑微的多,而且有史以来,史官也是不被人重视的职位,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的: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闲,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4]
但是二者在政治经历上并没有因为一个身世显赫一个身世卑微二有所不同。二者的政治经历,一言以蔽之:失意,挫折。屈原显赫的身世,并没有给屈原在政治前途上带来好处。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中写到:
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拟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5]
王道昏庸,小人当道使得即使与楚王同姓的屈原的人生也充满了挫折跟失意,也逃不了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命运。然而可贵的是,屈原在被疏远之后并没有放弃国家,仍然在国家危难之时直谏君王。也正是因为这样可贵的品质,使得屈原最终被放逐,投江而死。司马迁也因李陵之祸入狱,受宫刑,究其根源,真的是司马迁犯了“欺君之罪”了么?还是由于王道昏庸,小人当道。
可以说,两人虽然身世一个显赫一个卑微,但在政治前途上,却有同病相怜的一面,也正是由于这种同病相怜的因素,使得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对于屈原一类怀才不遇的文人多了几分崇敬跟同情。
然而,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若司马迁不是司马迁,屈原不是屈原,他们跟大多数人一样安分守己,不去过问过多自己职责之外的事情。比如司马迁就安安分分的做他的史官,皇帝让写什么就写什么,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屈原安于做他自己的皇族,平日里与其他王公贵族一起赏赏花鸟,喝喝闲茶,不去过多的涉及楚怀王的政论。他们的前途是不是将被改写?他们也许不会一个受宫刑,一个投江而死?然而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司马迁和屈原的政治悲剧不仅仅是由“王道昏庸,小人当道”这个简单的因素造成的,更多的则是源于二者的价值取向。
二、价值取向心灵相通
前面已经说到,如果司马迁和屈原都安于自己从祖上继承下来的身份,那么他们的前途将被改写,当然,历史也将会被改写,中国文学史上不再有《史记》和《离骚》两座并峙高峰。看完他们的身世及政治经历的简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悲剧除了历史特有的背景之外,更多的是源于二者自身的性格和人身价值观的取向。可以说,司马迁和屈原身上散发着一种共同的伟人气质:正直刚毅、不屈于权贵、洁身自好。所谓王道的昏庸及小人当道对于司马迁屈原而言不过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社会大背景、是个衬托而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还是有很多人生活的很好,还是有人得意。前面已经提到,如果屈原就过普通王公贵族的生活,他的历史将会被改写。然而,屈原生来就是刚直不阿的君子,在其诗作中,他也常以“香草”自喻,在《离骚》中他高傲的写到:
屈原追求的是一种高洁的品质,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甚至在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都觉得屈原就是一疯子。然而,细细想来,这正是屈原与众不同的地方。而在其临死前所作的《怀沙》屈原更是表现了他刚直不阿洁身自好的人身追求:
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画职墨兮,前度未改;内直质重兮,大人所盛。[7]
在屈原的心中,抛弃正路走邪道是会为君子所鄙弃的。他主张明确规范,牢记法度,认为品行忠厚,心地端正,才能为君子所赞美。可以说屈原的一生都在坚持他的刚直不阿,品行忠厚的原则。直到死前汨罗江渔夫劝他:
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8]
他仍然是义正言辞的回答说:
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9]
也许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这一段情景是司马迁预设的或者是原本存在的。但无论怎么样,这一段话与屈原本身的追求是相符合的。屈原的确是一个宁愿“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也不愿被尘世污染的人。同时,这段话还巧妙的将司马迁与屈原的品质相通之处联系在一起了。可以说,二者在性格上,在价值观上是心灵相通的。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写到: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後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屈平行正,以事怀王。瑾瑜比洁,日月争光。忠而见放,谗者益章。赋骚见志,怀沙自伤。百年之後,空悲吊湘。[10]
由此可见,司马迁在赞扬屈原文学方面成就的同时,更加敬重的便是屈原这种刚直不阿、敢于直谏的高洁品质,这些品质与司马迁的品质是相通的,相似的。可以说,这种性格是二者穿越时空产生共鸣的根本原因,所谓志同道合,便是如此。正因为二人在思想与灵魂深处的一致性使得司马迁对屈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11]
就是这段话,让我们知晓了司马迁为什么为李陵辩护,既不是因为是知己,也不是因为是亲戚,仅仅只是因为他欣赏李陵的孝、信、廉、义、礼和恭俭的高洁品质。也就是因为欣赏这些高洁的品质,他向汉武帝直谏而惹来宫刑之祸。这样的司马迁令人感动,我们不难推测,拥有这样的性格,持有这样的价值取向,即使下一次,李陵,张陵或是王陵出了同样的事情,司马迁还是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去直谏。因为这是他的价值观取向所决定的。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到: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12]
可以看出,司马迁崇敬屈原是由于其善于讽谏。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高度赞扬屈原说: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3]
这与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对屈原的态度是相映衬的。可以说,二人在人生价值观的取向上是心灵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