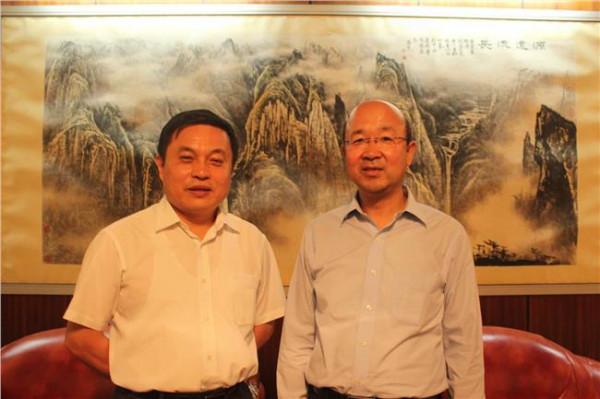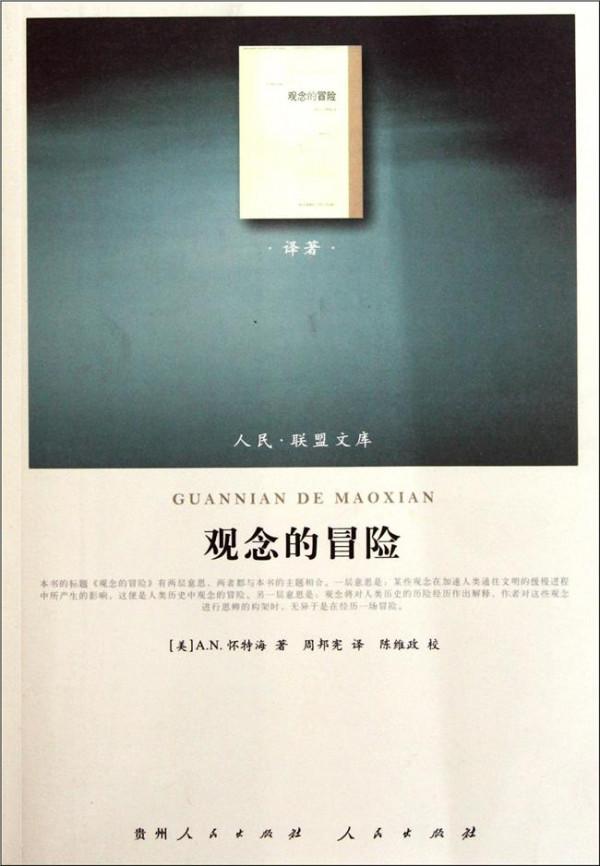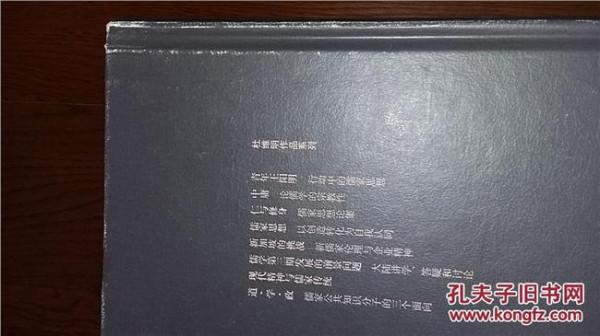陈思和初瑞雪 人文精神再讨论(陈思和王晓明张汝伦高瑞泉)(之一)
陈思和:已经十八年过去,那么久时间了,这么多年没想过这些事情。刚才汝伦说的当时的感觉是对的。其实当时大家只是有一种不安,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基本上是二元对立的,人们关心中国的未来,要么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要么就可能退回极“左”路线的那一套,当然知识界基本上是倾向于坚持改革开放的。
但是到了1992年以后,突然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大潮就汹涌起来,“开放”了。这个东西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来说不是一个新时代,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时代,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过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
其实在1949年以前生活过的人都明白,社会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用不着大惊小怪的。计划经济是1949年以后才实行的,才是很短的时间,但因为我们年龄比这个计划经济更短,所以我们就大惊小怪的,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市场经济突然开放,再加上1989年的政治风波,两件事撞在一块儿,对知识界来说,那个时候政治形势是没有办法公开去反思,所以就把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情都转到了经济话题上。
表面上看这两个问题并不相干,甚至有点相冲突,但是政治、经济、社会内在的矛盾性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怪诞的形态表现出来。这个内在矛盾包含了中国社会以后二十多年发展的基本形态,直到我们今天,不仅没有从这个内在矛盾中摆脱出来,而且冲突越来越尖锐了。
我们这代人,因为从小受的教育是反资本主义经济的教育,当时我们习惯的思维模式是对市场经济抱着警惕……其实到今天为止,中国这十几二十年来的市场经济,我们并没有感到陌生啦。
为什么没有陌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读过当时的所谓政治经济学理论。今天社会上被揭露出来的大量不法分子,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置道德法律于不顾的现象,就是马克思当年指出的,资本家为了追求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连上断头台都不怕的现象。
其实这套道理到今天,我觉得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对资本的描述也没有过时。所以在1994年那个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这样一种市场经济大变革,会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习俗都带来强烈冲击,可能在人文立场上带来的冲击更大。
这个问题,不是危言耸听,这二十年来实践是被不幸而言中的。但当时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受了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过于警惕而带来的忧虑,或者是一种不习惯,不适应。
但是我们提出的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根源肯定不在当时刚刚开始的市场化(因为它的危害性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而恰恰是近五十年的历史,是所谓的计划经济和对意识形态高度控制的政治形态才导致了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和人格的软化,所以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人文精神”讨论是从“寻思”开始的,所谓“寻思”是因为人文精神已经失落了,但是只有在市场经济兴起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把它提出来“讨论”,而且讨论的问题是从市场经济初期可能会带来的消极后果的忧虑开始的。
这样,这个讨论必然会带来两个后果:一个是它引起的社会反响是多方面的,有对政治上的极“左”路线以及计划经济下人格萎缩的反思;也有对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人欲泛滥的忧虑。
同样,它也带来了两种批评意见:一种认为我们是在批判市场经济,反对改革开放;另一种是认为我们还在延续启蒙的旧话题,还是自由主义的老调。
时过十八年再来看这个问题,我还是要问一下:中国的决策者在近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并不陌生,可是在全国推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关键时刻,为什么不在思想理论上对商品和资本可能带来的腐蚀性和破坏性作充分的警惕呢,为什么不把它放到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考中去解决呢?这些问题本来应该是理论工作者首先去进行的,结果轮到人文知识分子外行地提出这些问题来,不可能真正地打中要害。
人文知识分子只能在人文精神的立场和范围内思考和提出讨论,其局限性是必然的。
而且这些问题不是在高层次的范围里争鸣而是被媒体炒作式的开场,也是一个局限。任何理论问题进入大众媒体层面就变了味。人们可能广泛关心的就是汝伦刚才说的,我们拿三百块,人家拿三千块,人家就说我们眼红了。但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你拿三百块,人家拿三块。他也会说,你们拿了三百块的,还讲什么人文精神,你不让我们吃肉吗?
张汝伦:有哦,那个时候有人说了,你现在这个工作很稳定,社会地位也可以,你在讲风凉话了。
高瑞泉:思和讲到这个“不安”,是当时许多人共有的。把“存在决定意识”教条主义化固然让人反感,但是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一定会冲击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经济地位的升降。本来是一个几近凝固的社会结构,很少流动,现在突然横向的和纵向的流动同时猛烈起来,给九十年代初的普通教师造成的压力太大。
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出差都还不能坐飞机,好像除了没钱还有一个级别问题,出差通常坐火车嘛。从新客站下来,打车,司机就问到哪里?到华东师大。
沉默两分钟,司机保证会说:“大学老师还是老清苦的哦!”很衷心的。这个事情我在其他地方可能不止一次讲过,为什么?因为对历史有点了解的人来说,这个情景构成了很大反讽,很有代表性。回过去七八十年,“五四”时代,差不多鲁迅、胡适、周作人、李大钊这些人都写过小品文甚至诗,表示对人力车夫那些下层劳动者的同情。
说明在启蒙主义者那里是比较普遍的感受。他们的收入是人力车夫的几十倍,面对贫穷的劳苦大众,未免有一种道德的歉疚感而不安。
现在是倒过来,司机同情大学教授,因为那时候出租车司机一个月拿三四千块,而年轻的大学教师可能就是月收入三四百元吧。街上不是流行所谓“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吗?造导弹的人我们不敢说,至少一般学者,其实并不是真的吃不上饭了,尽管家里的房子只有几平方米大,买苹果时要挑挑拣拣——拣便宜的买,让摊主很不屑,毕竟与在农村插队时的日子已经不能比了。
但是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相对贫困化的威胁让许多人很不安。
更何况对于即将到来的商品经济的社会秩序,一般人文学者并没有实际的思想准备。记得有人很愤慨地断言:新时期的社会秩序已经排定,商人第一,文化商人次之,文化人最末。在许多人心底,还是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排序,瞧不起商人。
改革开放前的排序是“工农兵学商”,商人也一样在最下面。现在完全颠倒了,它一时引起的失落感是巨大的,你甚至不知道用什么来衡量你的职志。用学理化的话说,其实就是价值迷失、价值冲突的表现。
王晓明:他们的收入到现在还是三千来块,基本没提高。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已经完成,穷人还是穷,但是知识分子却被有效地整合进统治阶层了,当然,是被放在其中一个边缘角落里。
张汝伦:给了钱反而不出东西。想废掉你很简单的,什么都满足你就把你废了,这一招也很厉害啊。事实上,精神性的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的文科是两种,一种极端的技术化,搞材料,搞数据模型,这当然是全球性的现象,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
还有一种就是意识形态化,这不去说它。有一种真诚的人文关怀和孤愤精神的东西今天是不会有人写也不会出了。人文学科看两个东西,一个是课程,现在课程本身就是个问题。第二个,教师自己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原来是计划经济,现在都纳入统一的所谓学术工业中去了,没有什么意义啊。现在申请的国家项目,我有时候也去做评审,都没什么意义啊。因为你现在要做教授,要评什么必须有这个,所以大家拼了命去搞这个,全部废掉了。
现在的学生没有想象力,就是背答案、对答案,我们教师也没有想象力,是因为我们要搞这个东西。也是可怜,无非就是一年多个一二十万,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觉得,你讲的想象力是看不见的,这一二十万是看得见的,我可以买东西了。
现在这样是废得厉害了。所以人文学科已经没有了。比方说我们现在讲一个作家好,也没有什么证据来谈他对人性有很深刻的洞察,对文明有很深的思考,我们只是说他的细节很真实,为了写古代的一个什么东西,他做了大量的考证,看过很多的野史、正史,最后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的。
写这些文学评论的人都忘掉了文学是怎么回事情。文学不一定要真实,文学本身就是一个虚构。问题在于现在人文关怀还有没有?没有。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要你文学干什么?这就跟我们一样,我们搞个项目是拿钱,他写小说也是拿钱,但这些东西搞出来是不是还叫人文,大可怀疑。只不过你这个东西,是从外在给你的分类,你是人文,但实际上是魂没有了。这个是最大的问题。现在各个重点大学的人文学科,从规模上讲都在扩大,然后每个系底下都有无数的中心和研究所,搞什么啊?捞钱。还有就是名片上多个所长、主任,无非是搞这些很无聊的事情。
我一直在讲不要神化原来的民国教授。他们家里有厨子、有花匠,不一定做得出东西来。左右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搞一个话语系谱,各有自己的偶像,但是这些偶像到底怎么样,现在说不清楚。可怜以后的人都去站队,左的人有一堆偶像,右的人有一堆偶像,就苦了中间派。熊十力先生是中间派。钱穆、吕思勉这种人,哪边都不要他,这些人其实学术成就极高。
高瑞泉:吕思勉比较寂寞,1957年就病逝了,留下了大量著述,直到最近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齐《吕思勉文集》十八种二十六卷。不过我估计认真读他的人未必多,知名度还是不高。钱穆不太一样,他后来去了台湾,晚年很受蒋家厚待。在以大陆和台湾划界的人看来,他有些先知的派头,现在也被奉为一尊,不好随便说的,要防止人打破你的头。
张汝伦:这样一来我们再来谈问题就很难,很多东西是越抹越黑。知识分子的职责,在我看来,就是给社会提供不同的看问题的视角。知识分子不要参加制造偶像。实际上陈思和讲的那个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不容易的啊。别人玩的时候你要不玩,你要在那里备课,一章一章要写下来的,不容易的。这个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就是你自己做人,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你就会去做,你觉得不重要的,就去游戏人生。
这和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外在制度,它的一个最可怕的东西,就是把人变掉了。一开始,它是一个癌细胞,但一旦生了这个癌细胞,它就会吞噬你其他好的细胞,人的良知、人的责任心、人一生的追求全变了,包括哪一种学问是值得追求的也变了。
整个人生观变了,最后人变了。资本主义这个机器不像新自由主义鼓吹的那么灵便,未见得每次都能逢凶化吉。但是问题是,它最内在的那个东西,它的那个文化密码很可怕,这个文化密码使得所有反对它的人,实际上是另外的一个牌号的它。
现在回头看,有一点是当时我没有想清楚的,我光是看到文化和人心的剧烈变化,却没有更深一步去理解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
王晓明:接着你的话讲,当时大家担心的那个基本问题:文化和人心的败坏,这些年来是日长夜大。那个时候还有人说:你们太悲观了,杞人忧天。今天不会再有人这么讲了,问题已经这么恐怖地逼到每一个人面前,说得难听点,瞎子也看得到。
今天社会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官员贪腐、征地冲突、医患矛盾、瘦肉精、考题泄露……几乎每一件事,除了派警察去,就没有别的办法。一个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所有文化的、精神的、伦理的保障,似乎统统都垮了。
可是,如果这些都垮了,光派警察有什么用?何况警察也不是火星上来的,那些问题他们都有啊。有些人可能觉得,精神、人心、文化,这些无形之物的败坏的后果,是慢慢显现的,可现在看来不是,至少在中国,后果来得很快,现世报!
现在回头看,有一点是当时我没有想清楚的,我光是看到文化和人心的剧烈变化,却没有更深一步去理解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整个社会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的变化。今天没时间仔细讲这个,就说你们批评的这一套大学里的项目和经费导向的学术制度,这就是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的一环。就目前来看,全世界就是中国大陆搞这一套特别厉害,即便中文世界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也没有搞得这么凶。
在这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方面,今天中国人是颇有“创新”能力的。这一套项目和经费导向的“抓”学术的制度——实际效果基本是败坏学术氛围——的精髓,就是利益交换。它实际是一个订购的交易:我给你钱,你给我货,所以才列出那么详细的课题指南,那么强调实用性,那么赤裸裸地偏向政府急需的各种短期的对策研究。
这个制度不但充满金钱交易的味道,而且也是通过这种交易来重新定义科研基金的性质:它不是社会的公共资金,不是人民的钱,因此不该被用来发展对社会和人类有长远意义的研究,而就是政府的钱。因此,理当用来替政府做研究,就像你从微软公司拿到一笔钱,理当为它做研究一样。
这一套制度对整个学术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学人的影响,真是很大。我们这些人进大学教书的时候,没有这套制度,没有科研基金,但是有冯契、贾植芳、钱谷融他们这些先生在前面领路。他们让我们懂得什么是学术:天下公器、为人类进步……可现在的年轻同行,一进大学,这个订购制度就铺天盖地罩下来,而且都是以学术的名义:课题、奖金、论文、评奖……统统都是学术啊!
你不加入,就当不上副教授,这让年轻人怎么办?十年来,这个制度和其他大学制度(例如日益官本位、官僚化的行政体制)一起,快速而深刻地改变了大学的学术状况,资本的逻辑也由此在大学内迅速膨胀,渗透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
大学都是这样,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何况今天的官员、医生和法官,绝大多数都是读了大学才进官场、医院和法院的。
我有个年轻同事,给学生上文化研究的课,出了个题目:如果真像电影《2012》那样,有一艘船,让你做主,你会选什么人上船?教室里几十个学生,七嘴八舌,好几个回答是:要测试基因,挑选那些基因最优秀的人上船;还有人说,要挑选身强力壮的,体弱的不行。
只有一个同学说,各种各样的人,我都要挑一点。这位同事又问:韩寒该不该上这艘船?多数人说,不行;但也有少数人说,他有资格上船,为什么?因为他是多面手,又会开车又会写文章。同事继续问:你们觉得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上这个船?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为什么不应该?多数人说,没想过为什么不应该,但有一个学生回答:我们现在全部的知识,一个U盘就够了,干嘛还要知识分子?
我不知道这间教室里的讨论在今天的年轻人中间有多大的代表性,但它清楚地呈现了社会的人文危机的多种症状。在机场登机,一般都是VIP先走,经济舱的最后,但有些航班在让VIP先走的时候,也会让妇女和小孩先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等级排序。
如果一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VIP先走,那会是什么样子?再比如知识分子,如果这个称呼不再与反思能力和想象能力联系在一起,而只是与知识的积累相关联,那就真是可以被U盘取代了。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日本人轻蔑“支那人”,都是根据一套所谓优等人和劣等人的区别。
为什么今天还是有一些年轻人,几乎不假思索地就认为,“优秀”的人的生存的正当性,要比其他人更多?这间教室里的这些年轻人,恐怕大多数都不能在社会上挤进“优等人”的行列,但就是他们,却不自觉地接受那一套以强弱定优劣的观念。
因此,问题不在这些年轻人,而在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是如何让他们接受这一套明显是要置他们于苦难的世界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