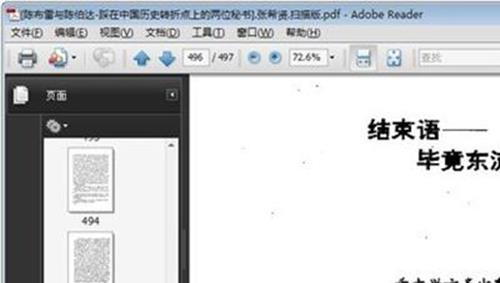王安忆陈映真 王安忆记忆中的陈映真 | 他为死罪少年的新生奔走呼号
1983年,王安忆去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国际写作计划”,陈映真前往接机。王安忆在记录与陈映真交往的《乌托邦诗篇》里这样写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而陈映真也写过王安忆。
1983年在美国爱荷华州聂华苓家。后立者茹志娟,右陈映真,前左二保罗·安格尔(聂华苓的先生,美国著名诗人),前左三陈映真夫人陈丽娜,前右二聂华苓,右一王安忆。
他为死罪少年的新生奔走呼号
文
王安忆
多年之后,有一个外国人,风尘仆仆,掮了一个沉重的背囊,他找到我后,倾囊而出一堆杂志,他的背囊转眼间轻飘无比。这杂志的名字叫做《人间》,总共有十来本。大十六开的版面,印刷精美,纸张优良。外国人说,他是从这个人的岛上来,这个人托他带来这些给我。
《人间》杂志是这个人和他的知识分子同伴们自筹资金创办的杂志,这杂志的名字让我琢磨了许久,《人间》的含义被我一层一层地释剖。这时候,我的困难时期已经安然度过,我情绪平定、内心充实,我有旅行的计划和写作的计划,有条不紊。
我把这堆《人间》放在我的床头,夜晚时分我就翻上一本,怀念的情绪就是在这样的夜晚升起。《人间》里有一个曹族少年汤英伸的故事。曹族是一个山地民族,是那岛上的九族之一。
汤英伸退学去都市闯荡,一夜之间犯下了惊世骇俗的杀人罪。从此后,《人间》就开始了整整一年的救援汤英伸的行动。我看见了这个人在这救援活动中的照片,于是,这场救援便忽然地呈现出生动的场面。这些年的有一个时间里,这个人原来在做这个啊!
我欢欣地想。他风尘仆仆地九死而不悔地,在为一个少年争取一个新生的机会。汤英伸少年英俊无比,聪慧无比,笑容清纯而热忱,这样一个孩子将要偿命,令人心不忍。由于他的母亲车祸受伤,家中经济情况面临困难,于是,他只身一人来到都市谋生。
但是,我还设想,他可能是从流行歌曲里开始了对都市的向往,他觉得那里机会很多,生活丰富多彩。摇滚的节奏总是使人兴奋无比,热血沸腾,对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
因为这时候,我们这里也成了流行歌曲的世界,人们唱着歌,心情就很欢畅。人们在上下班的路上,戴着耳机,让那震耳欲聋的音响,激励我们的身心,驱散日常的疲乏。少数民族通常是能歌善曲的民族,他们没有被大族整肃的文明同化,在偏远的山地,保持了原始人的自然的天性。
日月星辰是他们的伙伴,草木枯荣教给他们生命的课程。他们将他们的经验变成歌曲,一代传给一代。唱歌往往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他们交往的主要方式。
后来,留声机和录音机,多声道的音响传播了摇滚的节奏,机械与电子的作用使得声音具有排山倒海之势,自然之声相形见绌,软弱无力。流行歌曲真是个好东西,它使人忘记现实世界,沉湎在一个假想世界,以未明的快乐与出路来诱惑我们。
我设想汤英伸是戴着walkman的耳机离开山地,去到大都市。我从照片里看汤英伸有一个吉他,挂在墙上,线条异常优美,文章也告诉我,这是一个热爱唱歌的少年。而他没有想到,离开山地就意味着踏上了死亡之地。死亡是怎样来临的呢?
后来,我核算了一下时间,发现大约就在汤英伸少年踏上走向城市的旅途时,我正去往乡间。那是我的困难时期,书桌上的空白稿纸天天逼迫我。乡间总是使人想起规避之地,人走投无路时,就说:“到乡间去。”我与这个少年隔了遥远的海峡,在连接乡村城市的道路上交臂而过。
汤英伸唱着歌儿进城了,他满心都是成功的希望。我去乡间的心情飘摇不定,忽明忽暗。有人告诉我那乡间的关于一个孩子死亡的故事,这故事里有一种奇异的东西,隐隐约约的,呼吸着对我的经验的回忆,受到呼吸的这一种回忆似乎不仅仅是单纯的回忆,还包含有一种新的发现。
我就是为了这一点闪烁不定的东西去了乡间,乡间总是有着许多故事,这些故事带有古典浪漫主义的气息,鼓舞人心。我去追踪的孩子死在前一个夏季,死去的那年他十二岁。
他的家庭非常贫穷,那是在农村责任制分田到户实行之前。在我去的日子,他家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粮食囤,占去住房三分之二的面积。这孩子从小到大,没有照过一张相片,他的形象就渐渐地不可阻挡地淡化。
后来,有一个画家要为他画像,人们就你一言我一语,描绘给那画家听,画家反无从下手了。他还没有留下一件遗物,因为那乡间不仅贫穷还极其愚昧,认为十二岁的死者不宜留下任何东西,留下任何东西将会给其他孩子带来厄运。
人们将他的东西一把火烧光。于是,当人们要对他进行纪念活动的时候,就找不到一件实物,可寄托对他的哀思。他是为了一个老人而死,这老人无亲无故,已到了风烛残年,一场特大的洪水冲垮了他的破旧的草屋。
那乡间是个洪水频发的乡间,关于洪水,那里有许多神奇的传说。长年来,孩子一直陪伴老人,好比一祖一孙。这天夜间,屋顶开始落土,土块越落越大,屋梁塌下了。孩子推开老人,木梁砸在他的腹部。
这间草屋的所有部分都已朽烂,唯有这根木梁,坚硬如故。孩子被送往医院,十五天之后死去。孩子死去仅是故事的引子,正片这时才开了头。在这乡间,有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关于他的生涯他有两句诗可作写照,那就是:“学生为国曾投笔,粪土经年无消息。
”这一回,他将孩子的事迹写成报告,寄到报社,孩子因此而成为一名英雄。那乡间出了一名英雄的消息,顿时传遍了四面八方。许多孩子和大人,步行或者坐车到那乡间去瞻仰孩子的坟墓,孩子的坟墓从小河边迁到村庄的**,竖起了纪念碑。我就是这些孩子和大人中的一个,以我的经验,我敏感到这里面有一个秘密,这秘密在暗中召唤着我。后来,我相信我是有预感的。我预感到事情要有变化了。
现在,我所以要叙述这个故事,是因为在某一个时期里,我和这个人的活动都是围绕着一个孩子: 他是为了那一个孩子的生,我则是为了这孩子的死。这个人距离我是那样遥远,有时候我也想寻找一些或虚或实的东西,作为我与这个人的联系,好使我的怀念的诗篇有一些逻辑的性质。
他在他的刊物《人间》里,开辟了偌大的版面,描述汤英伸少年,使得全社会都注意到一个普通的孩子。孩子杀人虽不算是太平常的事,可却也不算太稀奇。都市里每天都发生许多案件,每个案件都有特别之处。
他和他的知识分子伙伴们大声地疾呼,请你们看看这个孩子!看看这个孩子为什么犯罪!当这个孩子犯罪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大人都已经对他犯了罪!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身置一个法治的社会,他们企望以自然世界的人道法则去裁决这一桩城市的命案。
他们甚至提请人们注意到几百年前,一个大民族对这个少年所属的小族所犯下的罪行,他们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带有浪漫的诗化倾向的事实: 当汤英伸少年向那雇主的一家行凶的时候,其实是在向几百年不公平的待遇复仇。
他们向这个严厉的法制社会讲情,说:“请先把我们都绑起来,再枪毙他。”他们还要这个法制社会注意到天国里的声音:“凡祂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丢失,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
”这个人的身影活跃在这些激越而温存的话语里,使我觉得无比亲切。亲切的心情是他时常给予的,“亲切”二字似乎太平凡且太平淡了,然而,千真万确就是亲切。有一张照片,是在汤英伸的死刑执行初步暂缓以后,律师、神父、汤英伸的父亲,以及这个人,正密切讨论下一步的法律行动。
他正面站着,以他**惯的双手撑着后腰的姿态。这时候,前途叵知,生死未卜。律师是他们中间唯一能够将所有人的理想、情感、愿望赋予行动的人。他们所有人都殷切地、热烈地期望于他。这个人在他们中间,使我感到多么的亲切啊!交通和印刷业真是个好东西,外国人也是个好东西,他是自由的信使,为分离的人们传递消息,使怀念由此诞生。
让我把那两个孩子的故事说完,汤英伸在城市里的遭遇很不顺利,他没有遇到好人,他遇到的人都黑了心肠,那个职业介绍所首当其冲。他们压榨这个初到城市的山地少年,欺他年少、单纯、人生地不熟。他们在一夜之间,就将这少年欺压得怒火中烧,焦灼不安,杀人的事情就是在黎明时分发生的。
争执是从很小一件事开始的,似乎是汤英伸要离开他的雇主,而雇主由于已经付了佣工介绍所许多钱,不肯吃这个亏,要扣下汤英伸的行李。这是一个导火线式的事件,汤英伸在一昼夜里积压的怒气如火山一样爆发了。
他变得力大无穷,不计后果,他一口气杀了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他不杀人不足以解气,太阳这时候才升起。他丢下手里的凶器,大约还拍了拍手,好像刚干完一件清扫的劳动。
他肯定会有片刻觉得无比的轻松,害怕与懊悔是后来的事情。如前所说,我那个孩子的故事其实发生在他死亡之后。他活着的时候,几乎没有故事,村人们对他记忆淡薄,只是说这孩子禀性宽厚,为人仁义,待那老人亲如儿孙。
在他死后,有关于他与老人神秘的奇缘之说在乡间流传,在孩子死后第三个七天,那老人安然长逝,三七是死者的回眸之时,召唤了老人前去会合。老人和孩子的传说本可以很优美,可是轮回之说却平添一股阴森之气。
后来,孩子成为一名英雄,老人与孩子的关系才有了明亮的色彩,成为一幅尊老爱老、舍身救人的图画。从此,乡间成了英雄的故乡,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村庄有了直通城镇的公路。这孩子以他的生命换来了乡间的繁荣景象。
为孩子树碑立传成为热爱文学的青年们争先恐后的事情,当有人去采写孩子与死亡作斗争的一页时,才发现孩子的创口在当时没有受到负责的治疗。这几个人很想以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好立惊世骇俗之说。可这个念头被悄然制止,这将使一个光辉的学**英雄运动变成了一桩阴暗的社会事件。就这样,这小草般的生命的冥灭,演绎出辉煌的故事,并且越演越烈。
这个人和他的同伴们,为汤英伸奔走呼号,他们甚至活动到使原告撤诉。他们说,世间应当有一种比死刑更好的赎罪方式,要给罪人们新生的机会。在那些日子里,汤英伸的案件妇孺皆知,人人关心。关于案件的判决一拖再拖,给予人们不尽的希望,汤英伸的命运成为了一个悬念,寄托着人们心中最良善的知觉。
诗人们提出“难以言说的宽爱”;教育家提出“不以报复的方式”;政治家提出“人文的进步”;历史家提出“优势民族与弱势民族的平等”;人们说:“可怜可怜孩子,枪下留人!
”这是一幅如何激动人心的场面。由于这个人投身其间,甚至处于领先的位置,使得这场运动与我有了一种奇妙的联系,我与这个从未谋面的少年似乎有了一种类乎休戚与共的情感。而我是在一年之后才得知关于汤英伸的消息,这时候,一切都有了结局,我只能在想象中体验着令人心悬的过程。
这时候,关于我的孩子已有了许多纪念与学**的文章。孩子们吹着队号,唱着队歌来到乡间,过一个庄严的少先队队日。
队日已成为乡间最经常的事件,一听到号角声声,人们便说: 孩子们来了。这孩子的死亡时间把我吸引到了乡间,我已经有了相当的阅历,我的阅历告诉我,这事件中有秘密,这秘密非同寻常,我决心着手调查这秘密,我意识到调查这秘密于我事关重大。
后来的事情证明我颇具先见之明,孩子的死亡事件于我恰成契机,它以一个极典型的事例,唤起了我对我的中国经验的全新认识。我的中国经验在此认识之光的照耀下重新变成有用之物,使我对世界的体验更上了一层楼。
我的经验由于孩子的死亡事件的召唤,从那些淹没了我的、别人的经验中凸现出来,成为前景,别人的经验则成了广阔的背景。我的经验不再是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有了人类性质的呼吁和回应。我就像个旅行中人,最终找回了我的失物,还附带有关部门的赔偿。我的经验走过那一个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的路程,改变了模样,有了质的飞跃。这就是后来使我名声大噪的《小鲍庄》。
选自《乌托邦诗篇》
标题为编者所加
《乌托邦诗篇》
王安忆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乌托邦诗篇》共有三个部分,分别是:乌托邦诗篇、英特纳雄耐尔和陈映真在《人间》。作者王安忆以散文的笔调记录与陈映真先生之间交往的点点滴滴、对现实的思考以及陈映真《人间》办刊史。
“二〇〇一年末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作为台湾代表赴会,我与他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还是对更多的人和事失望,虽然世界已经变得这样,这样的融为一体,切•格瓦拉的行头都进了时尚潮流,风行全球。
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
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回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是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