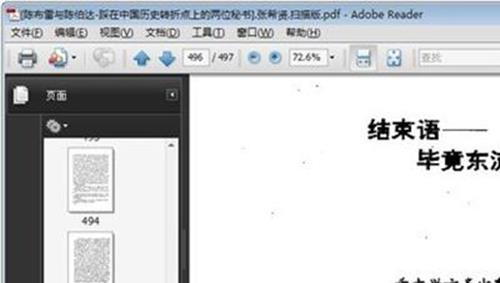王安忆陈映真 王安忆谈陈映真:曾经“我失骄杨君失柳”
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0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
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内容反而印象淡薄。
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
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
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十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的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内容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
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
这些年里,他常来常往,已将门户走熟,可我们却几乎没有见面和交谈。人是不能与自己的偶像太过接近的,于两边都是负担。有时候,通过一些意外的转折的途径,传来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亲离世,接到陈映真先生从台北打来的吊唁电话。
那阵子,我的人像木了,前来安慰的人,一腔宽解的话都被我格外的“冷静”堵了回去,悲哀将我与一切人隔开了。他在电话那端,显然也对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父亲也去世了。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同情。
说起来很无理,可就是这种至深的同情,才能将不可分担的分担。好比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看了我的发言稿,很欣慰,觉着中国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师,终身传布福音;当他被判刑入狱,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试图策动外交力量,营救他出狱,老人婉拒了,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吧!
他的父亲也已经离世,撇下他的儿女,茕茕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