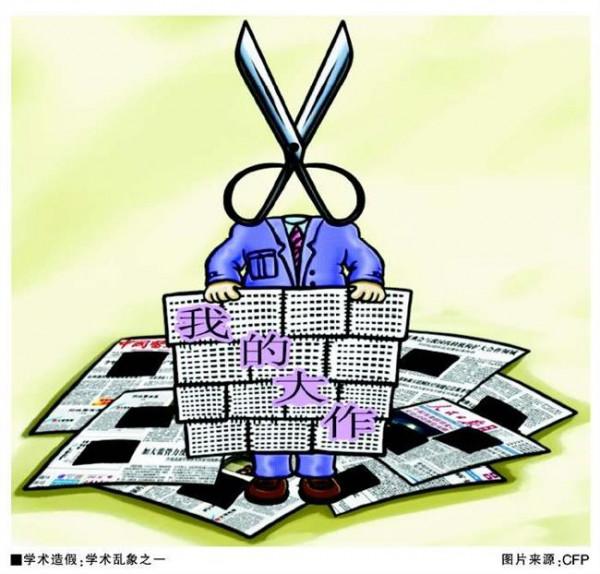章诒和与王蒙 张耀杰:章诒和笔下的真相与人权
2009年4月18日早晨,我从苏州回到北京家中。打开电子邮箱,见到一位老人发来的邮件,其中写道:“章诒和先生《卧底》一文在《南方周末》刊出后,引发了知识界热议,‘告密’成为近期各种场合的热门话题,臧否不一。昨天,‘周末报’发表了林达《继续划定“罪与非罪”的界线》一文,窃以为切中了包括知识界在内的各界、各年龄段人们认识的盲点与误区,是一场及时雨,有醒世之功!前三篇与此事相关;……我要力荐诸位认真一读的则是末篇,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先生今年二月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会上的演说辞:《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将这篇演说辞铭记心中,它将随时提醒我们自问:‘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站在哪一方?!’”
章诒和是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辈同事,逗留苏州期间,我与她围绕《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和《卧底》两篇文章,曾经有过几次片断的交谈,她收集研判第一手文献资料的严谨态度,也一直是我从事历史研究的模范和榜样。鉴于针对她的种种质疑,我觉得有必要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
一、来自王容芬与李大钧的质疑
《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公开发表后,最早站出来加以反驳的,是海外华人王容芬。她在《黄苗子和一代中国文化人的人权》中,摆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以及西方国家的隐私权保护法,一口咬定“章怡和的行为,古今中外都是异数,毒舌八卦,无法无天”。
稍有公民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人权保障,是以不侵犯伤害别人的正当人权为刚性边界的,现代法律从来不会保障任何个人及组织侵犯别人正当人权的权利。据章诒和老师告知,黄苗子当年在苦心抄录毛泽东全部诗词以表白忠心的同时,确实为公安机关诠释过他所提供的一部分聂绀弩诗文,从而“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必要的时候,她会以合适的方式把相关证据拿出来进行对质的。
在我看来,96岁的黄苗子重病住在医院里,并不是他免受历史叙述的据实记录的正当理由。同样的道理,陈水扁是直接促成台湾民主化的历史人物,他的妻子吴淑珍为了支持陈水扁的民主事业牺牲了双腿。台湾方面的司法当局并没有因为陈水扁的贡献和吴淑珍的病残而法外豁免他们的贪渎嫌疑。王容芬以“被章怡和诬为告密小人的黄苗子是一个非常爱惜羽毛的人,交游遍天下,一生无丑闻”的道德理由替黄苗子开脱,假如不是出于她自己的无知,就应该是别有用心。
正在编写《黄苗子年表》的艺术推广人、百雅轩文化艺术机构负责人李大钧,显然是黄苗子的利益相关人。他不避嫌疑发表在2009年4月16日《南方周末》的《质疑章诒和》一文,恰恰为世人提供了黄苗子甘心情愿充当密探的历史证据:“皖南事变时,在国民党系统内担任职务的黄苗子看到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文件,就通知周恩来同志。毛泽东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使国民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他曾多次巧妙地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掩护帮助了王昆仑等一些共产党人。”
黄苗子既然在中共掌握政权以前就可以秘密出卖自己担任职务的国民党政府,等到中共掌握政权之后,他或主动或被动地秘密出卖被新政权视为敌人的聂绀弩,也就不难理解了。急于替黄苗子表功的李大钧,反而因此表白说:“黄苗子一生传奇,阅尽人间沧桑,交友无数,助人无数,一生清楚地行进,在多个历史时期没有迷失,担当了清晰的角色。”
然而,一旦谈到章诒和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李大钧马上就变得又软又滑:“文中,章诒和用老练圆熟的文笔,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你们知道吗?把聂绀弩送进监狱的,不是那个错乱的年代,而是聂绀弩身边的一批朋友,尤其是他的至交黄苗子等人。”
事实上,所谓“错乱的年代”恰恰是由包括“黄苗子等人”在内的错乱人物所直接构成的,而不是由人类之外的上帝以及其他非人类的牛鬼蛇神所构成的。在并不十分“错乱”的国民党时期,就已经充当密探的黄苗子,从来就没有担当过“清晰的角色”。
二、王建勋的《听李锐说故事》
在前述邮件中,附有王建勋的一篇《听李锐说故事》,其中叙述的是2009年4月12日中午李锐老人的九二华诞:“李锐的夫人张玉珍秉持锐老在这类事上一贯的简朴、低调作风,假北京三里河附近的新九龙酒家,请来两桌客人小酌共庆。来客中大都是李锐的家人,只有几个外人,司机和媬姆也是座上客。”
作为“几个外人”中的一个,王建勋与“司机和媬姆”之类的“内人”一起,聆听了李锐老人的说故事:
“边吃边聊的随意漫谈,逐渐集中到近一两个月来,由李辉与章怡和发动的给一些文化老人‘脱裤子’上来。李锐对我说,你替我转告章怡和,要算历史大账。我在延安被‘抢救’时,关在保安处,5天5夜连续审问,不让睡觉,他们则轮番上阵。
一位王×在审我时还冲过来打我的耳光,1948年在东北再见到他时,我只字不提他打我的事。还有一位×××,住我楼上,大我两岁,在保安处也审过我,他后来被打成右派,也被发配到黑龙江。一天,他和另一人来看我,正好我大姐刚寄来一盒饼干,我请他俩一起吃。
1959年从庐山下来,回到水电部接受批判。为了整我,部机关党委编了本《李锐反党集团反革命言论集》,1960年内部印出,里面从刘澜波以下,多少人揭发、批判我。
过了20年,我复职后才看到这个《言论集》,对他们当年的落井下石我还是一句不提,否则,怎么一起工作呢?要算账的话,应该算毛泽东的,还有邓小平,小拨拉子,你揪住他干吗?后来我到组织部,邓颖超提出清理文件,烧毁了一批。
有一次我经手处理,看到待烧的文件中有‘两案’(指刘少奇和林彪——笔者注)的一个档案,周恩来管‘两案’,他的批语可比江青的严厉多了。这个账,怎么算?冤冤相报何时了!李锐在讲这番话时,语气平和,面容平静,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与已不相干。”
读了所谓“语气平和,面容平静”的李锐说故事,我所感受到的只有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描绘过的礼教吃人的阴森恐怖。在李锐老人“存天理,灭人欲”式的“历史大账”中,“小拨拉子”的黄苗子、冯亦代们,是没有必要被追究的。
周恩来配合毛泽东害死党内同志刘少奇和林彪的历史档案,也是可以亲手予以烧毁的。像章诒和那样被冯亦代卧底所摧毁的心理平衡和人格尊严,也是无足轻重、不足挂齿的。像我的爷爷张天霖和我的大爷爷张木霖那样的3600万中国农民,于1959年前后被毛泽东、周**、刘少奇、林彪、邓**、李锐、王建勋们所加入的执政党活活饿死的“历史小账”,由于仿佛是“别人的事”,也是可以用一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道德高调全盘抹杀的。
连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呐喊出的中国传统神道信仰中仅有的一点“人命关天关地”的人性火花,在依赖巨额公款医疗而“争取活到九十五”的李锐老人心目,也是要被彻底“唯物”或彻底“党性”的。自以为掌握着“历史大账”并且养尊处优的李锐老人,尽可以躲藏在“历史大账”的旗帜下安享后福。
好在我并不是太过健忘,就在不久前的2008年,王建勋偏偏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坐实了于浩成老人的告密嫌疑。在更为切近的所谓《零九上书》中,正是自称“党内民主派”的李锐老人以及他的朋友们,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民主授权程序,就擅自盗用公共名义把全国人民的灵魂一起出卖给了他们所要效忠的最高当权者:“我们老干部和你们在一起!全国人民和你们在一起!”
所谓《零九上书》的如此表现,正如90年前自以为“民主”与“科学”却偏偏盗用北京市民的名义走上街头散发所谓《北京市民宣言》的安徽人陈独秀一样,所彰显的其实是李锐老人以及他的朋友们只反对别人专制而不反省自己身上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和专制习性的自欺欺人,以至于“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明确选择了站在掌握最高权力的专制者那一边。
换言之,作为一名自我健全、严格自律的现代公民,笔者既尊重一切个人反对专制的道义勇气,更尊重反对专制的个人对于自己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和专制习性的反省清算。自称“党内民主派”的李锐老人以及他的朋友们,至少在对于自己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和专制习性的反省清算方面,是完全不及格的。
三、戴晴的《高法书记李玉臻》
比起中共的编外密探黄苗子和业余卧底冯亦代来说,前《光明日报》社记者戴晴才是真正有特殊背景的异议作家。明白了她的真实身份,由她署名的《高法书记李玉臻》一文的政治控诉,也就不难理解了。
据戴晴在《高法书记李玉臻》一文中介绍,诗人、纪实作家寓真,本名李玉臻,山西人。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先是分配在老远的海南当警察,文革后期调回本省,八十年代初从地区中法院长、地区政法委书记做起,到八十年代中已升任省政法委副书记。
1988年开始担任山西省高级法院长兼党组书记(以及历届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在这个位置上一坐20年,直至2007年年满65岁之际,“辞去”政府职务,成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至今。
到山西煤矿打工的河南农民“杀人犯”郝金安案发生于1998年,“当时李玉臻担任山西高法(具有死刑核准权力)院长兼党组书记已有十年。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屈打成招的郝金安在狱中从未停止向山西省各级司法机关申诉。
每月8元的津贴,大部分用来买邮票寄申诉信。可是……怎么封封石沉海底?那囚人还以为邮票贴得不够,就在信封上多贴几张。五年后(2003),郝金安获允与家人通信。一手抚养他成人的姐姐这才得知弟弟关在山西。此后,郝金安在狱内申诉,姐姐、姐夫在狱外奔走……这些,正在位且具有‘一览无余的敏达’的李书记全然不知么?”
但是,同样的疑问也可以套用在戴晴本人身上:郝金安案发生于1998年,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你戴晴从来没有关心过,为什么偏偏要等到“十万字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铿锵登场”之后才挺身而出呢?进一步说,李玉臻即使对于相关的冤假错案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也并不影响《聂绀弩刑事档案》的正面价值和李玉臻本人对历史事实负责的高尚追求。正如李锐老人以及他的朋友们以“党内民主派”自居,无论如何也比他们一厢情愿表忠心的最高专制者要难能可贵。
在笔者看来,林达的《继续划定“罪与非罪”的界线》一文只是讲明了一部分的道理。而另一部分更加重要的道理,是由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讲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在清算历史旧账的时候,像李锐老人那样只算“历史大账”,或者像那样林达轻描淡写地放过“创造了体制”的第一责任者即“我们”而凭空呐喊“法治社会的建立,对犯罪的明确界限,铲除告密者生长的土壤”,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上,和那个时代切割清楚”的。
没有真相就没有人权,更不可能逐步创造和建设出足以保障每一个人的正当人权的现代化普世性的宪政民主制度!在本国公民没有权力自由查阅本国政权的公共档案的特色社会里,在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自由思想者迄今为止依然屡屡遭受告密诬陷的恐怖年代里,章诒和呕心沥血还原历史真相的不懈努力,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瑕疵与盲点,其促进人权保障的正面价值却是不可替代更不容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