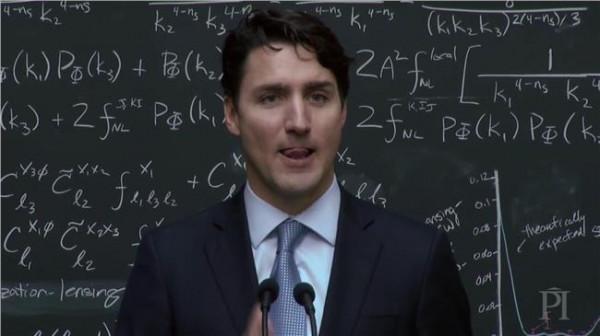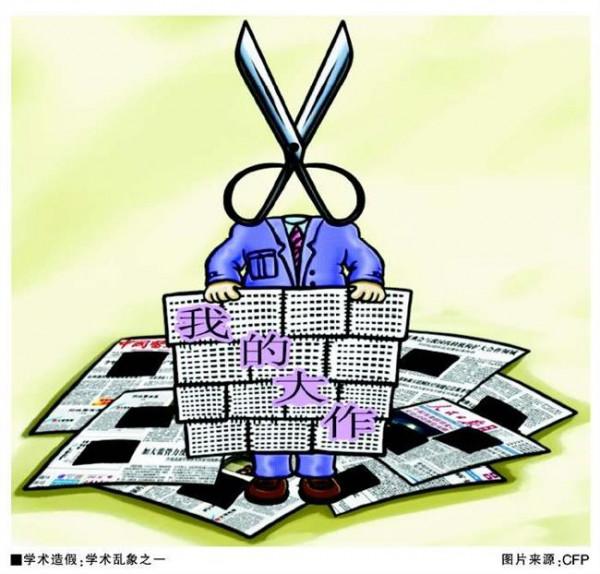于建嵘底层立场 张耀杰:《抗争性政治》于建嵘的底层立场
于建嵘教授的《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已经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定价32元。本文虽然是评论于建嵘教授另一部书稿的,其中的核心价值与基本立场,还是以一贯之的。特以此文庆贺于建嵘教授的新书出版。张耀杰2010年9月14日于南下之前。
不久前,一家著名刊物的女主编问我说:“你和于建嵘完全是不一样的人,为什么你们两个人总是在一起?”我想了想回答说:“你的意思应该是我这个人太书呆子气,说话太直容易得罪人。于建嵘下海当过律师,身上既有书卷气又有江湖气,比较善于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不过,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于建嵘和我在根本理念上是一致的:我们都坚持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这也是我们两个人多年合作的基本点。”
在《底层立场》这本书里面,于建嵘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民心工程也不能违法占地》,其中所表达的正是我们两个人一直坚守的底层立场:“长期以来,我们都在奉行着为多数人谋福利可以牺牲少数人合法利益的观念,美名为‘舍小家为大家’。
因此,为了城市的美化,可以强毁某些人的合法家园;为了城市扩张,可以强征农民的土地。凡此种种,地方政府和官员都是那样理直气壮,一点负罪感甚至不妥感都没有。在笔者看来,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只要是合法权益,就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只能是公平自愿的交换。一个和谐的社会,是绝对没有以剥夺部分人哪怕是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民心工程’的。大量事实表明,此类事件,并不总是那么真的‘公益’或‘民心’,即便没有经济利益考虑,也有政绩利益在内。”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有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或者说是在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筑起一道足以保障个体人权的刚性的制度规则和法律程序;于是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很随便地把西方社会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转换成为中国特色的个人独裁及群众专制。
1919年6月11日晚上,在《新青年》杂志中极力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安徽籍北大教授陈独秀,并没有征求包括北大师生在内的北京市民的意见,就擅自代表北京市民的公共名义,到公共娱乐场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要求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的官职并驱逐出京;要求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要求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来自行组织。
这样的政治表态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检、法的打、砸、抢、烧一样,在精神上是与中国本土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一脉相承的。
1949年之后通过土地改革逐步实施的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始公有制的近代化演变。所谓的“农民集体”并不是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法人组织”,而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不能具体行使对土地有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
因为它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没有解决“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
说得更加通俗一点,就是所谓的“农民集体”,从来没有把作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与资源的土地所有权,通过股份制及股权证的形式充分量化到每一个农民的名下,并且由每一个农民自主经营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或者通过民主参与来合理分享原本属于自己的一份收益。
举一个于建嵘曾经使用过的经典例证,在没有明确土地产权的情况下发生土地交易,同一个村子中的十户人家只要有九户举手同意,就可以通过所谓集体表决的民主程序,以“农民集体”或者是“民心工程”的公共名义,把另外一户人家的土地和宅基地公然出卖,而无视这户人家的正当权利和生死存亡。
假如这一户人家不接受、不服从九户人家的意见,就会被定性为少数坏分子钉子户的破坏活动。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就是这样做的,强迫农村把土地充公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也是这样做的。
目前的大拆大建大变样的所谓“新农村建设”的土地流转,在一部分地区同样是这么做的。但是,现代文明国家的人权保障,偏偏是而且也只能是从保障极少数人自利自利的个体人权和私有产权起步的,或者说是从保障少数坏分子钉子户的合法人权起步的。英国历史上的著名典故“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千军万马不能进”的磨坊主人,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钉子户。
我本人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底层人,我的爷爷张天霖和大爷爷张天霖,都是在1959年麦收季节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的。于建嵘虽然出生于根红苗正的革命家庭,无常的命运极其残酷地把他的全家推入了比农民还要底层的贱民行列:1966年“文革”开始时,于建嵘刚刚4岁。
他的父亲,革命年代的游击队员,革命胜利后的湖南省祁东国营酿酒厂的负责人,转眼之间被造反派“打倒在地”。母亲和4个儿女一次次从县城被驱逐下放到偏僻农村,颠沛流离中丢失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户籍档案。
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一家人沦落为寄生于城乡结合部的黑人黑户,母亲只好靠着到粮站拉板车和捡碎米来供养处于发育期的4个儿女。“吃垃圾米”是于建嵘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
7岁时,父亲托关系把于建嵘送到城乡结合部的一所乡村小学读书。母亲专门从粮站捡来麻袋布,染成黑色后请一位盲人裁缝做成上衣,结果两个口袋一个缝在里面,一个缝在外面。这是他记忆中的第一件新衣,却被同龄的农村同学以驱逐黑人为借口在教室里强行撕烂。
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1978年,于建嵘的父亲刚刚平反4个月就因病去世,他的母亲因此丧失了恢复工作的机会。未成年的姐姐带着他四处上访却到处碰壁,坚强不屈的母亲从此靠着捡拾破烂来养家糊口。1979年,17岁的于建嵘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童年时代的底层经历,已经初步奠定了他时时处处为底层弱势者着想的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
在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于建嵘表白说,自己坚持不懈地到“岳村”即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调查研究,“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真切理解绍庄村的乡亲们“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劳动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我对自己生命的承诺”。
正是基于这种根源于底层立场的生命承诺,于建嵘早在1984年就在《衡阳日报》记者的工作岗位上,独立起草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一个新闻和法律工作者的建议》。近年来他更是在不停的行走和不断的笔耕中,奋力完成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底层政治:对话和演讲》等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的底层研究和社会危机的应对治理方面,树立起一个又一个学术上的里程碑:在《岳村政治》中,他率先提出了重建农民协会的重大议题。
在《安源实录》中,他重新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进行了定性。2004年8月,他适时发表了《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关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形势的一项专题调研》的课题报告。
在信访部门借助于《信访条例》的修订要求扩大部门职权的大背景下,他基于自己的社会调查和底层研究,不顾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公开提出了逐步以制度框架和法律程序替代人治信访的政策建议。
为了解释日益频繁的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他独创了“社会泄愤事件”的学术概念。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他又在《剥夺穷人生存权就会同归于尽》等一系列文章中,大声疾呼保障农民工和城市失业者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利。
于建嵘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前沿地带游刃有余,还得益于他与底层立场相关联的底层心态、底层智慧及底层边界。在私人交往中,他反复强调的是自设边界并且正大光明的两句话:“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里面,第一不要把自己当人物;第二不要认为自己有别人特别是国家机器所不知道的小秘密和小动作。”
在我看来,可以把于建嵘的底层立场和底层研究归结为一句话,就是用谦卑敬畏的低姿态正大光明地从事自己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的真问题和真学术,而不是像他所批评的一些学者那样,动不动就采用“社会敌意事件”之类的高调概念危言耸听地误导社会舆论。
具体点说,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最需要的是依法限制公共权力并且依法保障个体人权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而不是所谓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服从于多数人的利益的道德高调与权利陷阱。
相比于公共领域里的民主参政、民主选举的政治权力,以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为核心本位的以人为本的私人权利,更加需要包括民间组织、民主选举、司法独立、权力制衡在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刚性制度框架的强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