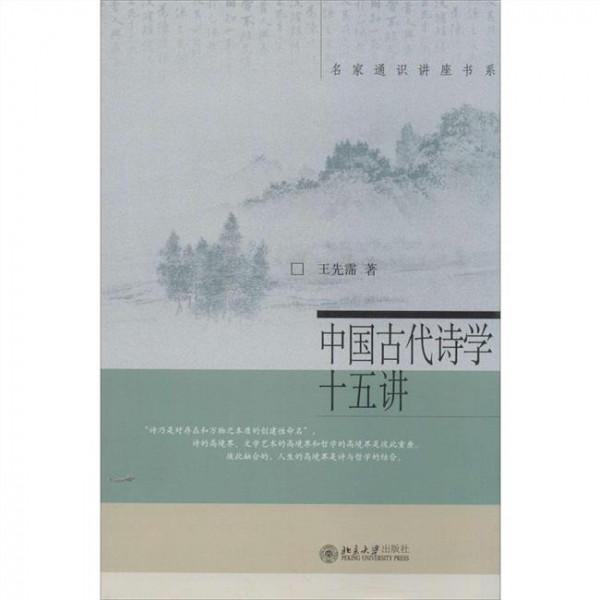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学史游国恩 洪子诚:当代文学史须对当代文学“保持距离”
提起治当代文学史,“北洪(洪子诚)南陈(陈思和)”闻名学界。借着一本新书《文学的阅读》的问世,记者拜访了作者洪子诚教授。
这是一本近似“口袋书”的小开本,看着很亲切。书中,作者对自身阅读动机和环境以及方法进行了反思,其中既有对巴金、金克木、契科夫、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的阅读史记录,也有对北岛、牛汉、张枣等人的新诗阅读体会,还有“与音乐相遇”的经历。
不同于他严谨克制的史论文字和概念辨析,新书里的文字流露了更多的个人阅读好恶,秉持的是“任何未经感觉的认识对我都是无用的”理念。他坦言比较喜欢严肃文学,武侠、言情、侦探之类的,“不知怎么总是进入不了”。
史论和阅读体会文字相同之处是他思维的缜密。文如其人,坐在对面的洪先生面色温润,头发花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出生的他谈吐带有家乡广东潮州口音。
几乎和自己研究的对象同生同长,洪先生认为对于做研究“利弊共生”。文弱书生经历了历次运动,难以想象,翻地、炼钢、看锅炉、开拖拉机(他笑称两次开进水渠里)这些事情和他有关。对于他来说更难以名状的,恐怕是在特殊年代里言不由衷的说辞。难能可贵的是,在他后来为“当代文学”修史时,能将亲身经历过的那段时和事“做出一种知识性、学术性的处理,而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
洪先生讲课没有高谈阔论,总是那么不疾不徐。他甚至说,“因为天性怯懦,虽然讲课已有40年的‘历史’,但只要一站到讲台上,依然还是战战兢兢,没有信心。”北大戴锦华教授却另有一番观察:“洪先生常会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
这种坚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尤其可贵。”正是这种“坚硬”,促使他“以一己之力在北大开创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一种基本文学研究方法”。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大上学的洪先生师从游国恩、王力、林庚、吴组缃、杨晦、王瑶等名家。后来留校的他似乎在继承一个“传统”,那就是上课极慢。杨晦先生讲文艺理论,讲“九鼎”,一个学期下来还没讲完。而洪先生准备讲“当代文学的发生及其形态特征”,学期结束,发现头一个问题也还没有讲完。
接触过洪先生的人都为他近乎“自我贬抑”的坦诚而惊讶,洪先生在不同场合总是透露出自身以及自己学问的“不完美”,可正是这些坦诚反而愈见其高。比如他留校北大,不说自己优秀的原因,却说是当时条件下出去的才是“专业对口”;被问及如何评价自己和陈思和教授的当代文学史,他毫不犹豫说“己不如人”,并罗列陈教授的研究对他的启发种种;有论者赞扬他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带有历史品格的‘深度批评’,是试图建立文学史当代性与历史性的关联”,他却说“当时更多的是无奈”。
他还说自己做文学史研究是因为文学批评做得不好。他经常跟学生讲,“我的想象力比较差,做的梦都是很现实主义的,非常有条理,从来没有做过上天入地的梦。”
洪先生有真正学者才有的独立自省精神,那个年代特有的“两点论”对他也有很深的影响。他曾在一篇回忆文字里写道:就对待前辈学人(包括我们老师)的那种粗暴态度,不容置疑的大批判方式,回想起来也是应该汗颜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
以先验的观念去粗暴剪裁、肢解材料的这种做法,在我这里便印象深刻。后来身处八九十年代创新热潮,虽然为新的理论、方法的到来兴奋不已,却也抱有警惕之心,防备着对它们的迷信,就像50年代“以论带史”那样。
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尺度:概念、抽象是对现象的丰富,抑或是对历史的窄化——这可以说是因得病而获得的免疫力吧。值得怀念的另一点是,大学5年,我们的生活与社会并非完全隔绝,不是生活在封闭的象牙塔中。这一点是今天难以复现的。
确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遇。洪先生说,对别一代的辉煌、幸福其实无须羡慕,自己的哪怕是难堪的日子也不必后悔。他从沈从文的这句话中找到了共鸣:毫无顾虑地来接受挫折,不用作得失考虑,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
■访谈录
写当代史要有一定公正性和共识性
记者:史书中涉及的作品,研究者是否需要全部通览。
洪子诚:大部分吧,一小部分也参考别的介绍,因为一些作家作品量很大,或者有一些作家的作品也不太重要,就会借助一些作品的评论。
记者:这本新书中,您曾谈到几次阅读巴金的不同体验,人生不同阶段对一部作品的理解存在差别,那么如何保持教材中对某部作品评价的客观性和恒久性。
洪子诚:应该还是有一些共识,虽然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感受不一定会是颠倒的,观点会有一定延续性,不同时期的观点会有一些差异。
记者:有没有对一些作品的理解变化比较大。
洪子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作品的理解和八九十年代就不一样,我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有讲过沈从文,也不知道张爱玲、钱钟书,当时认为是反动作家,而是比较推崇革命文学,比如郭沫若的早期作品,但是这些作品的评价后期也有一定下降。另外,包括徐志摩、戴望舒的作品,当时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这个变化和时代的变化、对经典的认定有很大的关系。
记者:除了五六十年代,还有哪些作品在您心中后期和前期的感悟不一样。
洪子诚:修正的有,但是完全推翻观点的没有,比如刘心武,现在大家可能谈论的少,但是当时讨论很火热,从作品和作家本身来说不会放在非常高的位置,但文学史里要讨论,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觉着读不下去,当时什么背景塑造了这种作品。
记者:您是如何平衡个人阅读的爱好和史学家的客观。
洪子诚:阅读当然完全是个人的感受,既喜欢但是又能谈出来东西的才会放在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比如巴金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但是他的作品很重要,有历史在里面,但是写当代史的时候不能有个人观,还是要有一定公正性和共识性。
我写的作家基本上都是比较重要的作家,但是可能在具体评价上和别的文学史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些重要作家我也没有谈到。对文学评价的观点,我认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流派,评价标准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比如美国学者夏志清,他对赵树理的评价就非常低,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因为他把西方文学当作评价标准,从中国文学角度看观点就会产生差异,包括意识形态也会影响评价。但是我相信人们对文学的理解还是存在共性,所有的人都在讨论,但还是会有一些指标,比如它的创新性,语言的深度和形象性,你不能说标准是恒定的,但却是在用这些标准。
记者:刚才您提到夏志清教授,能否再作些评价。
洪子诚:他的书还不错,很多东西有深度,但是他以西方文学为标准,而且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有一个时代背景,当时美国付出大量资金了解中国,对革命文学,像鲁迅的作品评价不是很高,但是鲁迅毕竟重要,所以他也写了。他毕竟读了很多文学,分析的方法还是值得借鉴。
当代文学一个问题在于它在什么时间截止
记者:看来,文学和文学史都需要经受历史的考验。
洪子诚:当时只是想为大学出一本教材,全国文学史教材很多,我的文学史不一样的地方是采用历史观的方法,希望把文学作品的出现和体制的问题放在一个历史情景里解说,主要讨论这个概念为什么出现,文学形式产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通俗小说在民国时期兴盛当代却衰落,为什么题材会发生转移,所以如果读者没有一定背景知识,理解上就会有一些困难。
记者:您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后有哪些修订变化。
洪子诚:有一些资料性的问题,比如作品发表的刊物、年代,所以不断在充盈的过程中有修正,1999年开始总印数有70多万了,学校采用这本书当教材的有点多,最近几年略少。大家普遍的观点是我的教材对本科生来说稍微深了一点,不是很好理解,很多研究生都在使用,现在教材也出了英文版、日文版和欧洲版。
记者:对当代文学的划分和界定历来观点不一。
洪子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不开的,但是学术上可以进行界定,当代文学一个问题在于它在什么时间截止,这个词用了70多年,是不是要进行一些变化,但问题的困难是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划分由教育部确立,当代文学是一个二级学科,这是一个制度,你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学术上可以有不同的处理。
我的看法不一定是通俗性的看法,所以有的学者把台湾香港放在里面,有的学者把延安文学放在里面,提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看法也不太容易,包括中国新文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也存在争议。
记者:当代文学研究最想解决什么问题。
洪子诚:清理当代文学发展历史,有哪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或者说存在什么问题,比如说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差异,主要是当代文学的风格不同,毛泽东建立的人民文学,延续了革命文学的传统,但是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计划和理想后来发生什么问题、矛盾,取得什么成就,这些讨论还在持续。
贴得太近,情绪和评价会比较激进
记者:当代文学离我们太近,如何做到“切近的客观”?
洪子诚: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贴得太近,情绪和评价会比较激进,保持距离也不是很容易,总的来说要把作品放在一个研究对象的位置上,要凭借个人修养对作品进行观察,很多作品没经历时间的检验,不见得这个作品对当代很重要,对下一个时代还依旧重要,比如唐朝“当代”的唐诗选和后人编写的就有很大差别。
但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一个优点,就是对事情的了解比较细致,后人难以了解,所以也不是没有价值,当代人研究的当代文学史可能会在后来减少一些东西,但也会留下一些,学术在于一个积累的过程,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得到大家都认可的结论。
记者:《文学的阅读》非常个性化,您觉得阅读史和文学史的区别是什么?
洪子诚:阅读史解决的是印刷方式、书桌变迁、环境是怎么影响人们的阅读,像战国时代书刻在竹简上,书怎么收藏,谁有权利阅读,阅读史研究的就是条件变化对阅读本身的影响。我的阅读史写的是我阅读中的体验和收获,和文学史不同,主要是我自己的体会。
记者:对您影响比较大的著作有哪些?
洪子诚:《聊斋志异》语言的简洁、形象化,还有《红楼梦》,都有影响,诗歌对我的影响表现在意境方面,外国文学读俄国的比较多。
记者:阅读中有这种现象,某部作品蕴含的意义可能就在那里,有的读者能体会到有的体会不到,但我们也常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您觉得文学价值评价是否存在恒定的标准。
洪子诚:不是说一个时代就一个标准,或者一个阶段就有一定标准,但人类仍然存在一些共识性的东西。比如作品被公众阅读是一个标准,但有的经典作品不一定被广泛阅读,包括欧洲的一些作品,大众不会去读,但作品的地位还是很高。
像但丁的《神曲》,北大图书馆之前有一个记录,学生借第一部的人多,第二部的人减少,第三部就干脆没什么人借了,可这也并不影响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好作品的标准还是有的,比如艺术的创新性,在艺术史上产生的影响,还有写作手法上、对人的心理的开掘程度上,当然,这也不是衡量所有作品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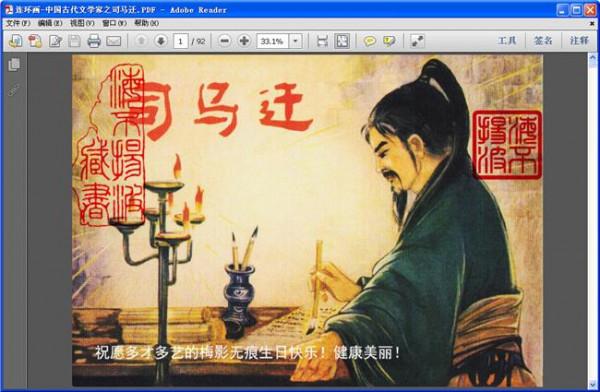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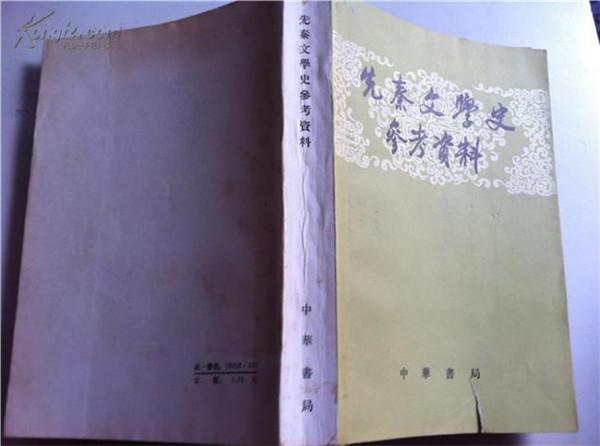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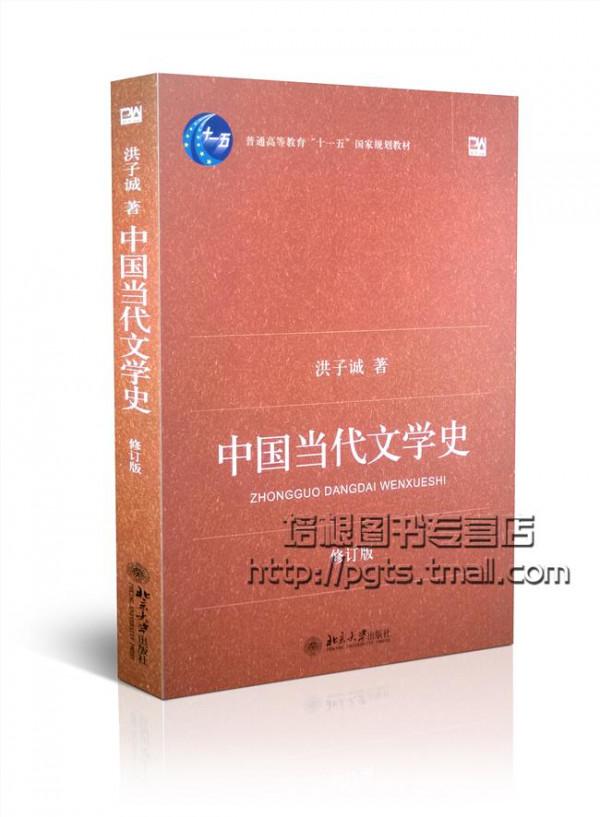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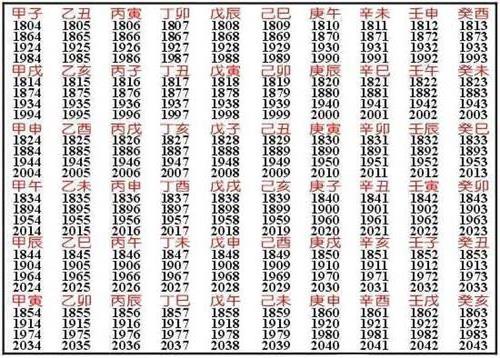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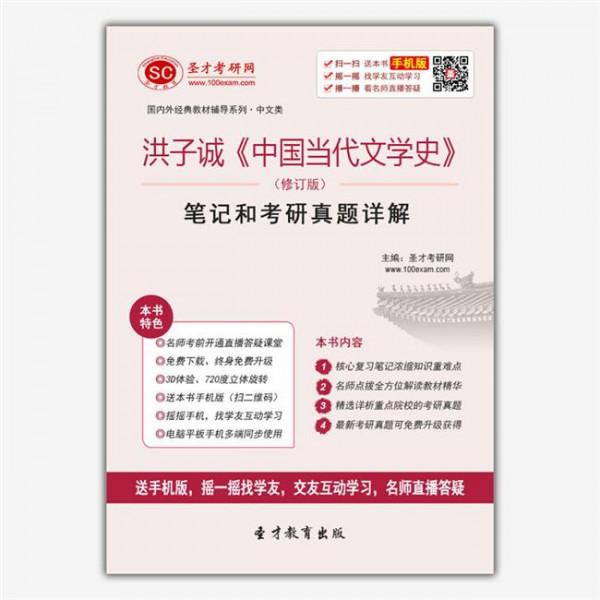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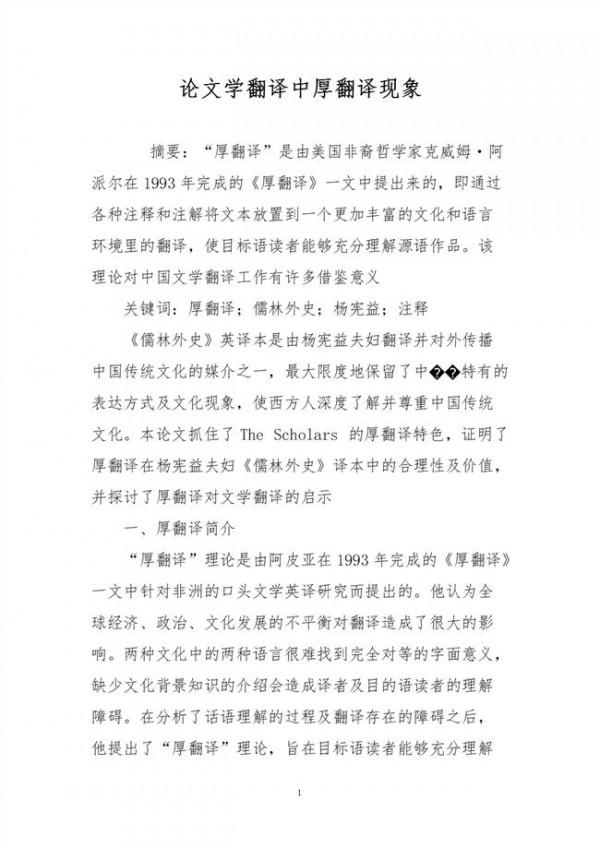

![>[原创]我为什么不喜欢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https://pic.bilezu.com/upload/7/79/7791938d725525f0fa86d29349b9c050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