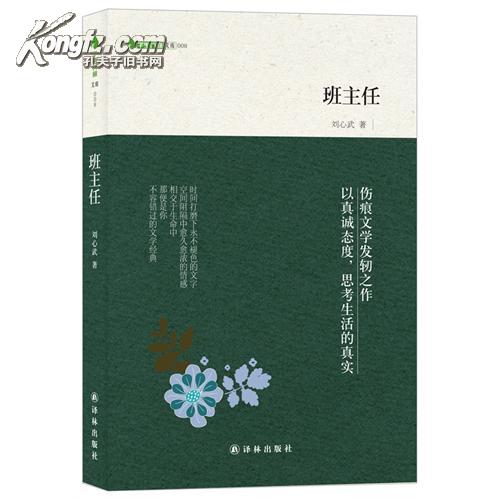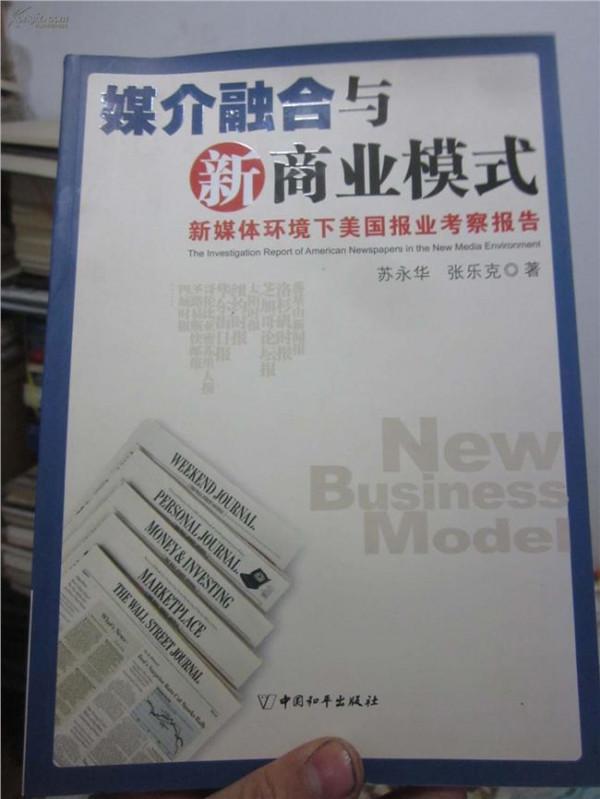刘心武的班主任 刘心武《班主任》真实阿张在《苦途》 回忆半个世纪前的骑行
近四十年前,“文革”刚刚结束之时,还没有成为著名作家的刘心武写了一篇小说《班主任》。小说讲了一个中学教师张俊石挽救被“文革”扭曲了心灵的学生的朴实故事,引发人们对十年动乱的深刻反思,因此被推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刘心武当时正在北京市十三中当语文老师,他在《班主任》中所描写的张俊石老师,乃是借用了和他共处一间办公室共享一张桌子的同事张金俊老师的名字。刘心武曾亲口告诉张金俊老师说:“他叫张俊石,你叫张金俊,金和石不分的。”后来,刘心武调离十三中,还时不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主人公叫“阿张”——那是他每次肚子饿了,倚在张金俊老师身上求他买东西吃时,对张老师的“爱称”。
张老师还珍藏了许多刘心武的趣事。“刘心武这个人聪明、灵巧、干练,剪报一剪就一大本。写东西也快,把蘸水钢笔用剪刀剪平了,刷刷地写。”他透露说,刘心武还老有些“坏招”,比如教他们上火车把毛巾蘸湿了敷在头上,嘴里连喊“哎呦、哎呦”,就会有乘务员过来掺到有桌椅的地方去。
“《班主任》人物原型”的称号足以令一个人出名,但张老师知道刘心武向来“顽皮”,对此从没有太放在心上。二十多年过去了,刘心武成了“大人物”,张老师也只给几个熟人提过这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班主任,人家写的不是你,你担当主角,给人说你怎么教育了学生,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他宁愿把那篇小说视为纯虚构的产物。
不过,2008年开始,退休十来年的张老师也开始像他的前同事那样,执起了写作之笔。他开了一个“张金俊的博客”,把自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大串联”时期从北京骑行到南方的壮举记录下来。他不会打字,就用汉王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再弄到电脑上。
这束题为“苦途”的老式回忆放到网上,竟引来无数经历或未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访客,他们看了之后意犹未尽,还总是“催更”。张老师一高兴,在学生的帮助下,干脆出了本书,名字还叫《苦途》。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上海……八个省、十几个城市、上百个村落,这在今天看来都是一段不那么容易的旅程,很难想象张金俊老师和他的三位伙伴骑着破破烂烂的自行车,只用了十三四天。
“最慢一天骑几十华里,最快一天能骑三四百华里。”从南方回来,修车师傅检视着他的破车,惊讶地问,你的轴碗呢?不光轴碗磨秃了,滚珠也掉光了,他就那么骑着一辆普普通通的永久牌自行车,在那个红彤彤的革命背景下,从北向南,见证了一个特殊时代中的祖国。
决定骑行,是缘于心中的“苦闷”。“文革”开始后,不少张老师身边的朋友、同事被排挤、甚至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张老师是个尊重知识、学问的人,和这些有问题的人走得近,没有划清界限,于是也受到一些有头有脸人物的挤兑。“大串联”开始后,青年们意气风发地去“周游列国”、“交流革命经验”了,打小对祖国各地充满向往的张老师也心痒痒,不料“人物”发话,不让他去坐火车。
被喷着革命蒸汽的火车抛下,张老师一怒之下,干脆召集和他同病相怜的伙伴,骑上自行车就出发了。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里,能去“大串联”的青年是幸福的,不仅有免费的交通工具乘坐,还有专门的“串联接待站”管吃管住,人人欢呼雀跃,喜气洋洋。
不过相比起来,张老师可真是“苦途”,不仅要“自行”,还得自备钱和粮票,一路上紧巴巴的,饥一顿饱一顿。到最后,还不得不打电报求爱人寄了一百块钱来,这才回到北京来。张老师的爱人回忆道,当时工资才三十来块钱,一百块钱真称得上“巨款”,但她支持丈夫的“任性”,知道“他本身好这个,喜欢这个,不爱在家呆”。
虽然精神苦、身体苦、经济苦,进个澡堂还得背语录,但和学问渊博的“问题伙伴”抱着团,一路感受风土人情,一路掏空储备,进行“头脑风暴”,分享当地的历史文学文学知识,倒也是难得的收获。在曲阜,他们不顾孔子被打倒的现实,专程去探访孔庙;在杭州,他们“文青”了一把,剑走偏锋地去拜谒苏小小墓;在绍兴,他们没看成鲁迅故居,倒背诵了一遍《兰亭集序》。
与其说这是在“大串联”,不如说就是一趟文化之旅,颇有些古人“一生好入名山游”的风范。张老师的学生齐一民连说,张老师就像个离经叛道的“文侠”!
特殊年代的骑行难免会看到些特殊年代的风景。去南方之前,出现在张老师头脑里的,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但等他真的到了南京或杭州,眼前竟也是和北京一样的景象:来来往往的红卫兵,处处可见、处处可闻的标语口号。特别是当他们特许坐上回北京的火车时,在车上感受了摩肩接踵、寸步难移的滋味。车外的红卫兵总是纵身从窗户跃入,而车内的红卫兵总是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构成了一幅独特的画面记忆。
问及张老师对那个轰轰烈烈的学生革命场面有什么样的评述,张老师没有说太多话,只说都写在书里了,完全真实。然而令他遗憾的是,因涉及敏感题材,出版的书有所删节,众多场面描写和更为细腻的心灵感悟都没有被呈现出来,而是显得更加积极、向上、充满红色年代的正能量,但也显得有些不疼不痒,很多“苦”的东西没有被舒展开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苦途》不仅是亲历者个人经验的怀旧记录,也是一个国家在特殊年代中的反映与写照,为后世保存了一份充满现场感和历史感的珍贵资料。
当年身处其中的青年张金俊或许还未能完全体悟时代的意义,但将近半个世纪后,业已78岁高龄的张老师在写下那些故事时,会有更为刻骨的感慨与思考。他的书写或是沉默,都有着可堪琢磨的意味。
苦途中,令张老师感受最深的,不是某个特定的场面、风景,而是“国家”。“我看到的大海、大山、建筑、城市格局,都是真切的事情,丰富了我对国家的认识。这个国家好,这个国家不是空洞的,这个国家表现出了历史的渊源和面貌。
” “国家”,这个词语很抽象,但出现在张老师的叙述中,仿佛有种不拘于时间和地域的超越性和具象性。身处一种“在场”的历史环境中,很难想象张老师这种超越性是从何而来。不过,就像齐一民所评价的,几十年前就有“文侠”的禀性、有骑行中国的时髦想法,张老师与所处的时代始终是有点儿距离的。我们能够相信的是,他们那辈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宏大话语是真诚的,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不容置疑的真诚。
二排左一为张金俊,后排右一为刘心武
作为一个“骑行”的前辈,谈起对这些年大肆流行开的骑行运动的看法时,张老师连连点赞说,鼓励去鼓励去,要有机会,他也想去呢!
张老师能做出“骑行中国”的壮举,倒也是有传统的。在那个交通工具除了自行车就是走路的年代,他最爱的就是骑着爱车到处跑,还和萧克、杨成武等大将都有过交情。七八十年代,作为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还常常组织全班学生聚众“骑行”,从市区一路骑到百花山,来回两百多公里。
晚上就睡在公路上,回来第二天接着上课。后来,干脆组织了学生话剧社,自任导演,带着同学们到周围的县里,一个村接一个村地演《雷雨》、《蔡文姬》、《屈原》等经典戏剧,惹得怕耽误孩子学习的家长们意见频频。
他文体细胞丰富,在课上给学生们大讲他在海里游泳时是奔着一个岛游的。上作文课,他把大家带到香山顶上,出个不合时代潮流的文艺题目,让学生们做口头作文。学生的周记本发下来,上面是他用红笔密密麻麻写的批注修改。齐一民上他的课是在八十年代初,说“张老师上课能把人‘魔’住,口才极好,指哪打哪”,堪称“学生偶像”。
“这种人思维和正常人不一样。”这是张老师爱人的评语,看起来像批评,意思却是这种人很酷。两人曾做过一件现在看来也显得叛逆的事情。在大学生是个稀罕物的五十年代,正在地质学院上大二的他们竟罔顾不许恋爱的规定,擅自相恋,并甘愿为爱情双双辍学。连学都敢辍,张老师一路离经叛道到底,骑行中国之类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也就不奇怪了。
在刚刚解冻的年月里,刘心武的“班主任”令人惊诧,但无论是感化小流氓,还是教育思想僵化的“好学生”,张俊石身上都有着一种响应时代的“政治正确”意味。张金俊否认自己就是张俊石,但他的学生都认为他比张俊石更酷、更高、更丰富、更超前。“他是个理想主义的人,跟正统有点造反。”
直到现在,78岁高龄的他依然如此。张老师前些年因突发脑梗,现在说话不如以前利索,也没法再续写“苦途”,但他始终安安稳稳坐在那里,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脑袋里很清楚。你若是打乱他的话语顺序,他会说,等一下,一会我会讲这个。他的学生和爱人在旁边讲他的轶事,他总静静听着不说话,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