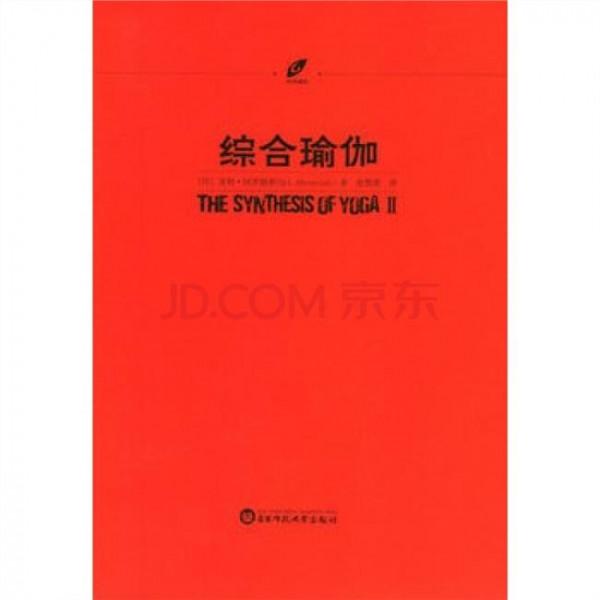徐梵澄与印度文化 译介印度古代宝典 徐梵澄纪念文集
据新京报报道:今年是中印友好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持、上海三联书店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推出的16卷《徐梵澄文集》,无疑将给两国的文化交流增加足够的分量。
此《文集》编辑、整理历时四年,包括论文与论著、小学菁华(英文)、英语论文与论著、文论及诗集、《社会进化论》、尼采六种、《薄伽梵歌》与《歌论》、《母亲的话》、《瑜伽论》、《神圣人生论》、《五十奥义书》。3月15日将在全国各大书店上市。
时下学人对徐梵澄了解不多。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孙波认为,徐梵澄由翻译尼采到介绍室利阿罗频多,从译介印度古代宝典到阐扬中国文化菁华,其心路历程和精神轨迹,端的是沿着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迈进的。本《文集》之文字犹如一座精神的富矿,有待于后来者“入山采宝”。
徐梵澄多才多艺,在学术作品之外,广泛涉猎艺术领域,包括版画、木刻、绘画、书法等各个方面,此为梵澄部分艺术作品。
翻译成就:坚持纯精神的“立义”的翻译传统
在20世纪的中国翻译界,首先作为翻译家名世的徐梵澄是非常特殊的。要理解徐梵澄的意义,也许只有在翻译史和近代以来的较大的思想语境和精神关联中,才能准确一些。
作为翻译家他一个人将传统与现代印度典源的精粹翻译完成,这原本应该是一代人的任务,但由他一个人完成了。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被我们忽略而无力从事的独立文化体系。
中国有两千年的翻译史。中国没有传教传统,却有取经传统。笼统地说,中国的翻译史有三大阶段——始于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有传教士和中国士人共同参与的西学翻译,以及从林则徐、魏源开始兴起的近代翻译高潮,这个时期延续至今。
当然,哲学、文学、艺术乃至宗教等人文方向的翻译工作一直也有人在做,但不管怎样,这个领域事实上并非主要的聚焦之处。所以,在此有必要重提鲁迅所倡导的另一个翻译传统,那就是与“立人”直接相关的、纯精神的“立义”的翻译传统。
没有健康的心性结构,“人”无从立,人无从立,所有的制度建构,终究不过是空中楼阁。从这种视角来看,徐梵澄的翻译启蒙来源于鲁迅。尤其是早期的鲁迅思想。从“改造国民性”走向建立新的心性结构,以世界公民的心态,探索不同的精神传统,传统通过立人来改造社会。让“有路可走”和“有家可归”成为一个时代主题的不可或缺的不同方面。
徐梵澄世家出身,家庭教师是王闿运的弟子,用统传的方式接受国学的熏陶;而他的父亲又是开明士绅,他很小时就学外语。同时他有很强的反叛性,家里让他去武昌学医,但不久(1927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
作为翻译家徐梵澄的伟大在于他将“立义”——为生命和生活建构意义世界的问题重新置于他的终身努力的核心。中国民众大多知道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但不知道早在2-3世纪,佛教在印度就逐渐衰落。而印度古典时代的精神遗产(如《奥义书》)、印度当代的精神财富(如当代“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思想),却往往不为国人所知。
徐梵澄系统地翻译及著述,不但为我们打开通往另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的门窗,还为我们通向我们性灵深处的真自我,发出了诚挚的吁请和敦促。
当代玄奘的孤独之路
新京报:听说海外有学者称徐梵澄为玄奘第二,怎么来看待,异同又在哪里?
孙波:这个比喻不过分。玄奘在印度待了十七年,徐梵澄待了三十三年。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二人精神同其伟大。玄奘从事的佛教唯识学,与吾华亲和不够,立功未远,后下声势渐没。而徐梵澄系统地译出印度民族之大经大法,即古今韦檀多学一系的经典,这贡献岂可谓小?尤其是印度“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思想,是今之印度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理论武器,亦是该民族未来光大复兴的精神旗帜。
阿罗频多的精神哲学,特别张扬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完全契合于我国儒家思想之健康向上一路。我以为,精神不悖,义理也合,那么,对话还成什么问题?交流还有什么障碍?
新京报:如此说来,徐梵澄的影响应该既广又远,何以他的声名不被多少人知晓?
孙波:这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工作性质有关。你要注意他的劳作过程,譬如盖房,从小工到设计师,皆由他一人完成。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个人主义”,但要冠之以“崇高”二字。他的观点是:只有健康的个人才能合为健康集体。
这好比“一体”而“两端”,其“道通为一”(庄子语)。个人要向崇高转化,是应然之理,要学习,求进步,超出自己的局限性,若人人为之,时时为之,整个人类历史就真成为了一个“文化培育的过程”(康德语)。
但是,凡应然之理,实现起来都是极为漫长的。他的学问不是求“现世报”,而是教人“往前看”,“向上走”。至于名利,在他看来皆为眼前或本地之物。他一般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带学生,我们可以这么来看他的“不合群”:他对自由的心灵与自由的时间锱铢必较。
新京报:他不太为人所知或径直说被“忽视”吧,是不是与他坚持的高境有关呢?
孙波:也可以这么说。如果真要深入了解他的学问,《五十奥义书》和《神圣人生论》就不能不看,可是能啃下来的人不多。另外他的工作,别人也无法替代,比如我见过他做的翻译,《佛教密乘研究——摄真言义释》,一纸分步聚为四:梵语原文、拉西文注间、古汉语注音,然后是古诗体译文。我当时与他开玩笑说:“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在干这活计了!”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说:“可能的”。
新京报:你说梵澄所治之学是鲁迅的精神建设的学理性建构。请具体概括一下。
孙波:是的。因为精神哲学从学术形态上来说,是双摄哲学与文学。
鲁迅当年苦恼“两条腿只能走一条路”,并有和王国维一样的困惑,即所谓“可信者(不妨看作哲学)不可爱,可爱者(不妨看作文学)不可信”。因此他自外于学术圈,宁肯以文学作为战斗的武器,因为,文学有跳跃样的“灵感”。
而精神哲学,重“灵感”,重真觉,出自以诗的语言,又不离清晰的学术概念,从而在高境上解决了“可信者”与“可爱者”的矛盾。这一路径就是“超”出一般“心思”,谓之“超心思”,亦是阿罗频多文学。(记者:曹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