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恕、张玉艳:努尔库运动与葛兰运动的关系辨析
在当代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当中,努尔库运动(The Nurcu Movement,又称“光明道路运动”)和葛兰运动(The Gulen Movement)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葛兰运动,由于它在埃尔多安率领“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被称为除该党和军方之外的土耳其的“第三股力量”[1]。
但是,这两个运动并不是孤立发展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普遍认为,葛兰运动是努尔库运动分裂产生的一个分支,因此又被称为“新努尔库运动”(The Neo-Nurcu Movement)。
鉴于国内学术界尚未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实践活动进行系统分析[2],本文旨在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并概述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境内外的发展状况。
一、努尔库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努尔库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库尔德人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î,1876—1960年)在土耳其创立的,它在土耳其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早年的努尔西强调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的相容性与调和性,但在经历多次挫折和对现实进行反思后,他将《古兰经》作为思想的指导,接受了苏菲主义思想,并寻求共同的穆斯林兄弟情谊。
可以说,伊斯兰教是努尔西思想的基础,他的民族主义观也建立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
他认为伊斯兰世界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但伊斯兰世界应该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因为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不应存在种族主义,之所以在穆斯林内部划分出民族、族群,是为了相互识别[3]。鉴于此,有学者批判努尔西的思想主张带有“泛伊斯兰主义”的色彩是不无道理的,这也成为努尔库运动后来被用于进行反苏反共的一个重要原因。
1919年英国占领伊斯坦布尔之后,努尔西出版小册子,揭露英国人的卑劣行径,支持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土耳其建立了凯末尔世俗政权。凯末尔政府考虑到努尔西在反抗英国侵略中的作用,邀请努尔西来到首都伊斯坦布尔,并吸纳他为国会议员。
但是,努尔西进入国会后开始宣传伊斯兰教思想,这使凯末尔大为不悦[4]。1925年谢赫·赛义德发动了第一次反对凯末尔主义的库尔德人叛乱,尽管努尔西并没有直接参与,但当局十分担心努尔西领导的力量支持库尔德人,因此以宣扬极端伊斯兰思想、开展非法宗教活动为由禁止努尔库运动活动,努尔西此后经历了长达23年的流放和囚禁生活。
在这段时间里,努尔西写成了《光明集》一书,着力强调穆斯林的宗教意识。
随着《光明集》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秘密传阅,阅读者们被官方称为“努尔库”,意指“追求光明的人”,从此便有了“努尔库运动”。 1946年土耳其从一党制转入多党制,社会政治环境得到缓和,1949年努尔西被释放。
1950年上台执政的民主党对宗教政策持宽容态度,努尔库运动获得了新的发展。1952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恢复努尔西文学作品名誉的决议,努尔库运动实现了合法化[5]。
受益于民主党执政的努尔西在广泛拓展活动空间的同时,逐渐改变了与当局隔离的态度和立场,转而支持民主党的统治,并在1950年代的多次大选中动员努尔库成员投票支持。也正是在1950年代,努尔库运动的主要传播组织“读经小组”(dershane,音译为“德尔沙尼”)的数量迅速增加。
但是,1960年5月民主党下台,土耳其出现了第一次军人干政,努尔库运动再次受到打压,加上努尔西的逝世,努尔库运动陷入了短暂的低潮。
随着苏美冷战的炽热化,站在北约阵营一边且与苏联南部地区拥有相似甚至相同的民族—宗教属性的土耳其自然成为一支反苏反共的重要力量,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伊斯兰教是治疗共产主义的良药”[6]。
20世纪60年代,中右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将努尔西思想整合进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通过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的调和来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日益增长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这使努尔库运动实现长足发展[7]。
这也是后来努尔库运动的境外活动以原苏联地区为主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但是,努尔西的逝世直接导致了努尔库运动的分裂。自1970年代起,葛兰运动成为努尔库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并逐渐成为一股影响土耳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葛兰与葛兰运动的发展
1.葛兰思想的成熟
葛兰运动的领导人是土耳其著名的宗教领袖、思想家法图拉·葛兰(Fethullah Gülen,1941年生)。他在埃尔祖鲁姆市的宗教学校学习时接触到努尔西的学说,后加入努尔库运动中一个比较关注政治的派系——叶尼·阿斯亚派。
自1969年起,葛兰开始宣传自己对努尔西思想的解读,并在土耳其商人的资助下建立了“光之屋”(lighthouses)学生宿舍,在青年人当中传教[8]。1970年代初,在左右翼政党激烈斗争的条件下,葛兰认识到应与各种政治组织保持一定距离,因而开始呼吁通过教育活动来扩大影响,“为大众服务”(hizmet)[9],并从叶尼·阿斯亚派分离出来。
1980年第三次军人政变后,国家公诉人针对葛兰的宗教立场对他提起诉讼,但由于军政府试图借助伊斯兰教来消弥左右翼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处于反对共产主义的需求,提出了“土耳其—伊斯兰结合”(Turkish-Islam Synthesis)的思想,所以并没有判处葛兰。
而且,自1980年1月起,土耳其开始实质性地进入市场经济转轨,这大大提升了社会环境的开放度和自由度,使土耳其的各种宗教派别有机会将宗教思想、商业成就和教育项目结合起来[10]。
葛兰利用这些条件加快传播自己的思想,于1978年开设了第一个“德尔沙尼”(与之前的“读经小组”不同,它以“高考学习中心”的名称公开活动),1982年开办了第一所学校[11]。同时葛兰运动的经济活动也取得了新的发展,于1983年建立了由多个有实力的公司所组成的“卡依纳科控股”(Kaynak Holding)企业集团[12]。
正是在1983年12月至1989年10月的厄扎尔政府时期,葛兰思想逐渐趋于成熟,社会影响力也逐渐增大,于是葛兰与当局之间呈现互相借重的发展趋势[13]。
可以说,1980年代是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境内迅速积聚力量的发展期,形成了“企业创造财富——资金投资教育——媒体宣传推动”的一条龙式的发展模式。
应该注意的是,葛兰思想的成熟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在1993年亨廷顿首次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冲击下,葛兰对伊斯兰教的命运做了更多深入思考,主要表现在人权、土耳其的发展模式、穆斯林社会与西方的关系等问题上。
葛兰支持人权,认为人们不论种族、肤色、性别为何,作为“人”的存在都是高贵的,但葛兰把《古兰经》中对人权的解释奉为普世的、恒久的原则,并认为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人类社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和/或宗教差异,容忍和对话都是穆斯林处理与非穆斯林关系的关键[14],通过现代化的教育能够实现信仰与理性、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学的调和。
葛兰反对无政府状态,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维持社会有序的必要条件,土耳其应该走一条能够融合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中间道路,即在土耳其民族认同的国家话语(state discourse of Turkish national identity)与土耳其民族认同的伊斯兰话语(Islamic discourse of Turkish national identity)的结合处重构身份认同,通过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结合,复兴“现代奥斯曼意识”[15]。
葛兰还在土耳其的对外关系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土耳其与突厥世界具有强烈的共同认同,虽然与西方缺乏公共认同,但强烈渴望融入西方,与伊朗严重缺乏共同认同,所以土耳其应该整合中亚,并扩大西方在中亚的影响,并通过加入欧盟来认同西方,拉开与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的距离[16]。
至于“文明冲突论”,奥本大学学者理查德·佩纳斯科维克(Richard Penaskovic)则把葛兰的回应归纳为“容忍”、“信仰间的对话”、“慈悲之爱”三点,认为葛兰从伊斯兰教的信仰角度出发得出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共存的观点是正确的[17]。
葛兰的上述思想对葛兰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他对教育作用的重视和土耳其外交战略的思考成为葛兰运动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2.葛兰运动的国际化发展
苏联解体是葛兰运动开始进入国际化发展阶段的标志。苏联解体,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国家、中亚国家获得了独立,土耳其的各类组织获得了进军新市场的机会,其中不乏葛兰思想的追随者[18]。
从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责任、突厥语民族文化、伊斯兰教信仰、地理和地缘政治以及苏联解体导致的意识形态真空等多种考虑出发,葛兰运动把国际化发展的对象首先放在了周边的突厥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亚突厥语国家和俄罗斯的突厥语地区。
诚然,葛兰运动在这些突厥语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趁虚而入,也有诸如这些地区的教育危机、政治经济困境、外交政策调整、发展道路选择等原因,但这些因素的始作俑者仍然是苏联解体。因此,把苏联解体作为葛兰运动开始国际化发展的标志是合理的。
葛兰运动的国际化起于周边国家和前苏联地区,并逐渐向全球拓展。对此,有俄罗斯学者认为,葛兰运动是西方,首先是美国实施“大近东计划”中的一个因素,美国有关机构向运动提供资金支持,运动则向美方提供情报信息和搜集情报的便利途径(例如,以葛兰学校教师的身份搜集情报)。俄罗斯学者认为,“美国的利益在哪里,葛兰运动就在哪里”[19]。
下面以葛兰学校为例,说明葛兰运动的发展。表1清楚地显示出葛兰学校在1990年代上半叶已经在向全球拓展。这一时期,葛兰学校的分布虽然仍以原苏联地区为主(占到表中总数的87%),但在距离更遥远、文化差异更大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葛兰学校,尽管它们的数量还不算多。
现在,葛兰运动已遍及世界各地,在美国、印度、日本、德国、瑞士、荷兰、孟加拉国、越南、也门、柬埔寨、塞内加尔、新加坡、巴布亚新几内亚、阿富汗、巴基斯坦、苏丹、墨西哥、肯尼亚等国家和地区都开办了学校,全世界的葛兰学校已经超过1000所,仅在美国就有140所[20],独联体成员国约有200所[21]。
显然,葛兰学校的分布不再以原苏联国家为主,它们在那里的发展受到以俄罗斯[22]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主的打压,在中亚五国的数量约减至55所[23],在俄罗斯也有所减少。
相应地,葛兰学校受欢迎的地方,也是葛兰运动的其它组织发展迅速的地方,反之亦然。
表1 1990年代上半叶葛兰运动的学校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分布
资料来源:Bayram Balci. Fethullah Giilen's Missionary School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ir Role in the Spreading of Thrkism and Islam. Religion, State & Society, Vol. 31, No. 2, 2003.
还应注意的是,葛兰运动在国际化发展中采用了它在土耳其境内的体系型发展模式,这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葛兰运动都能独立发展,避免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弊端。我们以葛兰运动在中亚地区的运作模式为例,如图1所示。
葛兰运动设立了统一的管理组织——土耳其作家和记者基金会,通过对中亚各国境内的协会、公司、媒体的整体调控,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我们看到,这种运作模式使葛兰运动在中亚国家既有独立运作的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和媒体宣传,也有统一的行动指导。
葛兰运动在其它国家也基本上采用这种运作模式。例如,葛兰运动在德国利用支持自己的阿比和阿訇,开设了100多个教育组织(学校和培训中心),组织了约15个“咨询协会”,其中一个协会“Barex企业主协会”由柏林和勃兰登堡地区的150家公司组成,葛兰运动的主要宣传媒体《时代》日报(Zaman)、《源泉》期刊(Ирмок)、“埃伯鲁”电视台(Ebru TV)、“萨满沃鲁”电视台(Samanyolu TV)等在德国都有分支机构。
这些机构之间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体系,葛兰运动也因此被德国马尔堡菲利普大学伊斯兰学者乌苏拉·施普勒—施特格曼(Ursula Spuler-Stegemann)称为“德国最主要的、最危险的伊斯兰运动组织”[24],但德国民众大都对葛兰运动了解不多,也不排斥葛兰运动的学校、媒体和企业。
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也为了国际化发展的需要,葛兰运动的发展目标也在发生着变化,西方化、世俗化的成份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中亚地区,作为葛兰运动核心内容的教育也发生了变化。1990年代,葛兰宣称在中亚开设学校的目标是“使安纳托利亚的道德责任重返中亚”,明显表现出泛突厥主义的思想。
他认为,安纳托利亚曾经在道义和精神上支持过中亚,现在安纳托利亚更应该帮助经历过被殖民、被征服、被剥夺了自由信仰伊斯兰教的合法权利后获得独立的中亚人民恢复伊斯兰意识。
随着运动越来越具有国际性,也由于宗教教育的敏感性,葛兰在解释学校存在的目标时,对普世性的论据使用越来越多,而伊斯兰教的色彩有所淡化,但其目标并无改变,只是在进行公开宣传时更加隐讳。
当然,葛兰运动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目标是不同的。在突厥语国家和地区,葛兰运动中的突厥内容与非突厥语国家和地区相比,有明显的差异。也正是由于这些变化和区分,葛兰运动才能继续有序地进行国际化发展。
3.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境内的发展状况
与国际化发展的良好势头不同,1990年代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境内的发展却是另一番景象。1995年,葛兰被指控“阴谋反世俗主义和企图建立神权国家”,他与当局的关系趋于紧张[25]。
1997 年,在军方发动的迫使繁荣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垮台的软政变过程中,葛兰曾支持军方。埃尔巴坎下台后,耶尔马兹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对违反《关于穿着世俗服装和参加亲伊斯兰集会的法典》的行为加强惩处,并在1999年以违反土耳其宪法为由禁止葛兰运动开展活动[26]。
自此,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境内处于非法状态。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葛兰以身体状况恶化急需手术为由移居美国。随后,葛兰号召追随者们积极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土耳其政府则缺席指控葛兰企图破坏土耳其宪法[27]。
但是,这一时期,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境内的发展已成气候。有资料称,2000年之前,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境内设有88个基金会,20个团体,128所私立学校,218家公司,17家出版机构,1个电台,2个广播台,1家无息贷款银行,1家保险公司[28]。
由于葛兰运动的隐蔽性很高,也由于它在土耳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9],所以,这些组织并未被完全清除,一部分转入地下活动,一部分则仍以合法身份公开活动,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境内的体系发展模式并未被打碎,这既为后来葛兰运动与埃尔多安进行“合作”提供了前提,也是埃尔多安对葛兰运动持双重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0年以来,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境内的发展状况与埃尔多安的政策密不可分。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葛兰曾发动运动成员投票支持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两大阵营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军方力量被削弱。
此外,两位领导人都支持扩大土耳其在境外的影响力,首先是在原奥斯曼帝国的地域内。可以说,两个组织的联盟实现了互利,葛兰运动利用联盟进一步渗入国家内务系统和司法部门,同时通过它所控制的传媒机构为埃尔多安提供必要的公众支持,使埃尔多安获得了一个反对军方和其它阻碍他扩大政治权力的势力集团的重要盟友。
埃尔多安上台初期,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境内的影响力得到加强。2004年,正义与发展党的议会成员中有1/5是葛兰运动成员,其中就有司法部部长和文化部部长。
2006年,土耳其原警察局局长阿吉里·塞尔达尔·萨占(Адиль Сердар Саджан)指出,在土耳其警局中葛兰运动成员担任的领导职务超过了80%。
埃尔多安还利用司法系统中的葛兰追随者,对“厄尔根尼康”案件[30]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司法审判,葛兰运动则趁机扩大其在国家机关中的力量。曾当担任过土耳其总检察长的伊里汗·吉哈涅尔(Ильхан Джиханер)在2007年对葛兰运动是否从事非法金融业务展开调查,但因受到政府施压而被迫停止调查。
2010年他被以参加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厄尔根尼康”为由逮捕,类似情况已发生多次[31]。一时间土耳其社会上出现了“任何试图反对葛兰的人都会被消灭”[32]的恐惧。此外,埃尔多安对土耳其宪法进行了修改,于2008年取消了对葛兰的所有指控,但未赋予葛兰运动合法地位。
当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军方力量被削弱、在政治舞台上受到严重排挤时,联盟的既定目标便实现了。但是,正义与发展党和葛兰运动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尽管前者当中有不少人是葛兰的追随者。
我们看到,政治舞台和对政治舞台的影响力只是葛兰运动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其目的,无论政权或反政权载体的政治意识形态为何,葛兰运动都很容易找到与它们进行合作的利益结合点。而且,土耳其社会对埃尔多安加强政权、“侮辱军人”的做法表示不满,社会局势呈现紧张,这对土耳其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
出于对这些情况的担忧,埃尔多安政府转而在“厄尔根尼康”案件上妥协,不但限制葛兰运动在土境内的活动,而且把最不受埃尔多安欢迎的葛兰运动成员从政府中调了出去。
作为回应,葛兰运动则攻击埃尔多安的支持者[33]。这样一来,“厄尔根尼康”案件就发挥了另一种作用,即从由葛兰运动支持的打压军方的司法审判,变成以牺牲葛兰运动成员为代价与军方妥协的砝码。
埃尔多安还对司法系统和执法机关进行了整顿,撤换了一大批葛兰运动成员。例如,他把伊斯坦布尔的700名侦察、反恐、打击有组织犯罪机关的警官调往土耳其的东南部,这些人被认为是葛兰的支持者[34]。埃尔多安对葛兰运动的担忧至今犹在。2012年6月,他邀请葛兰返回土耳其,葛兰以害怕回国会损害葛兰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为由,拒绝回国。埃尔多安的“邀请”和葛兰的“拒绝”都是互不信任的表现。
自葛兰运动兴起以来,它不仅成为影响土耳其国内政治变化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土耳其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从土耳其政府对外政策的需求来看,多届政府都认为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境外的活动有利于扩大土耳其的影响力,有助于实现土耳其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在穆斯林—突厥语国家。
例如,埃杰维特总理在2000年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发言强调葛兰学校在传播土耳其文化上发挥的重要作用[35]。埃尔多安不仅重视土耳其的境外影响力和吸引力,而且也非常看重葛兰运动在扩大土耳其的境外影响力上的作用。
从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境外的影响力来看,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葛兰运动的教育和经济活动受到当地居民和政府的欢迎,特别是在尚未与土耳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它不仅是土耳其文化的代表者和传播者,而且也是土耳其利益的唯一代表。
所以,埃尔多安政府对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境外的活动持支持态度。这样一来,目前土耳其政府便对葛兰运动形成了“国内限制、国外支持”的双重政策。
三、葛兰运动对努尔库运动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葛兰运动是努尔库运动发生分裂时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派别,它自然继承了努尔库运动的许多内容和形式,而且,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土耳其社会环境的变化、葛兰思想的成熟等原因,葛兰运动还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使它与努尔库运动明显不同。应该说,葛兰运动继承和发展了努尔库运动,但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创新。
从努尔库运动和葛兰运动的发展历程来看,二者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1.对文化伊斯兰在伊斯兰教复兴中的作用进行积极评价,对政治伊斯兰持怀疑态度,但不拒绝利用各种政治势力的力量,所以两个运动都与政权既存在斗争,也进行合作。
2.都推崇《古兰经》的作用,分别把努尔西和葛兰对《古兰经》的解读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作为行动指南,这使两个运动具有宗教色彩。3.吸收、借鉴西方文明成果,否定哈乃斐派和沙斐仪派这两大传统伊斯兰学派的合理性,认为传统伊斯兰教“落后”,“与科学和进步不相容”[36]。
4.宣扬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强调安纳托利亚伊斯兰是多样性的统一,认为土耳其对原奥斯曼地区负有历史责任。
5.通过宣传东方非穆斯林的历史、社会、智力和道德缺陷,使追随者对非穆斯林和不信仰努尔西和葛兰思想的穆斯林形成负面形象。6.都曾拒绝承认世俗政权,使追随者对世俗国家形成消极态度,号召他们积极参与政治进程。
7.非暴力是两个运动的主要原则,但在宗教动机充足的情况下,允许使用暴力手段达到目的[37]。8.都强调在年轻人当中宣传自己学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9.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出或被赋予反苏、反共、反俄的倾向和内容。
自1970年代以来,葛兰运动与努尔库运动渐行渐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正如巴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拜拉姆·巴尔齐(Bayram Balci)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努尔库运动和葛兰运动。
从现有研究来看,二者的区别主要在:1.在指导思想上,葛兰运动所奉行的葛兰思想比努尔库运动所坚持的努尔西思想更西方化、更现实,而且,葛兰运动正在从文化伊斯兰迈向后伊斯兰主义[38]。中东技术大学教授伊丽莎白•奥兹达格(M.
Elisabeth Özdalga)认为,主流的正统逊尼派伊斯兰、纳格什班迪教团的传统和努尔库运动是葛兰思想的主要来源,但与努尔西不同,葛兰更加强调为大众服务的“虔诚的行动主义”(pietistic activism)而不是精神的需求[39]。
拜拉姆·巴尔齐则把葛兰运动视为后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一部分[40]。2.在运作模式上,葛兰运动用“商人—记者—师生”这种协调一致的体系[41]和现代化的网路技术[42]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其影响力已经渗透到商界、教育界、传媒界,在个别国家甚至已进入政界、军界。
努尔西的追随者们仍然坚信努尔西的著作《光明集》,努力组织阅读活动来扩大努尔西的学说,他们人数不多,影响不大,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宗教学校,主要在住宅房屋内举行宗教聚会[43],而葛兰运动的发展则迅速得多,规模也大得多。
3.在资金来源和使用上,努尔库运动以接收捐款为主,资金主要用来组织读经活动;葛兰运动的资金来源比较隐蔽,但有研究估计,葛兰运动每年的预算超过250亿美元,葛兰及其追随者的企业投入的资金占到企业营业总额的10%[44],这是葛兰运动的主要资金来源,而运动成员的捐款只是一种补充来源,这些资金主要用来进行教育办学,例如向到土耳其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部分资金用于慈善事业。
4.在国际化发展水平上,葛兰运动的国际化程度和受欢迎度都高于努尔库运动。
现在,葛兰运动已经遍布全球各大地区,95个国家已确定本国存在葛兰学校,而据葛兰运动成员的说法,它可能在140多个国家进行积极的教育和传教活动[45],而且,葛兰运动的企业和学校在很多国家受到当地居民和政府的欢迎。
努尔库运动不但在规模上远小于葛兰运动,而且在土耳其、中亚合作组织成员(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被禁止活动,处于地下活动状态。5.由于不同的发展模式,努尔库运动和葛兰运动在自身实力和发展前景上呈现不同。
以“读经小组”为主要宣传方式的努尔库运动没有独立、稳定的资金来源,其生命力主要依靠成员对努尔库思想的信仰度,而且运动内部还在继续分化成各种派系;葛兰运动则呈体系性发展,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完善的宣传媒体,利用办学塑造源源不断的追随者,而且,还通过迈向“后伊斯兰主义”,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6.“泛”的侧重点不同。努尔库运动和葛兰运动都有“泛”的内容,但在现阶段前者更倾向泛伊斯兰主义,后者则更倾向于泛突厥主义。
葛兰运动强调土耳其的大国地位、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责任,认为所有突厥语民族都应以土耳其为中心联合起来,泛突厥主义是泛伊斯兰主义的“初级阶段”(''преддверие''),当突厥语民族联合起来后,所有穆斯林应该以土耳其为中心联合起来[46]。所以,现阶段葛兰运动在突厥语国家和地区的活动经常被指责为推行泛突厥主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葛兰运动继承和发展了努尔库运动的很多要素,但也进行了大量创新。经过40余年的发展,葛兰运动已经从努尔库运动中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思想较为温和、体系更加完整、组织更加有序、实力更加雄厚、国际化程度更高的组织,因此,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来进行研究,而不仅仅是努尔库运动的一个分支,尤其是21世纪以来,它在土耳其境内外的发展状况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四、结语
在土耳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努尔库运动和葛兰运动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多数人至今仍停留在“葛兰运动是努尔库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分支”的认识水平上,未对二者的区别做深入思考,甚至我们看到的很多资料都把二者简单地完全等同起来,这造成了认识的模糊和表达的混乱。我们认为,必须清楚地区分葛兰运动和努尔库运动,既要看到二者的联系,更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
与此同时,应该抓紧对葛兰运动及其对我国周边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研究。现在,葛兰运动已发展成一个“超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尽管它在一些国家受到质疑和打击,但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特别是在我国的西部邻国,葛兰运动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活动非常活跃,运动成员不仅与土耳其在那里的使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土耳其政府对葛兰运动在突厥语国家和地区的作用寄予厚望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与当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仅有许多当地政府高官的子女就读于葛兰学校,而且当地民众也能从葛兰运动开办的企业和学校当中受益。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中亚居民对葛兰运动本身并不了解,他们之所以对葛兰运动的学校、企业、媒体宠爱有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对葛兰运动的认同,而是由于对土耳其的认同,因为文化上的共性更容易在民间引起共鸣,而且共鸣的程度更深、持续时间更久。
但是,进入了这些组织之后,他们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受到葛兰运动所宣传的思想的影响。
尽管,葛兰运动比努尔库运动有了更多西方化、世俗化的要素,但并未改变“泛突厥主义”的内核(主要是在突厥语国家和地区实施)。已有资料指出,葛兰运动的势力已经进入我国新疆和台湾(多以“Hizmet movement”的名称出现)地区[47],这更需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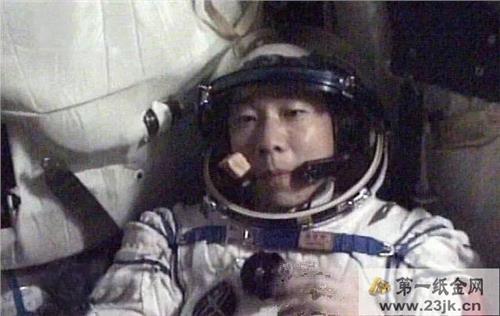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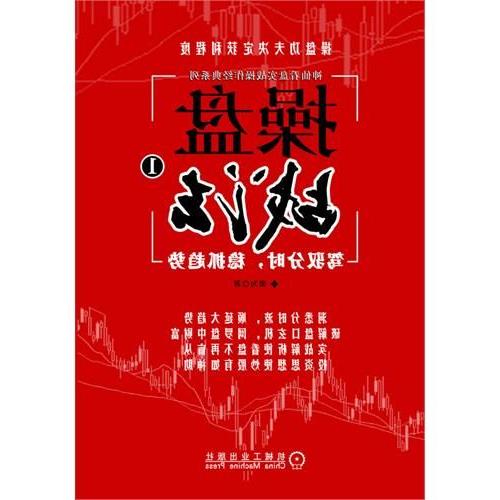






![>张尧域名 星光大道2011年度总决赛 赵本山弟子[张尧、张玉娇]无名组合获亚军](https://pic.bilezu.com/upload/2/4d/24d781eb48fdd19a0cc5378583955788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