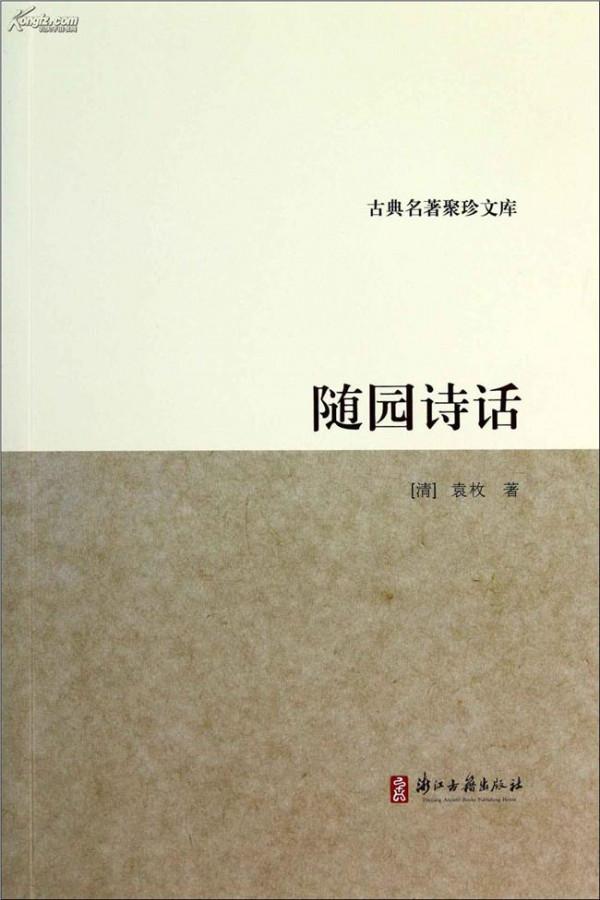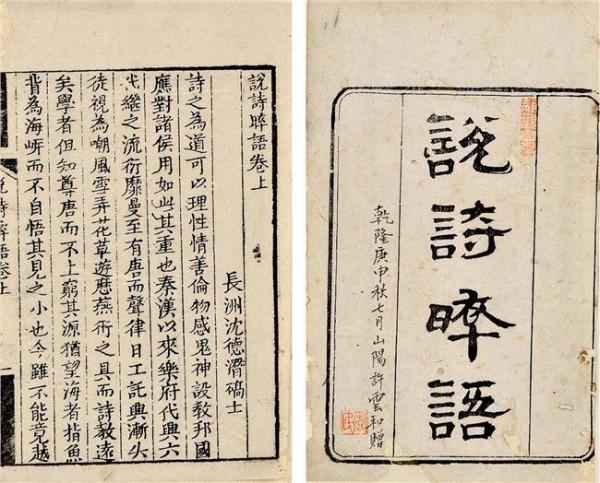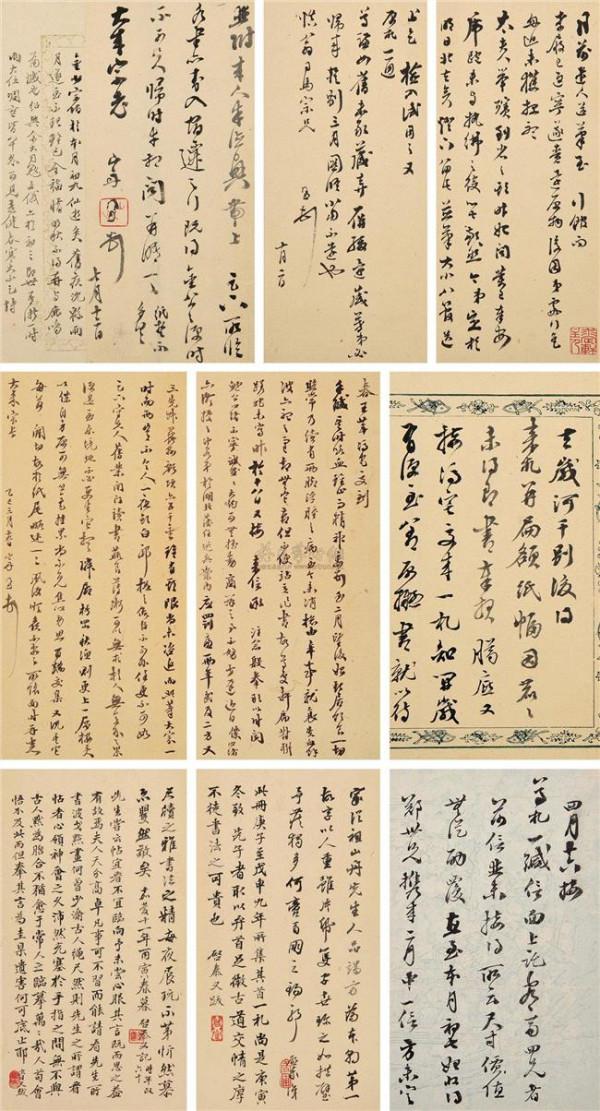清代沈德潜 清代格调派领袖沈德潜研究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不遇。四年,成进士,此后连获提升,至十二年,为礼部侍郎。十四年,诏以原品休致。此后恩遇益隆,得以优游林泉。
三十四年,卒,谥文悫。四十三年,江苏东台县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发,集内载沈德潜为徐所作传,乾隆帝乃下诏追夺沈阶衔、祠谥,仆其墓碑。沈著述甚多,有《沈归愚全集》,唐、明、清三朝《别裁集》,《古诗源》等行世。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三零五、《清史列传》卷十九、《碑传集》卷二钱陈群作《神道碑》、《归愚自订年谱》等。
德潜一生,能称异者有三。一是长寿。康熙末年,德潜年已半百,更历雍、乾两朝,卒,寿97。二是晚遇。成进士时,已经67岁。三是速达。67岁中进士已经是一奇,不到十年而位至侍郎,益奇。且退休后,给尚书衔,晋赠太子太傅,并予在籍食全俸,恩施至为优渥。
其原因何在?是他有超人之才,立大功建大业?非也。乾隆帝云:“伊自服官以来,不过旅进旅退,毫无建白,并未为国家丝毫出力,众所共知。”(《清史列传》本传》)沈德潜的所有传记资料都没有他政治作为的记载。
乾隆十一年沈德潜升内阁学士后,乾隆帝谕曰:“朕向留心诗赋,不过几馀遣兴,偶命属和,其中才学充裕,如沈德潜等,间或一加超擢。……不知沈德潜优升阁学,朕原因其为人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此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优擢。”(同上)
德潜之速达,一是确实有作诗方面的原因。《归愚文钞》卷十八《御制诗集后序》云:“臣向以有韵之语,受九重特达之知。”乾隆帝也云德潜“以诗文受特达之知。”(《清史列传》本传)当时能诗者甚多,为何乾隆帝独重德潜?这与德潜言诗之道有关。
沈德潜将《国朝诗别裁集》进呈御览并求序,因集中列钱谦益诗,乾隆帝训斥道:“且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谦益诸人,为忠乎,为孝乎?德潜宜深知此意。
今之所选,非其宿昔言诗之道也。岂其老而耋荒?”(同上)其“宿昔言诗之道”,言忠言孝,与乾隆帝合可知。二是德潜乃乾隆帝树起的样板。徳潜67岁尚赴进士试,这本身已见出统治者以科举牢笼士人的功效。让他中进士,超常地提拔他,正是为了加强这种功效,让更多的汉族士人受其牢笼,缠死于其中而不知。
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以德潜为托塔天王,云:“筑黄金坛以延士,则必请自隗始。”此若言其中进士获巨恩,则是戏语正说了。此后,士人晚遇者,虽尚未有超过德潜者,但50馀岁中进士者,知名人士中亦有好几个。由此可知,50以外仍然赴试者,肯定不少。这不能说与乾隆帝加殊恩于德潜全然无关。
德潜挣扎于科场半个多世纪,儒家思想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归愚文钞》卷15《答滑苑祥书》云:“自唐虞以来,理则天人性命,伦则君臣父子,治则兵乐刑政,如江河乔岳,万古不可磨灭者,六经四子文是也。
”其保守、迂腐可知。儒家所重,在行道与传道。德潜出仕行道,苦无机会。讲学传道,苦无渊博的学问与闪光的头衔作为资本。他出身寒门,醉心功名,除了科举所用外,经史功底,并不扎实。幸而为诗得叶燮指受,且曾以诗歌获得诗坛前辈泰斗王渔洋“横山门下尚有诗人”一语,(《竹啸轩诗集》卷一)也得到过尤侗等其他前辈诗人的赏识,(《归愚自订年谱》)于诗之道,颇有信心,遂于帖括之馀究心之,以实现其自身价值。
其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充满儒家思想,亦在情理之中。
儒家向重教化。于乱世,教化难于见功而多不行。于太平之世,教化除了加强思想统治之外,又有点缀润色之功,因而为其时统治者们所乐道。儒家诗教,乃其教化之一端。当时已经承平数十年,满族统治者早已懂得用儒家思想统治天下的奥妙,其时正是需要诗教之际。
沈德潜打起诗教大旗,自己所作,扬忠说孝体现诗教,于他本人,或仅是出于传统儒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立身扬名、实现个人价值的观念,然正好迎合统治者需要,遂以近古稀之年,得乾隆帝赏识而奇迹般地步步青云直上。
诗教是德潜论诗的出发点与归宿。他把诗歌的社会教化作用看得极为巨大:“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物伦,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说诗晬语》,以下所引德潜语未注明出处者出此书。)其《明诗别裁集序》中,甚至把明朝之亡,与诗教之衰落联系了起来。
既然重视诗教,故于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他以前者为重。诗歌内容之所重者,情也,意也。他称“诗贵性情”,又主性情须真,诗歌须表现诗人的个性,如此方使人能读其诗而知其人。他说:“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读太白诗,如见其脱屣千乘;读少陵诗,如见其忧国伤时;其世不我容,爱才若渴者,昌黎之诗也;其嬉笑怒骂,风流儒雅者,东坡之诗也。
即下而贾岛、李洞辈,拈其一章一句,无不有贾岛、李洞者存。倘词可馈贫,工同鞶帨,而性情面目,隐而不见,何以使尚友古人者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乎?”这种观点,叶燮《原诗》外篇卷三也已经言之。
德潜又明确指出“诗贵寄意”,“意在笔先”:“写竹者必有成竹在胸,谓意在笔先,然后着墨也。惨淡经营,诗道所贵。
倘意旨间架,茫然无措,临文敷衍,枝枝节节而成之,岂所语于得心应手之技乎?”意又不能“雷同剿说”:“咏古诗未经阐发者,宜援据本传,见微显阐幽之意;若前人久经定论,不须人云亦云。王摩诘《西施咏》,李东川《谒夷齐庙》,或别寓兴意,或淡淡写景,以避雷同剿说:此别行一路法也。
”咏史如此,写其他题材,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无新意,宁可“别行一路”,也不要重复别人之意。情和意,又当以深挚为上。“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隐,借有韵之语以传之。
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远嫁’,或慷慨吐臆,或沈结含凄,长言短歌,具成绝调;若胸无感触,漫尔抒词,纵辩风华,枵然无有。”深挚之极,自然“不得不言”了。重性情之真,重诗意之新,实已先于袁枚发之。
既然重内容,形式自然不能废,因为内容正有赖于形式的表现。他说:“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
”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服从于内容的表现,诗人不能脱离内容而片面地追求形式,更不能为讲究形式而脱离乃至妨碍内容的表达。其“以意运法”而不能“以意从法”之说,就是这个道理。
他又以“意”与“字”的关系说明之:“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近人挟以斗胜者,难字而已。”此乃见道之语。当时诗人以炼字著称者有二,一是厉鹗,一是胡天游。二人炼字确实有独到处,但是也确实有一种用难字的趋向在。德潜“近人”云云,定有所指。人云沈、厉曾同在浙江史馆而论诗不合,(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十〉等)此或也是“不合”之处。
若仅就以上观之,德潜论诗,识解宏通,跟诗教似乎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但也并没有多少过人之处。然而,他对诗歌的思想内容(包括诗情诗意)和艺术形式方面,还有进一步的论述,就诗教的需要将它们限定在某个范围内,这就显示了他论诗的特色,他的过人之处与迂腐之处。
他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襟抱”、“学识”是一种储备,一遇机缘触发,就产生诗情诗意,写出佳作。
仅就诗情诗意而言,“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产生的诗情诗意,当然肯定是第一等的了。这就保证了诗歌思想内容的“质量”。此论实是本于叶燮《原诗》内篇上卷一:“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
有胸襟,然后能裁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辩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杜)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如钻燧之火,无出不发;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夭乔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无不具足。”连语言也是差不多。
“第一等襟抱”似乎难以把握,人们的标准、着眼点未必一致。德潜所说的“第一等襟抱”的内涵是什么呢?《归愚文续钞》卷八《尚宝应农部诗序》云:“作诗者必先具诗人之胸,方寸之内,空洞无物,及与物相遭,凡四时之和煦寒暑,……往古之是非得失,块垒不平,一一取而见之于诗。
惟其中有触之即动者也。夫诗人之胸,既已本之于天,然或情欲婚宦,耽耽逐逐,渐汨没灵襟,又或略观大意,入焉不深。……终于得其粗而遗其精。则求诗之工,又在乎用力之专、用心之一者焉。
”诗人胸襟之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灵襟”,但其人的俗务情欲,会使这种“灵襟”汨没。其实,这种“灵襟”,就是指诗人感受外在世界的一种极为敏感的能力。有纯真才有“灵襟”,“空洞无物”便是纯真的形象写照。
如果诗人为世俗名利等等所拘,一旦失去纯真,“灵襟”就会大减甚至消失。又《归愚文钞馀集》卷一《高文良公诗序》云:“惟夫笃于性情,高乎学识,而后写其中之所欲言,于以厚人伦,明得失,昭法戒,若一言出而可措诸国家天下之间,则其言不虚立,而其人不得第以诗人目之。
”其人胸中所怀,乃国家天下之教化、治乱、得失、成败。由此可见,“第一等襟抱”,一是要保持诗人的纯真,二是要胸怀国家天下,此二者又都忌个人名利萦绕于其中。
有这样“第一等襟抱”的人,其思想感情必然高尚,这就足以保证其诗中思想感情的高尚。诗人能从外在世界发明新意,但新意也有美丑、善恶、深刻与浅俗、重大与卑琐等等的差别。其人具有“第一等襟抱”,他就能裁度新意而出之,将美的、善的、深刻的、重大的新意用诗歌表现出来。德潜论诗,重诗人品格,揭示了人品与诗品之间的关系,强调诗人的思想品格修养的重要性,这些,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第一等襟抱”必须胸怀国家天下,必须保持诗人的纯真,这些都不错。不过,胸怀国家天下,还有个立场问题。德潜所赞赏的立场,当然是封建立场。其《文钞》卷12《缪少司寇诗序》云缪“取高第,官侍从,乘史笔,柄文衡,佐秋官。
人文国论,储峙胸中,未尝听听焉以诗自鸣,争短长于音韵藻采间也。”如此“人文国论”,其核心乃封建伦理道德。因此,如此“第一等襟抱”所出思想感情,总是无法超越封建伦理道德的范围,唯其如此,诗歌才能担当在封建社会中履行教化的重任。这体现出沈德潜诗论明显的保守性和落后性。
“第一等学识”范围极广,当然包括经史学问,分析研究社会问题的能力等等。学识高,作诗立意能高屋建瓴,诗也就容易作好。《文钞馀集》卷二《吴南勤诗序》云:“读书多则理足,理足则识高,识高则气昌辞达,而神自生焉。
”在德潜看来,“第一等学识”还应该包括明了诗歌发展的源流正变,富有正确的取舍能力。他说:“作文作诗,必置身高处,放开眼界,源流升降之故,了然于胸中,自无随波逐流之弊。”他为了明“源流升降”,也是为了帮助人们明了“源流升降”,作了大量的工作,编选了《古诗源》和三朝诗《别裁集》等诗选。
他说:“秦汉以来,乐府代兴,六代继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衎之具,而诗教远矣。
学者但知尊唐而不知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而诗道始尊。”又《唐诗别裁集序》云:“备一代之诗,取其宏博,而学诗者沿流讨源,则必寻究其指归。
何者?人之作诗,将求诗教之本原也。”《古诗源序》云:“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他辨诗歌的源流升降,着重点在于“诗教”,求“诗教之本原”。
所谓“诗教之本原”即是“《风》《雅》之诗教”,“《风》《雅》之遗意”。这就为诗教在诗歌史上找到了强有力的依据。明诗歌源流升降之辨,当然能吸取古人诗歌创作的经验以丰富自己,但更重要的是,能志托《风》《雅》,心中有主,不至于被宗唐、宗宋、性灵等诗风所裹挟,自觉坚持作能像《风》《雅》一样行“诗教”的诗。
叶燮论诗,亦重明诗歌之源流升降,然其旨在以此证明诗歌发展变化的合理性,证明创新的合理性和复古的不合理性。
德潜之明源流升降,则在溯源而宗之,与其师事同而旨相反。宗《风》《雅》,也未必就不好。例如,继承《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我们今天不是也还提倡么?可是,德潜着眼的是“诗教”,“诗教”就具有封建教化的内涵了。他认为,诗至唐而大盛,但是离《风》《雅》之“诗教”已远,故论诗作诗,虽然还要取三唐之格,但应该用以行《风》《雅》所行的诗教。
在艺术表现方面,德潜主张“以意运法”的活法,而反对“以意从法”的“死法”,这完全正确。不过,以法将包括意在内的思想内容显豁呈露地表现出来,还是含蓄蕴藉地表现出来,这又是进一步的问题了。诗人不仅要将思想内容有效地表达出来,而且要让它动人,有较持久的魅力。
应该说,含蓄蕴藉者胜于显豁呈露者,因为它有味之不尽之意,更容易持久地吸引人。诗之能否行诗教,还在于它能否打动读者。德潜所欣赏的,也正是含蓄蕴藉一路。他说:“意主浑融,惟恐其露;意主蹈厉,惟恐其藏。
究之恐露者味之弥旨,恐藏者尽而无馀。”又云:“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言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
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王子击好《晨风》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讲《鹿鸣》而兄弟同食;周盘诵《汝坟》而为亲从征。此三诗别有旨也,而触发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唯其可以兴也。
”作者的思想感情体现在作品的形象之中,形象动人,而形象体现的思想感情随之感染人。形象大于思想,即成功的形象所体现的思想感情,比作者想要在其中体现的思想感情来得丰富。读者在受形象感动时,还会因为自身的情况而悟得作者并未有意识表现的思想感情。
相反,如果作者的思想感情已经表现得明明白白,就没有回味的余地,就失却了浑融性,也就减少了艺术感染力。因此,在艺术取向上,德潜之所以取唐而舍宋,主要原因盖在于此。
德潜推崇含蓄蕴藉,其落脚点还在“诗教”上。《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为什么“诗教”应该“温柔敦厚”呢?儒家重“温柔敦厚”。“儒”之为义,乃文雅、温顺、柔缓、敦厚一类的意思。仁爱、孝悌、忠恕,无不温柔敦厚,用于教化,其内容形式,当然也必须温柔敦厚。
因此,就诗歌思想感情方面而言,德潜主张不仅要合于封建教化的需要,而且要中正和平,即有怨气,也要“怨而不怒”。就艺术表现而言,德潜提倡含蓄蕴藉,“比兴互陈,反复唱叹。
”如此内容和形式一归于“温柔敦厚”,与“风雅之遗意”相合而称佳,然后诗教得行。德潜多次表现出此类观点。如《文钞》卷十二《方氏述古堂诗序》云方遭遇流放等逆境而“流离颠沛之中”,其诗“一归于和平温厚”。
卷十一《明诗别裁集序》言其选诗标准:“深造浑厚,和平渊雅,合于言志永言之旨。”卷十一《国朝诗别裁集序》云:“合乎温柔敦厚之旨,不拘一格也。”同卷《施觉庵考功诗序》云:“其词和顺以发情,微婉以讽事,比兴以定则,其体渊渊,其风泠泠,味之淡淡,而炙之温温,读者不自觉,静其志气而调其性情也。
是可谓诗人之旨也。”此外,如同卷《勤恪陈公诗集序》,卷十二《使滇集序》,《文钞馀集》卷二《轩渠集序》等,都有此类论述。
德潜认为,在诗歌发展史上,诗至有唐而极盛,读者于唐诗,犹“观水者至观海止矣”。(《唐诗别裁集》凡例)《文馀集》卷三云:“格调欲雄放,意思欲含蓄,神韵欲闲远,骨采欲坚苍,境界欲如层峦叠嶂,波澜欲如巨海渊泉,而一归于和平中正。
”此数者,正是唐诗的特点,也正是行“诗教”所需要的。因此尽管唐诗离“诗教”已远,其格调还是可取的,但必须以其格调写“诗教”内容,如此方合《风》《雅》之旨,亦即行《风》《雅》的“诗教”。德潜主格调,崇唐诗,倡“温柔敦厚”的“诗教”,其具体内容如此。
德潜在艺术取向上主汉魏唐诗,狭隘性是很明显的。他虽然不全盘否定东坡、剑南、遗山,(《诗钞馀集》卷七《书剑南诗稿后》)但于总体上否定了宋元诗,说“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别裁集序》),见宋元诗的缺点而未充分见到宋元诗的佳处,自然不能称全面。
艺术上排斥宋元诗,也排斥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作为一种诗歌理论,尤为失当。不过,德潜与明七子,还是有区别的。他确实从他所注意的诸角度肯定了明七子。《文钞》卷十四《七子诗选序》云:“七子者秉心和平,砥砺志节,抱拔俗之才而又亭经藉史,培乎根本,其性情,其气骨,其才思三者具备,而归于自然。
故发而为诗,……宗旨之正,风格之高,神韵之超逸而深远,自有不期而合者。
犹河山两成,条分南北,山不同而崚嶒之体则一也;水不同而混茫之气则一也,谓非诗教之正轨也?”然而,他对明七子没有全盘肯定。《古诗源序》云七子“其弊也株守太过,冠裳土偶,学者咎之。”并且,他根据七子之失的历史教训,对当时人们学汉魏唐诗株守太过、弃神理而取形似的倾向予以批评。
《归愚文钞》卷十五《与陈耻庵书》云:“假使王李以后有人焉,溯古人之真而不袭古人之迹,以自授其隙,公安、竟陵之徒何自而置其喙哉!今也不然,谓古体宜汉魏,某章不似汉魏,非诗也;近体宜盛唐,某句不似盛唐,非诗也。
诗之宗法在神理,而不在形似,乃弃神理而取形似,执己见以齐人。东坡之超旷,放翁之渊博,不可尽没也,或至取为诮让之词,与前时之贬汉魏盛唐者,异途一辙。
究其流极,仍必画西施之貌、规孟贲之目,而入于剽割仿佛之一途。设使其时复有有力之人如公安、竟陵、受之者,大声疾呼,以力矫之,势必靡然相从而风会又移于坏。”历史不会重复,但有时确实很相似。袁枚出,承公安、竟陵之说而昌大之,横扫各种复古诗风,而首当其冲者,正是德潜为首的学汉魏三唐和主“诗教”的诗风!
德潜之诗,多有为而作者。其中竟有几首有关朝政国事。如《竹啸轩诗钞》卷四《使者》云:“使者南来密网罗,楚囚严谴荷殳戈。健儿已入回中籍,少妇新成塞下歌。木叶山高人罕到,松花江远鸟难过。遥知乡陇关心处,目断吴天奈尔何!
”此诗明显为吴地遣戍塞外者而作。从首句看,此案颇为重大,朝廷派专人赴江南办理,株连甚广。诗人对受害者,有明显的同情在。此诗编年在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究系何年所作,失考。
卷十四《制府来》,写两江总督噶礼贪酷不法被杀事。本师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云:“此作无愧诗史,”可以与王世贞的《袁江流》相比美。《归愚诗钞》卷四《汉将行》写年羹尧事,暗示年参与立雍正事,雍正忌而杀之。
卷十七《百一诗》写江南百姓赋税等负担过重,“阊阖一何高,排云听谁叫”,直是为民呼吁。有云:“吾思牧民术,先威而后恩。治弊用重典,古人之所云。霜雪既已加,相济在春温。锄诛岂常用,盗贼亦平民”。希望地方官能行仁政。
“盗贼亦平民”一语,意义更为深刻、丰富。这些,在当时诗人集中,是不多见的。可惜此类诗歌在德潜集中也不多见,且都是作于康熙年间。雍正以后,特别是德潜出仕以后,其所作诗中,此类诗就几乎没有了。
德潜诗中最多的,是有关社会教化的诗,也就是行“诗教”的诗。当然,这些诗歌的思想感情,一以儒家思想观念为准则。扬忠倡孝之诗,时人集中,总有若干首,以装点门面,而德潜集中尤多。特别是扬忠者,于张巡、岳飞、文天祥、于谦,一直到明末清初的抗清英雄史可法、侯峒曾、侯歧曾、阎应元、陈明,他一一谒祠吊墓,系之以诗,表彰他们的忠烈。
不过他是站在清王朝立场上来发议论的,出仕以后,尤是如此。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将“忠”抽象化。凡是涉及明清之际者,否定或忽略其具体的历史意义,只是将“忠”作为一种抽象的道德观念来颂扬。出仕以后所作,尤是如此。例如,《馀集》卷四《江阴二忠祠》将清初领导江阴百姓抗清的明典史阎应元和陈明说成:“桀犬吠尧存志节,”又说:“暨阳许续睢阳烈,圣代旌扬肃豆笾”。
这与清统治者表彰史可法等人,配合得如此紧密。二是将忠僵化、愚化。他后期所作《谒汤阴岳侯祠》云:“狱成三字臣何怨,代隔千秋众不平。
”被以“莫须有”罪名铸成如此冤狱而竟然无怨,历史上的岳飞,恐怕未必如此。德潜愚化岳飞之忠,跟统治者之意正好相合。他在康熙年间所作《岳鄂王墓》云:“千秋见孤愤,认取向南枝,”见《竹啸轩诗钞》卷六。
同吊岳飞,是如此的不同,其间原因,不难明了。德潜倡孝之诗,有《梁父吟》、《慈乌叹》等。一些与忠孝不合的古代名篇,他也不厌其烦地改作。如其《履霜操》自序云:“《琴操》有《履霜》,原词实多怨怼,非以教孝也。予特拟其词云”。又《种瓜篇》自序云:“陈思王《种葛》、《蒲生行》、《浮萍》等篇,文藻有余而怨怼或甚,似非风人之旨,因拟是篇。”《美女篇》也是如此。
提倡忠孝以外,其他“正风俗、理人情”的诗很多。如《旃檀林》劝女子不要出家:“人生有伦理,空用朝法王。寄言世间女,终身只合守闺房!”《禽言》之《婆焦饼》、《姑恶》,就婆媳关系而发。《田家杂兴》中,知足达观,乐天知命,不争值,无机心,睦邻居,勤劳作,尚简朴等等的观念,一一以形象发之。
人们的种种不满,不如意乃至怨气怒气,他都在诗歌中予以疏导,使一归于平和。封建社会中,贪官污吏横行,对贪官污吏的怨怒仇恨,是百姓和知识分子中极为普遍的感情。
然而,其《吏胥》云:“吏胥如虎狼,秉性在吞噬”,又云吏胥之凶恶远过虎狼,且云:“官能吏亦能,如指臂使器”,把矛头由吏胥而直指官。然而,结尾云:“民俗渐凋伤,天心自仁爱,驺虞得天心,仁风被草莱。
不须用殄戮,久久化丑类。虎狼亦回心,共庆民攸暨”。叹租税之重,于农民是常情常事。其《观刈稻了有述》云丰收之年老农叹“半输公家租,半偿私家责。”诗人责老农:“隐食天地德,乃敢生怨咨?”那些水旱之灾严重之处,百姓困苦,“尔曹刈获余,饱食息忧虑。
”“吾生营衣食,而要贵知足。”于是“老农闻我言,自贺福有馀。岁岁愿复然,老死安耕畲。”老老实实适应这样的现实。在这方面,所谓“诗教”,实在与佛教没有多大的本质差别!
德潜论诗主新意,但是其诗中的新意极少。有的所谓新意,实在新得陈腐。如云如果扶苏当皇帝,秦就不容易灭亡,因此张良遣死士击秦始皇不中,乃是天意欲亡秦之故。又如《王昭君》云:“君王不好色,遣妾去和亲。”就史事而论,确实新得出奇,但是就观念而论,则未免太陈腐了。
在艺术表现方面,德潜诗歌最大的特点是好用比兴寄托,故其诗歌大多含蓄蕴藉。这正与他的诗歌理论相合。《竹啸轩诗集》卷一《悲歌》云:“莫以琏瑚器,持向田家叟;莫以宫中妆,夸示下里妇。瑟不如竽,抱此焉徂?仰天而歌,其声呜呜。
歌声呜呜何太悲,烈士壮年力就衰!”此乃科场失意之作,怨愤悲慨之情,以一连串比喻出之。当时德潜仅28岁,他还没有形成“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理论,词气不免激愤,而能以比兴出之。
同上卷二《新嫁娘》云:“未熟姑心性,但闻姑最贤。爱姑如爱母,妾自得姑怜。”此当从唐人王建诗“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化来。其旨远不限于婆媳关系,乃言臣工之于君主,下属之于上级,当修忠修敬,克尽在己者,亦即《孝经》移孝悌于忠君顺长之义。
又《枯鱼过河泣》云:“鲂鲤入肆,其目不闭。寄语河中鱼,市价方腾贵。”此乃不幸受害者告戒同类,或为《南山集》案而发。所有这些,不管是否有所特指,但是意蕴丰富而广泛,又有含蓄之妙。
德潜五言诗,学汉魏和晋之陶潜,唐之杜甫,佳作如《塘上行》、《拟古》、《古风》、《田家杂兴》、《田家》、《泛碧浪湖泊道场山下》、《夏日田居杂兴》等。《拟古》诸篇,明显仿《古诗十九首》。乐府或拟乐府小诗学汉魏,甚至汉魏谣谚,如《陇头流水》、《禽言》、《补禽言》、《企喻歌》等即是。
如《稽古》云:“稽古秀才不知书,帝字认作虎。”又《咄咄怪》云:“咄咄怪,东家儿郎太狡狯,眼中不见丁字形,腰间取印如斗大,咄咄怪!”则纯然是古民歌民谣。
德潜七言古诗。多杂长短句,绝少律句,主要学李白,兼及杜甫。如《黄山松歌》、《狂歌行》、《妙空岩观日出歌》、《赋得罗浮山》、《黄山看云海歌》、《登文殊台作歌》、《天都峰》、《登光明顶放歌》、《华顶观日月同渡》等,明显学李白。也偶尔有学苏轼者,如《琵琶引赠仇青君》等。
德潜律诗学杜甫,较胜者,乃登临怀古诸篇。如《北固山怀古》、《过真州》、《金陵咏古》、《望岳》、《平靖关》、《张中丞庙》、《观音阁》、《等盘山》、《登莫厘峰》、《大风登黄鹤楼》等。兹五律举《平靖关》云:“荆豫分疆处,天然屹此关。
断崖通一线,绝顶控千山。地险风云壮,时清戍守闲。当年龙战日,飞鸟尚难还。”七律举《金陵咏古》之一云:“石头如虎踞岩疆,鼎足三分此一方。但恃江流横铁索,不知名将下龙骧。
紫髯空自争荆楚,青盖旋看入洛阳。太息雄图消歇尽,霸才终古忆周郎。”登临怀古,概括古之兴亡,描绘雄奇山川,气象易于阔大,感慨易于抒发。这些诗属对工稳,可见其琢磨之功深。然而新意殊少,感慨亦泛,语多俗调,气象易成空腔。由此入门,固然无可厚非,如果奉为标准刻意追求,遂入绝境。
德潜七言绝句,学唐人王孟一路,欲仿王渔洋神韵诗。《秦淮杂咏》云:“不数回风唱丽娟,怀宁一曲万人怜。家亡国破浑闲事,留得新声《燕子笺》。”与王渔洋《秦淮杂诗》中“细字冰纨”一绝,题材相同,然而情韵不及渔洋婉转深长。
《雨泊话旧》云:“寒雨萧萧夜打篷,篷窗相对一灯红。十年无限存亡感,并入空江话雨中。”则于渔洋庶几近之。或学《竹枝》一类的民歌。如《吴中棹歌》:“官船峨峨来往过,看侬打浆听侬歌。尽日风波共摇荡,不知人世有风波。”颇有言在意外之妙。又《西湖杂句》:“女伴闲行过净慈,金钱暗掷卜归期。鹫峰尚有飞来日,不信狂夫爱别离。”此则几近民歌。
德潜五言绝句,如古绝者,或学古民歌民谣。如《船娘曲》云:“上水侬撑篙,下水侬把橹。尽日风波中,不识风波苦。”颇具哲理。又《企喻歌》:“苍鹰摩高天,不为燕与雀。壮夫出塞行,不为圭与爵。”在当时诗人中,别具一格。一般五绝,亦以含蓄胜。如《王明君》﹕“毳帐琵琶曲,休弹怨恨声。无金偿画手,妾自误平生。〞
德潜之诗,温柔敦厚,丰实朴重,古色古香。尽管所写事绝大部分是当时的事,所抒情也确实是他自己的情,然而观念是儒家的观念,语言是古代诗人的语言,笔法是古代诗人的笔法,甚至题材也是古代诗人常写的题材。
虽然往往能得古代诗人的神理,但是这些神理是属于古代诗人的,毕竟不属于他。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方面,他都很少创新。这固然是学问才力所限,也是他诗歌理论强调溯“诗教之本原”而忽视创新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