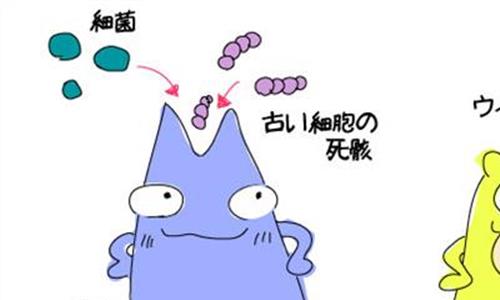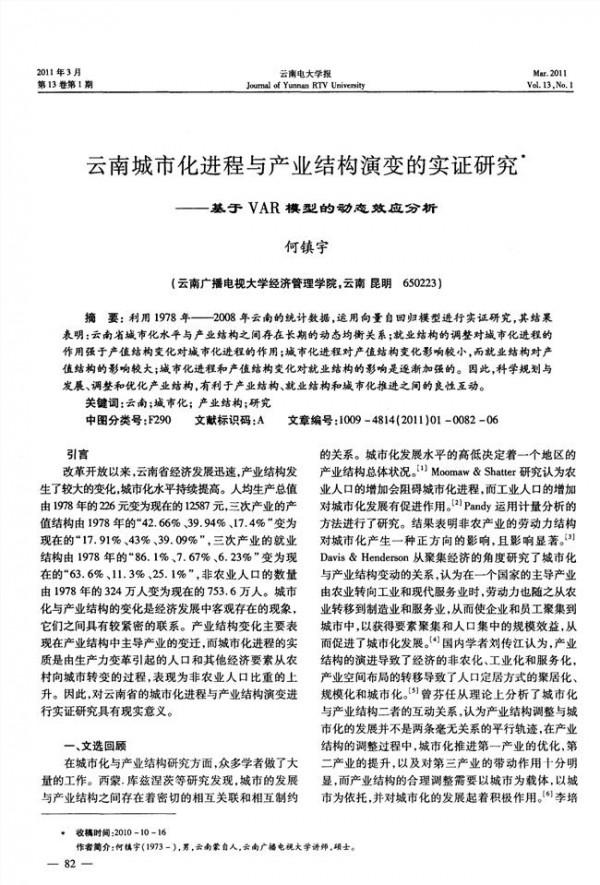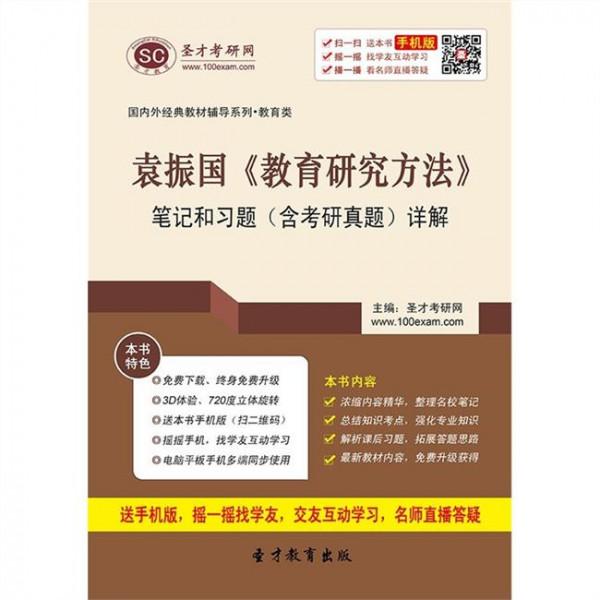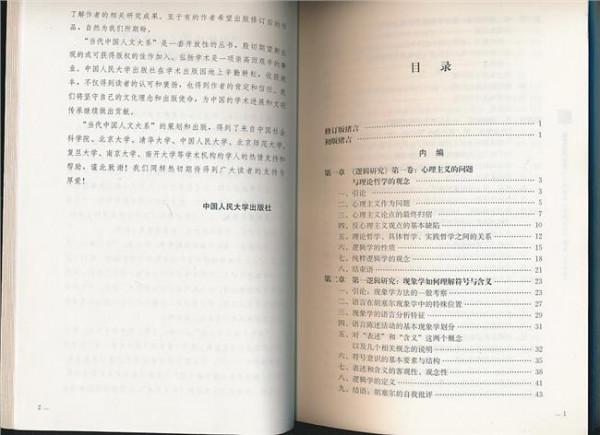邓石如研究 邓石如其人其艺研究
我在编著《鼎甲鸿迹——中国状元书画集》《中国书法的形式与内容》《中国书法通史》时,接触了大量的明清书法家的作品,因为心之所好的原因,特别关注清代的以贴学为主的书法家,尤其是家族书法的演变与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当然因为我对清代的伊秉绶(1754——1815)隶书情有独钟,进而研究伊念曾、伊立勋一家三代的书法,重点收集了他们祖孙三人的书法作品数百幅,特别是一些未见于常见作品集和网络中的新见作品,是把他们编成题为《伊门书风》作品集,拉出清样,以供自己清玩,研习。这样我对清代碑学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邓石如作为碑学的一个开拓者和奠基人,就进入了我的视野。于是我在网络和图书馆寻找他们的书迹,自己编了一本书法集。
目前国内关于邓石如的综合性作品集主要有王家新主编《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和陈振濂编的《日本藏邓石如书法精选》。
邓石如(1743—1805),清代碑学开拓者和奠基人。邓派(亦属皖派)篆刻领军人物、细朱文发展转折人物。在中国书法、篆刻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笈游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安徽怀宁人。
邓石如是清中期享誉书坛的金石书法家。20多岁就赢得书坛理论权威、经学宿儒、金石学家和文坛泰斗的赞誉。他在清代书坛披靡之际,锐意创新,擎起了研习碑学的旗帜,活跃了清代书坛。他的书法特点是五体兼擅,形成了“邓派”书法艺术。
陈振濂在他编的《日本藏邓石如书法精选》的前言中说:清代碑学巨擘邓石如,是一个被当时人誉为“四体书皆国朝第一”的书坛人家。其实“第一”与否,并不值得过份计较。事实上要诸体皆为第一,也有点勉为其难。但邓石如在清中期以一己之力开宗立派、登高一呼,使书法几千年帖学传统风气为之一变,这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与种种可能溢美的“第一”相比,邓石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书法史上的历止人物,他的努力改变了书法的新航向,这也许是一个更高也更贴切的评价。
邓石如出生于寒门,祖、父均酷爱书画,皆以布衣终老穷庐。邓石如九岁时读过一年书,停学后采樵、卖饼饵糊口。17 岁时就开始了靠写字、刻印谋生的艺术生涯,一生社会地位低下。他自己说:“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识字人相待。
”邓石如30岁左右时,在安徽寿县结识了循理书院的主讲梁巘,又经梁巘介绍至江宁,成为举人梅镠的座上客。
邓石如在江宁大收藏家梅镠处8年,“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寒暑不辍”。不久得到曹文埴、金辅之等人的推奖,书名大振。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80寿辰之际,户部尚书曹文六月入京都,邀其同往。秋,途经山东,遂登泰山观览。进京后,邓石如以书法响誉书坛。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两湖总督毕沅处做了3年幕僚。张惠言、包世臣都曾向他学习书法。
邓石如在自述身份时说自己出身寒门,布衣一生。简单看来这种描述没有太大问题,但若细纠则其似乎在说邓石如缺少必要的文化基础修养。这自然是对邓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实际早在其当世即已存在。如邓石如自云:“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识字人相待。
”邓石如于书法辛勤耕耘一辈子,但社会并不把他作为有学问有修养的“识字人”相待。而其实对邓石如出身的准确说法应该是:出身书香门第,幼受庭训,发奋努力,书艺卓绝,为靠书法谋生的职业书家。
邓石如祖父、父均善书画。邓石如的祖父名士沅,字飞万,号澹园,爱好书画。当于寿州当过授课先生。其父名一枝,字宗两,好北林,善诗文,工书画,喜刻石。石如九岁时即被父亲送往私塾读书,虽一年后辍学,但其十三四岁“心窃窃喜书”,已从内心开始喜欢读书作学问,17 岁时就开始为别人作书、刻印谋生,二十岁开始在家乡开设书馆,教授童子,后又随祖父到寿州蒙馆授课。
之后其游走江湖,混迹士大夫达官显贵之间。以上身世经历如何能以“不识字人”观其人呢?
中国社会向以官本位衡量人之社会地位,但至明代,王阳明心学与狂禅的结合汇就中国中世纪自由浪漫思潮的兴起,“满街都是圣人”“我心即佛”“心即理”的思潮成一代风潮,打破了官本位思想的彻底笼罩,加及明末清初朝代更替,民族矛盾等原因,不仅出现了一大批没有官阶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也出现了许多具有独立人格的书画家,如徐渭、傅山、金农、高翔、黄慎等。
邓石如不仅工书法篆刻,而且有《铁砚山房诗抄》传世。因而对邓石如之身份决不能以一句布衣而简单论之。邓石如的布衣是相对于缺乏科举功名而言的,而不是指没有知识和文化。
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的行书《陈寄鹤书》还与历史上一段著名的轶事有关。邓石如家中养两只鹤。据说,这两只鹤的年龄至少有130岁。一日,雌鹤死去了,仅隔十几天后,邓石如的发妻沈氏也相继去世。这种巧合,在当时的文人当中产生了很多联想。
59岁的邓石如伤心至极,雄鹤也孤鸣不已,与他相依为命。因不忍再看孤鹤悲戚的样子,邓石如于是择地三十里外的集贤关佛寺,将鹤寄养僧舍中。从此,他担粮饲鹤,三十里往返,每月坚持不懈。忽然,又一日,正在扬州大明寺小住的他得到传报,雄鹤被安庆知府看中,抓回了府中。他即刻启程赶回安庆,用行书写下了《陈寄鹤书》向知府陈情上书索鹤。
这篇文章写得哀婉动人,催人泪下,气势排山倒海,文辞如云幻天,以极尽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历数得鹤、寄鹤悲欣往事。为了这只鹤,他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正如书中所写“大人之力可移山,则山民化鹤、鹤化山民所不辞也。
”知府接书,无言以答,不日将鹤送还佛寺。从此,与鹤为伴,晨昏无间。邓石如死时,那鹤发出尖厉的唳声,哀鸣数日后,打了一个旋,消失在大漠青空之中,羽化而去。鹤唳、青空、远去——这是我心头漫过的图景,也是眼前流过的诗境。
是的,一袭布衣,仰视苍天,有所牵挂而来,无所牵挂而去;既知万物有灵,更轻身外之物;“你自归家我自归”——人鹤两化,只留下一段聚散情义于古今。他的好友、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曾给他写过这样一幅对联:茅屋八九间钓雨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
不慕富贵而自然隽永,不闹情绪而旷达平和。钓雨耕烟,灌花酿酒的人生,洗去的是庸脂俗粉,尘泥污垢,浸润出来的却是经史子集里的书卷气质和一身的仙风道骨。于人,互为表里,安身立命,也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人生一达这种境界,艺术的深沉和久远便应运而生。
邓石如9 岁随父读书,1 0 岁便辍学,1 4 岁“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然在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对书法、金石、诗文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并有长足进步。1 7 岁时,为“潇洒老人”作《雪浪斋铭并序》篆书,即博时人好评。自此,便踏上书刻艺术之路。2 0 岁在家乡设馆,任童子师,不耐学生“憨跳”而舍去,随父去寿州(今寿县)教蒙馆,2 1 岁因丧妻辞馆,外游书刻,以缓悲痛。
乾隆三十九年(1 7 7 4 年)他3 2 岁时,复至寿州教书,并常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和以小篆书写扇面。深得书院主讲梁献(亳县人,以善摹李北海书名于世)赏识,遂推荐他到金陵(今南京)举人梅谬家学习。
梅家既是宋以来的望族,又是清康熙御赐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家藏“秘府异珍”和秦汉以后历代许多金石善本。石如纵观博览,悉心研习,苦下其功。在梅家8 年,前五年专攻篆书,后3 年学汉分。于四十七年他4 0 岁时,离开梅家,遍游各处名胜,临摹了大量的古人碑碣,锤炼了自己的书刻艺术,终于产生了“篆隶真行草”各体皆备、自成一家的大量作品。
乾隆四十七年,他游黄山至歙县,结识了徽派著名金石学家方君任和溪南经学家程瑶田,及翰林院修撰、精于篆籀之学的金榜。
后经梅谬和金榜举荐,又结识了户部尚书曹文埴。 乾隆五十五年秋,弘历八十寿辰,曹文埴入都祝寿,要邓石如同去,石如不肯和文埴的舆从大队同行,而戴草帽,穿芒鞋,骑毛驴独往。
至北京,其字为书法家刘文清、鉴赏家陆锡熊所见,大为惊异,评论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后遭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代表的书家的排挤,被迫“顿踬出都”,经曹文埴介绍至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源节署(署武昌)作幕宾,并为毕源子教读《说文字原》。在署三年,不合旨趣,遂去。
乾隆五十九年他5 2 岁时,由武昌回故里,买田4 0 亩,翌年建屋一栋,并亲书匾额“铁砚山房”置于门首。常将书刻售资救济乡人,贫不能葬者,都尽力资助。以后的1 0 年,他的书刻艺术越臻化境,他不顾年迈,常游于京口(今镇江)、南京、扬州、常州、苏州、杭州等地。
临终前一年,还登泰山,会晤友人,切磋技艺。6 0 岁时,他游京口,结识包世臣,授书三年,并以书法要诀示曰:“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
”包以其法验六朝之书都全符合。他6 3 岁临终这一年,仍收录门生程蘅衫,为篆书《张子西铭》。 是年,得知泾县有八块碑需以大篆、小篆、分书、行楷各体书写,慨然应邀,仅书一碑因病而归,阴历1 0 月卒于家。
邓石如身材高大,胸前飘一绺长长的美髯,遇人落落,性格耿介,无所合,无款曲,无媚骨,无俗气,称得上顶天立地的一个伟男子。
因为其祖辈出身寒微,枯老穷庐,他的一生更备尝人间的酸甜苦辣,过着“采樵贩饼饵,日以其赢以自给”的生活。他以“山人”自居,于荒江老屋中高卧,把功名两字都忘记了。
为什么淡泊如此?他生活的时代,是历史上堪称盛世的“乾嘉时代”。他来到这个世界时,政局早已稳定,天下亦早已被爱新觉罗氏那双射雕射虎的手抚摩得比较熨帖了。生活随着时间的河流,日复一日地平静地流去。我们只知道他戴草笠,着芒履,策毛驴,浪迹天下名山大川,有如云水之间孤独的浮鸥。
他的好友师荔扉曾经送他这样两句诗:“难得襟怀同雪净,也知富贵等浮云。”看淡了浮华、浮夸、浮名,也就与浮躁相去甚远。“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那种怀才不遇的牢骚他没有;“患名之不立,患年之不长”,贾逵的雄心进取他缺乏;“名飞日月上,义与风云翔”,李白的济世大志他也不具备。
他只是归于淡,把世间万物都看得淡了,淡到自甘寂寞,远离红尘。
可是,他又真正地热爱着书法,一天也舍不得丢弃。每日清晨,他研一盘满满的墨水,就着净几挥洒,必待墨水用干了才上床休息。所谓“热爱”,在邓石如的人生里,除了出身寒微,饱受生活的煎熬以外,还得把功名利禄置于脑后而全身心地投入艺术的艰苦锤炼中。他不怕板凳一坐十年冷,更不愿像现在的某些“名人”那样热衷于今天上电视,明日登报纸,后天获大奖,不然就日子一天也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