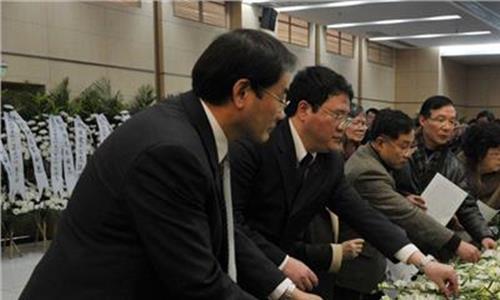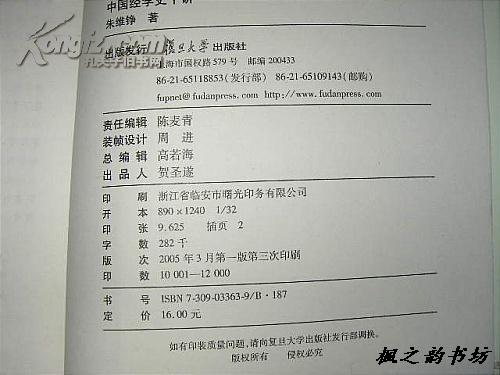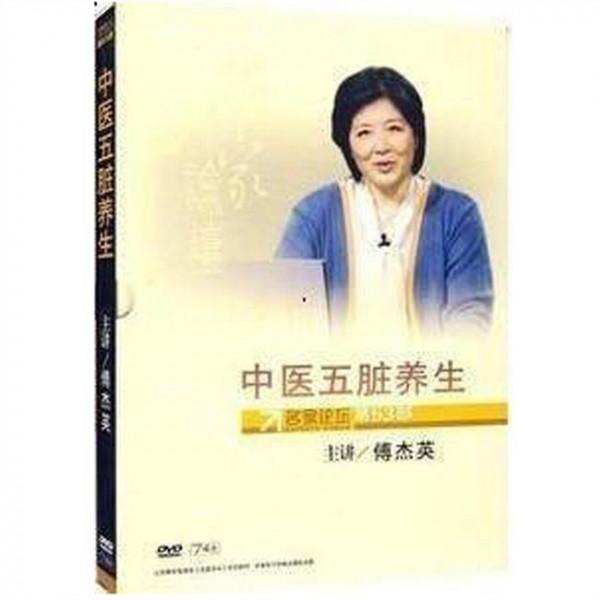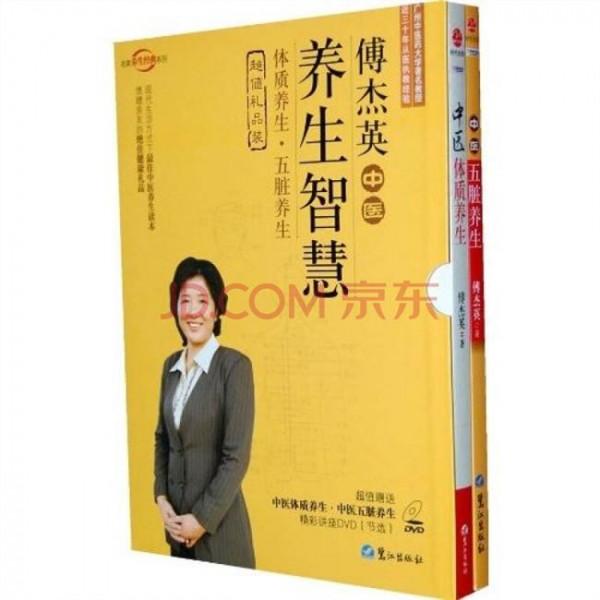重读近代史朱维铮 傅杰:忆朱维铮先生
朱维铮被公认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
朱维铮著述很多,生前分散在多家出版社出版。2018年初,中信出版社获得先生著作的大部分出版权,这是朱维铮著述首次有规模集中出版。

本报特编发著名学者傅杰先生的回忆文章,以为纪念,以飨读者。
第一次见面没说上话
第一次见到朱先生是1986年6月。
当时我是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浙江从省政协到杭大等多家单位联合举行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我的导师姜亮夫先生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在沪上又问学章门,我去参与会务。

那次并没有跟朱先生说上话,只记得他的报告是论晚年章太炎的。他闭着嘴都不是混在人堆里就找不着的主儿,何况开了口?所以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持论则精悍有力量,模样则凛然有傲色。
硕士毕业后,我留在古籍研究所担任亮夫师的学术助手;同时应郭在贻师之命,接任他在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训诂学课。当年的学生、现在已是浙江大学中文系文献专业负责人的陈东辉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在课堂上向他们推销《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并说虽然二书后出的版本甚夥,但他现在给学生首荐的,也还是朱先生的校注本。
“维铮”是王元华先生常提起的名字
再见到朱先生,已是六年后了。
1992年秋,由亮夫师推荐,我到元化师兼职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成为元化师最后一个博士研究生——而朱先生正是“王府”里常见的座上客。
“维铮”是元化师经常挂在嘴边的名字。比如正谈着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元化师会突然插进一句:“这个可能维铮不一定同意。”
不知远在复旦、没准还在国外的朱先生会不会顷刻间耳根发烫?
一天元化师告诉我:有友人打来小报告,称朱先生在外扬言:上海也就是王元化还可以谈谈。“这个朱维铮!我跟他说:你爱怎么得罪人我管不了,你别把我带进去啊!”
语气是嗔怪的,但元化师的笑容却灿烂之至。跟朱先生一样,元化师当然也不是怕得罪谁的人——他的得意是显而易见的。
被弟子气得蹦出国骂
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出类拔萃者的比率不到百分之三。教了大半辈子书、培养名士无数的名师朱先生面对学生,也有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位女博士生——朱先生窝心时抱怨是“我出国时他们给我弄进来的”,为人聪明,但志与力都不在史学,人脉广活动就多,读书少基础就差,老师一再敲打精疲力竭,学生遍体鳞伤依然故我,以致老师一提起学生血压就高,学生一想起老师心里就抖。
朱先生每周三下午上课,跟那位女生同宿一舍的章培恒先生的博士生爆料:“太可怜了,她每到周一就开始脸色发白,嘴唇发青,等周四才会红回来。”
一天下课,朱先生跟我推着自行车回中心村,言及这位低足,气不打一处来: “我让她交开题报告,她千方百计躲着我,实在躲不过了,今天就交给我这么皱巴巴的一张纸。”
他一手握车把,一手从搁在车兜的包里摸出一张真的是皱巴巴才写了大半页的信笺。气急败坏之下,连着蹦出两声国骂。
洒脱自如的文人风骨
林语堂说牛津学生的学问都是导师用香烟熏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朱先生的学生享受到的待遇直逼牛津。
吞云吐雾的架势跟朱先生的满腹经纶、挺拔身姿与自信神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没见过一个比他更有风度的边抽烟边讲课的教授。
上研究生课朱先生不带讲稿,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他边抽烟边漫谈,虽然海阔天空,但却不枝不蔓——这是大半生修炼成的境界。
这样讲半年,讲一年,自然不可能没有失口的时候。
有一天他提到颜之推的观点,一时口误,所述与《颜氏家训》正相反。下课我又跟他推着自行车回家,我一提你刚才讲到颜之推如何说,他就反应过来了:糟糕,我弄反了。
一周后再上课,内容顺流而下,而中间自然回溯到前一次的时,他又提到《家训》:“上个礼拜我把颜之推的意思讲反了,傅杰给我指出来的。”
某次开会,有位自然科学家言辞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文科的轻视,朱先生忍无可忍了:“你不要以为在国外帮人涮了几年瓶子就了不起,我告诉你:你出去是学人家,我出去是人家学!”
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朱先生和师母结婚后,生活才算走上正轨。在师母无微不至的悉心照顾下,朱先生的晚景是幸福的。
而幸福总是短暂的。
这是2010年4月24日——离朱先生被查出绝症,只不到一百天了。手术后的一个傍晚,我去肺科医院看他。他的虚弱是显而易见的,他对术后生命重新开始的信心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信心到后来才被逐渐击碎。
他从床边取出新鲜出炉的《重读近代史》,像以前的每本书那样,一笔不苟地签上“傅杰兄正”,说书编就有日,序却拖着没写:“来这里前一天,我想这下子一进去不知道还出不出得来,不好再拖了,用了一个晚上,到早上七点总算改完。九点就进来了。”
我借机进谏:出院不能再抽烟了。
“除非我以后不工作了。”他本能地拒谏,随即带着一种盗光了国库却逃脱了法网的成就感炫耀道:“来这里前一晚弄这篇序,我还抽掉了两包烟!”
脸上又一次浮现出“贼忒兮兮”的朱式微笑——只是这次笑得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