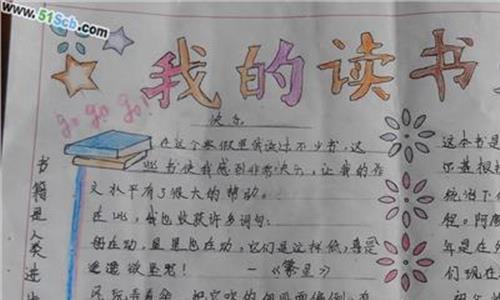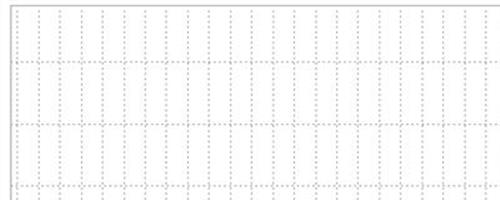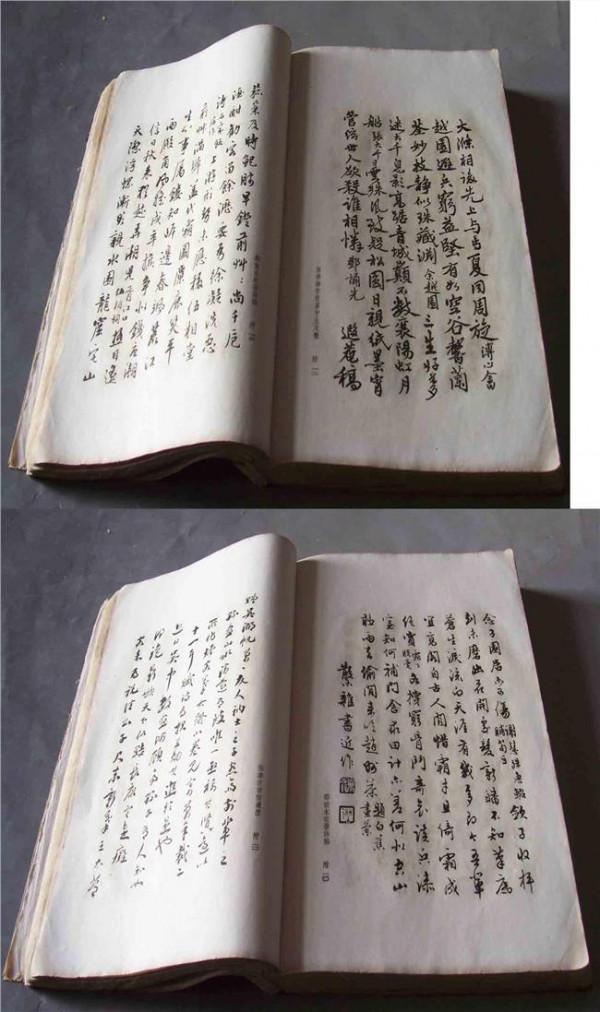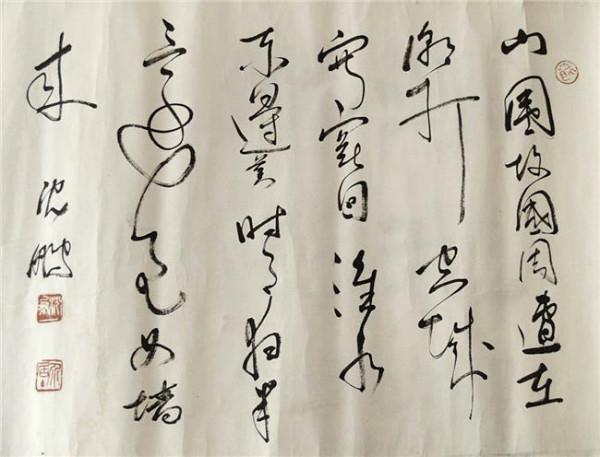沈石溪的书免费阅读 【少年文艺】沈石溪罪马(下)
正打得不可开交,娄阿甲闻讯赶到,与屠清霞一起,用木棒和马鞭将双方分开。娄阿甲很了解眉心红的德性,晓得又是它在寻事生衅,给它套上结实的缰绳,紧紧拴在柱子上,左右开弓挥动马鞭,咬牙切齿叱骂:“你这匹劣马,你这个孬种,看你还敢惹是生非!”

细长马鞭像条黑色灵蛇,饥渴地舔吻眉心红的屁股。白毛飞旋,肌肉饱满的臀部爆起一条条红蚯蚓似的血痕。缰绳放得极短,马嘴几乎贴在柱子上了,这种拴马方式,就像把犯人五花大绑了,使受鞭笞的马无处躲藏。眉心红撕心裂肺地呜叫,四只马蹄胡乱踢踏,围着柱子小范围避闪,却根本不管用,马鞭仍雨点般落到它身上。黑色的马鞭被血染红,马的嘶鸣声渐渐嘶哑。娄阿甲打累了,这才罢手。

整整一个星期,眉心红只能瘸着腿走路。这顿暴打打掉了眉心红的威风,挫败了眉心红的锐气。它进食时再也不扭头抢夺白珊瑚食槽里的草料,到了训练场上,也不再调皮捣蛋恶作剧,而是服服帖帖地听从白珊瑚的调遣。
野心家脱胎换骨变成了驯服的良民。可突然间,白珊瑚竟做出明显姿态,要把头马位置禅让给眉心红。禅让者,即用和平方式无条件地将王位奉送给继承者。
那是在白珊瑚停止绝食后的第三天,屠清霞吆喝马队前往训练场。同以往一样,白珊瑚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另五匹白马跟随其后。刚走出马厩,进到狭窄的花园甬道,白珊瑚扭头望望紧跟在它身后的眉心红,突然朝旁边跨了一大步,挤到花坛的墙根下,停了下来。
按照惯例,头马停了下来,后面的马也都驻足观望。白珊瑚眼睛盯着眉心红,马头不断朝前晃动,做出一种谦让姿态,似乎是在告诉眉心红:我已经让出路来,请你先往前走吧。
眉心红瞪起警惕的眼睛,不仅没有朝前走,反而往后退缩了一步。
咴咴,白珊瑚柔声嘶鸣。声音也是一种信号,表达出友善的态度。它再次往花坛墙根边靠,让出更宽敞的路来,示意眉心红走到前面去。
眉心红举蹄欲往前走,才跨出半步,马蹄刚刚落地,却又像踩着火炭似的缩了回去。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还是小心为妙。
六匹高头大马拥挤在狭窄的花园甬道,堵塞了交通,屠清霞不知发生了何事,在后面大声叫唤,催促马队快往前走。
白珊瑚显得很焦急,用马嘴叼住眉心红的鬃毛,往前拉扯。眉心红咴咴叫着,身不由己往前蹿出两步,走到马队最前列去了。白珊瑚紧跟其后,用额头抵着眉心红的屁股,推搡着它往前走。
眉心红走两步就要扭头往后看一眼,生怕白珊瑚趁机咬它的尾巴或啃它的臀部,走得提心吊胆,走得心惊肉跳。其实,它的担心纯属多余。白珊瑚像个本分的臣民,规规矩矩跟随在它身后,走得踏实稳健,丝毫也没有要捉弄它的意思。
到了训练场,这天是温习一个名叫“马步迪士高”的老节目。录音机播放摇滚音乐,六匹白马排成前一中二后三的三角队形,跟着音乐翩然起舞。这三角队形,是根据马的地位和舞蹈水平来排列的。白珊瑚是头马,迪士高跳得也最棒,理所当然站在三角队形的尖端。
眉心红舞跳得也挺好,在马群中的地位仅次于白珊瑚,所以排在中间左侧位置。蓝宝贝的舞艺在马队排名第三,站在中间右侧位置。其余三匹白马,分别站在最后一排。这个节目已经上台演出过,无非是温故而知新。六匹表演马都晓得自己在这个节目中所扮演的角色,音乐一响,不用驯兽员吆喝拉拽,便各自走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很熟练地排成三角队形。
屠清霞刚要挥动小红旗以示训练开始,突然,白珊瑚扭头离开了三角队形的尖端位置,朝左拐来到眉心红身旁,用身体将眉心红挤撞开。眉心红咴咴嘶鸣,仿佛在埋怨:你占据了我的位置,那我站到哪里去呀?白珊瑚马头耸动着,不断朝三角队形尖端位置点头示意,用肢体语言明确表达这么一个意思:请你站到领舞的位置上去吧。
眉心红偷偷瞟了三角队形尖端位置一眼,眼神暖昧,既有几分窃喜,也有几分胆怯。那里既是领舞者的位置,也是公认的头马位置。它早就渴望能登上头马宝座,可上次权力争斗留给它的教训太深刻了,至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它不敢做得太露骨。 两匹马在那儿推让挤撞,当然会影响训练正常进行。
屠清霞不得不来到白珊瑚身边,抚摸光滑的马脖子,指着三角队形尖端位置说:“你是头马,这个节目一向由你领舞的,你应该站到那儿去!”说着,她牵拉白珊瑚的辔嚼,想把它拉到领舞者位置上去。让她惊讶的是,白珊瑚四只马蹄像生了根一样,怎么也拉不动它。
“你究竟想干什么呀?”屠清霞厉声发问。
白珊瑚马头抵住眉心红的腰,一个劲往三角队形尖端位置推搡。
“你是想让眉心红代替你领舞?你是在犯傻,还是在犯贱?我没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再不肯听话,我可真的要让眉心红站到头马的位置上去了哟!”她拉住眉心红的辔嚼,试探着往三角队形尖端位置拉,观察白珊瑚的反应。
白珊瑚娴静地站立着,对她动手把眉心红拉往领舞者岗位,没有任何反感的表示,恰恰相反,那双马眼温柔地望着她,似乎在鼓励她去这么做。
当眉心红站到领舞者岗位后,蓝宝贝发出愤怒的嘶鸣,并扬鬃踢蹄摆出一副厮斗的架势。白珊瑚立刻跑拢过去,朝着蓝宝贝的耳朵严厉嘶鸣一声,用自己的脖子压在蓝宝贝额头上,用力将蓝宝贝气势汹汹高昂的马头压得低垂下来,其实也就是把蓝宝贝不满的情绪给压制下去。
然后,白珊瑚又跑回三角队形第二排左侧位置,很规矩地站立待命。 眉心红被屠清霞牵拉着,进两步退一步,似乎也不愿被牵到领舞者位置上去,扭拧马头做出抗拒的姿态,忸忸怩怩欲走还休,最终却半推半就走到三角队形尖端位置。
“那好吧,就由你来领舞!”屠清霞气呼呼地拍着眉心红的背脊说。
眉心红扬起脖子咴地发出委屈的嘶鸣,仿佛是在向马群声明:不是我要篡夺头马的领舞权,大家都看清楚了,我身不由己,是主人逼我这样做的!
它虽然马耳耷拉,马嘴翕动,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可马眼活泼地转动,马尾巴不停地左右挥甩,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得意。
公平地说,由眉心红来领舞,也未尝不可。在这六匹马中,眉心红的地位仅次于白珊瑚,从演技来说,眉心红虽然没有白珊瑚那么熟练,那么富有舞台经验,可它年纪轻,身体更高大健壮,皮毛更有光泽和弹性,也更有青春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
训练开始了,眉心红跳得很卖力,精神抖擞,激情澎湃。它迪士高本来就跳得不错,马逢喜事精神爽,第一次登上头马宝座,梦寐以求的事变成了现实,踏破铁蹄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所以舞姿格外优美,发挥得特别出色,领着五匹白马一口气跳了六支曲子,没有出现任何纰漏。而白珊瑚望着前面的眉心红,跟随着音乐的节奏,亦步亦趋,认认真真跳完每一个曲子,就好像它从来没做过头马。
这让屠清霞感到迷惑不解,只听说过马群为争夺头马宝座闹得不可开交的事,却从没听说过有哪个马群哪匹头马会主动将头马宝座禅让给属下的臣民。
这种行为,完全不符合马的物种特性。屠清霞心里隐隐不安,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向高导演作了汇报,希望高导演能帮她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高导演皱起眉头沉思了一阵,说:“孤立地看,这确实很奇怪。可如果把这件事放在大半年前娄阿甲意外身亡的背景下去分析,白珊瑚的禅让行为还是可以理解的。它一直怀着深深的内疚,认为自己不配再当马群的头马,类似于引咎辞职。
哦,你说它的马眼里有一层淡淡的忧伤,还说它喜欢伫立在西南角眺望哀牢山黑虎冢方向,这说明,它至今还未能从事故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心力交瘁,身心疲惫,已无力再承担头马的职责。”
“高导演,你分析得有道理。”屠清霞信服地点点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是要顺手推舟让眉心红当头马,还是设法维持马群的原有秩序?”
“与动物打交道,很多事情,顺其自然要比人为干预好得多。”高导演微笑着说,“白珊瑚已经十三岁多了,生理年龄和艺术生命都快要走下坡路了。眉心红牙口六七岁,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身体素质和马技表演都是第一流的,让它当头马,也未尝不可啊。”
“那好吧,我就顺其自然。”屠清霞说。
没想到,白珊瑚会舍得把蓝宝贝踢倒咬伤。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天是周末,下午三点左右,屠清霞领着马队到剧场去走台。
按节目表上的程序,马队第一个节目是障碍跑。在狭窄的马戏场地,竖立起三道一米五高的栏杆。马队兜圈跑动,不断跨越栏杆。
眉心红站到头马的位置,引颈抖鬃,向马群示意表演就要开始。
白珊瑚站在马队第二位,对眉心红行使头马职责并无任何异议。
屠清霞做了个可以开始的手势,眉心红刚要扬蹄奔跑,突然,排在第三位的蓝宝贝从队伍里蹿了出来,咴咴激烈地嘶鸣着,直奔马队最前面的眉心红。它鬃毛竖立,漂亮如蓝宝石的马眼里布满血丝,到了眉心红面前,昂首挺胸,不时身体后仰抬起前肢做出踢蹬姿势,很明显,这是一一种威逼挑衅行为,目的也很清楚,是要叫眉心红从头马位置上滚蛋!
眉心红立刻也竖鬃弹尾,身体蹿挺,两只前蹄在空中踢踏,摆开应战架势。可它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扭头望了白珊瑚一眼,收敛打架的姿势,跳闪到旁边去。
蓝宝贝迅速走到马队最前列,取而代之站在头马的位置上,发出长长的嘶鸣,仿佛在向天下发布告示:我是头马,这群马归我统辖了!
不难理解蓝宝贝的行为,它是匹牙口四岁半的公马,就像所有的雄性动物一样,渴望建功立业,渴望出“人”头地,渴望获得优越的社会地位。白珊瑚做头马,顺理成章,它当然拥戴。可白珊瑚几次三番要把头马宝座禅让给眉心红,它实在看不下去了。
既然白珊瑚要把头马宝座让出来,干吗就不让给它呢?它是白珊瑚的亲生儿子,血缘亲情,王位相袭,母亲把头马宝座禅让给儿子,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它已经是顶天立地的大公马了,就像野心家通常都很狂妄一样,它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比眉心红差,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坐上头马宝座6
走台还没开始,马队却陷入争权夺利的混乱中。
屠清霞气呼呼地跑过来,用拳头擂蓝宝贝的脖颈,嚷嚷道:“滚开!你有什么资格当头马?你年纪比眉心红小,演技比眉心红差,你做了头马,没有一匹马会服气的!让你坐马队第三把交椅,已经是很抬举你了,你应该有点自知之明嘛!”
无论屠清霞怎么骂怎么打,蓝宝贝就是占据着头马位置不肯退让。眉心红打着愤懑的响鼻,鬃毛恣张,马尾耸动,内心已怒火万丈。它不断乜斜眼睛看白珊瑚,很显然,假如白珊瑚允许的话,它会立刻冲上去与蓝宝贝恶斗一场。
白珊瑚似乎也识破眉心红的意图,咴地发出威严的嘶鸣,毫不迟疑地向蓝宝贝靠近一步,这等于在警告眉心红: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敢伤害蓝宝贝的话,我跟你没完!
眉心红高涨的斗志迅速萎瘪下来,鬃毛与马尾软软耷拉,悻悻嘶鸣着,转身跑开去。
蓝宝贝有白珊瑚替它撑腰,气焰更嚣张,在头马位置上欢蹦乱跳。
白珊瑚低头沉思了约半分钟,缓缓走到蓝宝贝身边,长长的马脖子柔软弯曲,就像高级技师在做人体按摩一样,在蓝宝贝身上轻轻摩挲。马是一种需要爱抚的动物,养过马的人都知道,天天用梳子替马梳毛,是增进人与马感情的最佳方法。
白珊瑚摩挲得非常仔细,四肢、臀部、腰胸、背脊、肩胛、脖颈及马头上的五官,统统摩挲了一遍。然后,它脖子贴着蓝宝贝的脖子,身体挤着蓝宝贝的身体,似乎要把蓝宝贝从头马位置推搡开去。
蓝宝贝站立不稳,朝旁边闪了两步,它不满地咴咴嘶叫,侧转身用力顶撞,又顽强地回到头马位置上。
白珊瑚仍用慢慢推挤的方法,要蓝宝贝离开这个位置,马嘴不停地咴咴哼哼,似乎在用马的特有语言劝告对方:我的心肝,你太年轻,资历和演技都不足以服众,听妈妈的话,回到你自己的位置上去,别胡闹了!
可蓝宝贝根本不把白珊瑚的忠告当回事,它唰地转过马头,来啃咬白珊瑚的脖子,白珊瑚只有跳闪躲避。它冲着白珊瑚长长嘶鸣一声,似乎在说:谁也别想动摇我登上头马宝座的决心,谁阻拦我,谁就是我的敌人!
白珊瑚退离蓝宝贝身边后,低着头马嘴贴着地面,像是在寻找可以啃食的青草,慢慢踱到蓝宝贝的侧后位置,马尾与马尾形成一个九十度夹角。它的眼睛蒙着一层悲哀,身体也在微微发抖,似乎很伤心也很绝望。
蓝宝贝仍神气活现地站在头马位置,四蹄不断踢蹬,急不可耐想要履行头马职责率领马群表演障碍跑节目。
眉心红咴咴引颈嘶呜,始终摆着讨伐叛逆的架势。
其余三匹白马,马心惶惶,挤在舞台边缘,不知该如何是好。
就在屠清霞左右为难不知该如何是好时,突然,白珊瑚勾紧脖子,鬃毛唰地竖立,两条前腿肌肉刹那间绷紧,腰弯成弧形,两只后蹄凌空飞起,做了一个非常漂亮非常标准的尥蹶子动作,啪的一声,两口、马蹄不偏不倚踢在蓝宝贝左侧臀部。白珊瑚动作迅疾,事先没有任何预兆,蓝宝贝根本没有防备,一下被蹬翻在地,摔了个四仰八叉。
两匹白马在翻腾,犹如一场小型雪崩。
马尥蹶子,是马抗击敌害最厉害的绝招,曾有人计算过,一匹体格强健的马,尥蹶子所产生的冲击力,超过一千磅。国外有一位动物学家在非洲草原曾亲眼目睹这样一件事,一只雄狮追逐一匹斑马,当狮爪就要抓住马屁股的瞬间,那匹斑马突然尥了个蹶子,两只马蹄蹬在狮子下巴上,雄狮当场被踢晕过去,那匹斑马趁机逃之天天,十几分钟后,倒霉的雄狮苏醒过来,下巴开裂,无法嚼咬吞咽食物,数日后活活饿死。
马戏剧场里所有的马都被白珊瑚的举动惊呆了,泥塑木雕般地站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来。
屠清霞也惊得目瞪口呆,要不是亲眼看见,她决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最震惊的当然是蓝宝贝了,它被蹬倒在地了,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扭着脖颈咴咴嘶鸣,仿佛在责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躺在地上了呀?
白珊瑚尥蹶子把蓝宝贝蹬翻后,仍不肯罢休,鬃毛恣张,恶狠狠冲将过来,张嘴咬蓝宝贝的脖子。
蓝宝贝这才如梦惊醒,明白是白珊瑚踢倒了它,而且还要啃咬它的脖子,惊讶的咴叫声变成悲愤的嘶鸣,一面竭力挣扎想重新站起来,一面扭动脖子躲避凶猛的啃咬。
屠清霞赶紧冲上去,抱住白珊瑚的脖子,强行把它拉开。
这时,马戏团几位驯兽师闻迅赶了过来,在好几个人的帮助下,蓝宝贝才颤巍巍勉强站了起来,左臀被蹭掉一片白毛,肿得像块发糕,布满乌紫的淤血,走路瘸瘸拐拐,看样子伤得不轻。
蓝宝贝被牵到兽医站去敷专治跌打损伤的草药了,一场风波就此平息。屠清霞把马候补演员雪姬牵来剧场,替代蓝宝贝。白马们各就各位,走台秩序井然。那天晚上演出,也顺顺利利正常进行。
白珊瑚大动干戈教训蓝宝贝,客观上帮了眉心红的大忙,等于在向每一匹白马表明,它是坚决支持眉心红登上头马宝座的,谁胆敢向眉心红发起挑衅,即使是它的亲儿子,它也是毫无保留站在眉心红这一边的。
‘眉心红威信大增,地位日趋稳固。
一个半月后,蓝宝贝伤愈归队,争权的野心早就化为乌有,老老实实跟随在眉心红身后,看头马的脸色行事,变成一个守规矩懂礼貌听话驯服的臣民。只是有一点,蓝宝贝对待白珊瑚的态度变得很恶劣,白珊瑚在马厩东端,它就跑到马厩西端;训练和演出时排列队形,坚决不愿与白珊瑚挨着站在一起,白珊瑚站在队伍的第二位,它非要站在第四或第五的位置上去,不然就不肯参加训练和演出,母子关系冷漠而疏远。
屠清霞发现,每当蓝宝贝故意从白珊瑚身旁躲离得远些,白珊瑚身体就会像触电似的一阵痉挛,眼神也更加忧郁凄迷,很明显看出它内心非常痛苦。有一天中午,屠清霞到马厩喷洒灭蚊灵,看到这么一个情景:蓝宝贝站在马厩东端围墙边,头朝外尾朝内,一面晒太阳一面打盹,白珊瑚原本站在马厩西端的,犹犹豫豫往蓝宝贝靠拢,它脚步放得很轻,凝神屏息,就像做贼一样。
到了蓝宝贝身后,它抻直马嘴,小心翼翼贴近蓝宝贝身体,鼻翼耸动作嗅闻状。
它马眼微闭,表情很陶醉,鼻翼翕动的频率越来越快,用贪婪嗅闻来形容绝不过分。也许是深沉的呼吸吹痒了蓝宝贝,也许是不小心鼻尖触碰到皮肤,蓝宝贝突然从昏睡中惊醒,扭头一看,是白珊瑚贴在自己身边,就像看到一个怪物正扑过来,竖鬃抖尾惊跳起来,打着愤怒的响鼻,逃窜到马厩的西端去了。
屠清霞看得清清楚楚,当蓝宝贝惊跳逃离后,白珊瑚两眼发直,浑身颤抖,口角泛出白沫,症状犹如癫痫患者发病,好一阵才算缓过劲来,扭曲着脖子发出长长的嘶鸣,声音特别悲凉,可用锥心泣血这四个字来形容。
显而易见,白珊瑚仍很爱蓝宝贝,浓浓的母爱没有丝毫稀释淡化。
让屠清霞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白珊瑚既然这么疼爱蓝宝贝,为何要在眉心红与蓝宝贝发生争权冲突时,站在眉心红一边,并如此凶狠地尥蹶子踢伤蓝宝贝,这在情理上是很难解释得通的啊。
然而就在这时,白珊瑚逃亡了,不辞而别,不知去向。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事先没有一点预兆。晚上还在圆顶马戏剧场演出呢,白珊瑚认认真真表演节目,该它出场就出场,该它做什么动作就做什么动作,没有丝毫反常表现,也没有任何想要逃跑的迹象。演出完后,已是夜里十点半,天淅沥淅沥下着南,屠清霞.
撑着伞,像往常一样,带着马队回马厩。路过中央花园时,她突然听见缓慢而有节奏的马蹄声中,响起嗒嗒嗒嗒急促的马蹄声,由近而远,似有一匹马离开队伍在奔跑。她急忙回头看,昏暗的灯光下,雾蒙蒙的雨丝中,果真有团晃动的白影,沿着花坛间青石板甬道,向马戏团大门跑去。
当时队伍里共有六匹白马,她还搞不清是哪匹调皮马跑掉了。她第一个反应是,紧紧揪住眉心红的辔绳,一般来讲,只要头马不跑,其他马就不会跟着瞎起哄。
随后,她放开喉咙大喊:“来人哪,马跑了!”大门口有两位值勤保安,听到她的喊声,兵分两路,一位冲上来拦截,另一位去关小门洞的铁门。这是一座新型大门,分大门洞与小门洞两个部分,大门洞通行机动车,小门洞通行非机动车与行人。
大门洞安装的是一米五高的有轨不锈钢栅栏门,有机动车驶来时,值勤保安在传达室里揿动按钮,栅栏门就会自动关拢或打开;小门洞安装的是普通铁门,半夜十一点至凌晨六点上锁,其余时间均有专人看守。
在离大门还有三十来米远时,那位值勤专保安拦住了逃跑的马,可不等他来抓缰绳,那马敏捷地转换方向,一闪身从他身旁穿插而过,然后直奔小门洞而来。另一位值勤保安动作非常利索,在奔逃的马离小门洞还有五六米远时,及时将小门洞的铁门关拢了。
随后,两名值勤保安一前一后形成夹攻之势,向逃跑的马围捕过来。那马似乎早有准备,亢奋地嘶鸣一声,斜刺蹿向大门洞,紧跑几步,扬鬃抖尾身体竖直起来,凭借娴熟的马戏技巧,玩了个在舞台上经常玩的跨越障碍的动作,从一米五高的不锈钢栅栏门上跨越而过,稳稳地落到门外,沿着马路狂奔而去,不一会就消失在雨丝迷蒙的浓浓夜色中。
这时候,屠清霞把马群引进马厩,这才弄清楚,逃亡的是白珊瑚。
马戏团动物演员逃逸,算是一件大事。虽然逃跑的不是猛兽演员,不必担心会伤及无辜行人,但奥赛特竞技马价格昂贵,丢失一匹就是丢失一笔财富6再说,一匹马在大城市霓虹灯闪烁的街道狂奔乱跑,影响也很恶劣。尹团长和高导演连夜组织十支追捕小分队,出动所有车辆,卡车、客车、中巴、轿车、摩托车和自行车,拉网式地分头寻找。
冒雨找了整整一夜,城市每条街道每个角落几乎都找遍了,却不见自珊瑚的踪影。无奈之下,只好向交通警求救,设卡堵截,封锁每一条出城道路,折腾了两天两夜,仍得不到白珊瑚的任何音讯。
白珊瑚仿佛是匹隐身马,魔术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虽然白珊瑚逃亡,却不怎么影Ⅱ向马队的正常训练和演出。它已经不是头马,而是马队的普通臣民,它的出走不会引起权力真空或政局动荡。大公马眉心红已如愿以偿登上头马宝座,蓝宝贝的野心得到有效遏制,众马对新头马心悦诚服,它的出走不会造成内讧。它生的女儿雪姬,已长大成材,当候补演员已有大半年,绝大部分节目都已经能够胜任,完全可以顶替它在舞台上的角色。
只不过一匹训练有素的奥赛特竞技马价值昂贵,丢掉了怪可惜的。
有一次,高导演与屠清霞一起分析白珊瑚出逃的原因和逃亡的去向。高导演皱紧眉头说:“马戏团免不了会发生动物演员出逃的事,可白珊瑚逃得实在蹊跷,给我的感觉,不是那种调皮捣蛋者心血来潮一时冲动趁机逃逸,而是有预谋有计划按步骤实施的叛逃。
哦,你想想,它执意要把头马宝座让给眉心红,它不顾母子亲情踢伤蓝宝贝,当时我们都不明白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假如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看,其实它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想逃跑。”
屠清霞频频点头说:“白珊瑚确实是匹很有心机的马,逃跑也很会挑时间,演出归来,夜深人静,老天又下着雨,这种时候,谁都会疏于防范的,它没流露出任何想要出逃的蛛丝马迹,突然一转身就逃掉了,让人猝不及防,逃得很有章法,肯定是处心积虑早就想逃跑了。”
高导演说:“假定它是有预谋要逃跑的,从逻辑上说,它也早就设计好要逃到哪里去。它想逃到哪儿去呢?它的祖籍在欧洲阿尔卑斯山,它插上翅膀变成一匹行空天马也飞不过去的。它出生在阳光大马戏团,这儿就是它的家,我不明白,还有什么地方比家更值得它留恋更值得它向往的呢?” “我想起来了,’’屠清霞说,“它没事的时候,总喜欢伫立在马厩西南角,眺望天边五彩云霞,有时一站就是两个小时……”
“它去了哀牢山黑虎冢!”高导演和屠清霞异口同声叫了起来。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半个月后,四百多公里外的哀牢山黑虎冢传来消息,南山麓深山老林里,出没着一匹浑身雪白的马,总是在娄阿甲的墓四周转悠,有时会静静站立在墓碑前,神情肃穆,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好几位樵夫和草医都看见过这匹白马,它奔跑如飞,非常机警,不等人靠近它,就像一朵白云似的飘进密林里去了。
毫无疑问,娄阿甲墓前出现的白马,就是在逃犯白珊瑚。
屠清霞请示高导演,要不要派辆车,再派几个人,带一支麻醉枪,去哀牢山黑虎冢把白珊瑚押回阳光大马戏团来。
高导演脸皱得像枚苦瓜,沉思了半天,才叹息一声说:“这匹马在舞台上活跃了十年,还给我们生下一儿一女,为阳光大马戏团立下了汗马功劳。它很懂事啊,怕自己出走会给马术队带来麻烦,事先把头马位置让了出来,又平息了蓝宝贝的争权风波。
一切安排妥当,它才伺机逃亡。它已经牙口十四岁了,最多还有五六年,演员生涯就到头了。强行把它弄回来,拴得住它的身体,恐怕也拴不住它的心了。它与娄阿甲感情太深了,它愿意生死相随,那就……那就……我个人的意见,那就遂了它的心愿吧。”
屠清霞噙着泪,拼命点头。
两年过去了,白珊瑚仍出没在哀牢山南麓老林子里。据当地老乡说,这匹白马就喜欢在娄阿甲墓地四周活动。哀牢山温暖潮湿,属于多蛇地区,自从来了白马,村民去娄阿甲墓地,经常可以看到被马蹄踩得稀烂的死蛇。
当地老乡不知道这匹白马叫什么名字,他们管它叫守灵马,也有人叫它踩蛇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