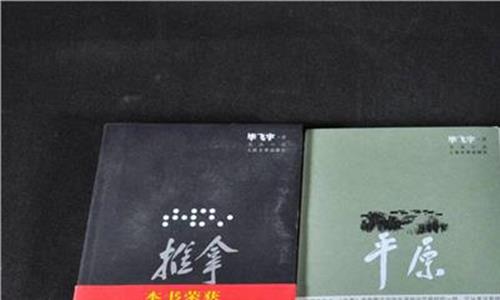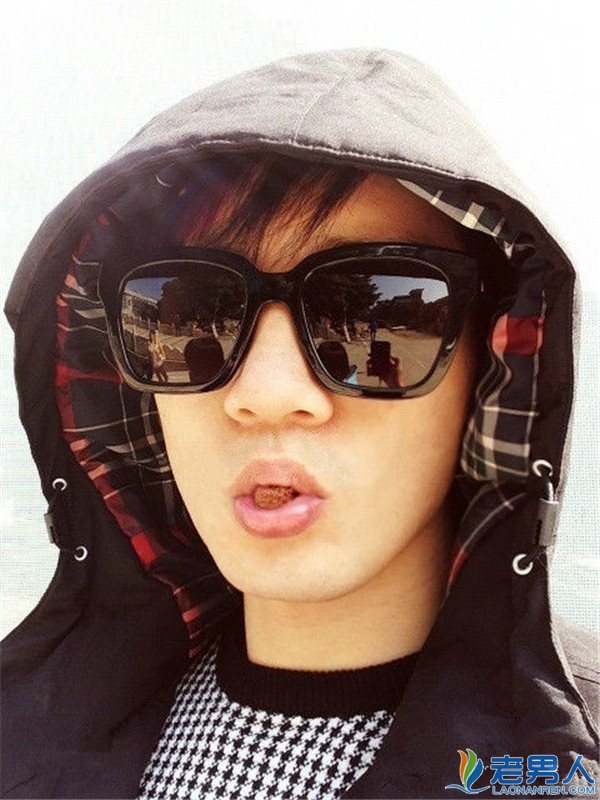毕飞宇研究资料 潘向黎毕飞宇对谈 品读诗词的“走进去”与“晃出来”
2018上海网络文学周
诗人郑愁予再临杭州
伦勃朗油画《夜巡》将修复并网络直播
......
......“图画书界奥斯卡”
“关于文学,尤其是诗歌,特别是古典诗歌,走进去是不容易的,能晃出来的都是幸运儿。”
“诗歌是一种‘无用的美好’,与其说我在推广诗歌,不如说我想要倡导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我们都要想办法获取心灵的力量安顿自己,同时对抗外在的对人性异化的力量。”

潘向黎 x 毕飞宇
“读古诗词说白了就是一个‘化’字,‘隔’是忌讳,读诗过程中不能有墙,不能有帘子,即便是一层纱布,强制性的融入易造成诗境的杂质。最好是摆脱俗世的纷扰,像一片羽毛、一朵云那般飘进去,飘入诗人为你缔造好的世界里。”不久前,作家潘向黎做客思南读书会,与小说家亦是好友的毕飞宇从新书《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出发,以诗词为引,谈日常之美。SMG主播、侧耳团队成员徐惟杰主持活动。

“关于文学,尤其是诗歌,特别是古典诗歌,走进去是不容易的,能晃出来的都是幸运儿。”毕飞宇说。作为潘向黎的多年至交,他觉得潘向黎在谈诗的时候着实通透,一点冬烘气都没有,说到底,和她的“早”有关,和她的“量”有关。

“走进去”与“晃出来”是读古诗词的两种状态,“走进去”的人能捕捉到诗歌的“爆点”,而要“晃出来”则需要更高的修养。如何做好二传手,将自己感受到的诗词“爆点”传递到普通读者心中,二人就此讨论了各自的看法。
潘向黎介绍了自己总结的 “出不来”的症状,当某个人在技术层面理解了一首诗,因“爆点”而拍案叫绝或潸然泪下,便自以为掌握了诗的终极真理,将最近迷恋的诗人作为“最好”,去与人掐架,读诗与赏诗因偏执的爱,反倒成了刻板的事情。她认为“读诗不需要专一,每个解释对应不同的通往诗歌花园的小径”。
她继而在毕飞宇《小说课》一书“文学科普”的说法上,提出了“美普”的观点:“这本书区别于学术性的科普文章,我更多从写作者的角度,在感性与理性的均衡中,将热爱与欣赏传递出去,让读者沿着一条不太曲折的道路,有趣且一路愉悦地抵达诗词想要表达的‘爆点’。
”她阐释道:“诗歌研究像药材铺的抽屉,一个个抽屉拉开,唐代、宋代、明清等划分整齐,这类文史研究对于部分人而言是重要且必须的,但从我的角度,我不太计较一首诗词的文学史地位,也不计较是否每个词都用的精准,有几分狂热就写几分狂热,有几分沉溺就写几分沉溺,但要切忌文史硬伤。
”毕飞宇则认为潘向黎的写法与她对中国古代诗歌史以及古代诗话的熟稔程度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古诗词的品读还是离不开史学、美学、艺术能力这三者。
《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潘向黎/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8
此外,毕飞宇提及读 《梅边消息》一书时,他更多读到的是潘旭澜教授与潘向黎父女间的互动与友爱。如在 《梅边消息》开篇的代序《跟着父亲读古诗》中,潘向黎写到了总角之年跟着父亲吟诵古诗,成长之中,从不懂到可以跟父亲 “辩驳”两句。
又如《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对于父亲大加赞赏“着实好”的杜甫,她少不更事,不以为意。那时相比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她更爱“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直到三十多岁步入中年,有天读杜甫《赠卫八处士》,只感到“如冰炭置肠,倒海翻江”,竟至流下泪来。
“却原来,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里等我,等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等我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来到那一天。”潘向黎这样写道。
她说在父亲的影响下爱上古诗词,不同的年龄发现他们不同的优点,所以活着活着竟把这些诗人们熬成了朋友,“我非常热爱他们,但是我从来不膜拜,当然也绝不可能是俯视,基本是平视的亲切距离。”即使父亲离去多年,一首首古诗词就像一颗颗和田玉籽料,在岁月中沉淀下来,且愈加光莹。
潘向黎
父亲有时没来由就说起杜甫来,用的是他表示极其赞叹时专用的“天下竟有这等事,你来评评这个理”的语气——“你说说看,都已经‘一舞剑器动四方’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久低昂’。”我说:“嗯,是不错。”父亲没有介意我有些敷衍的态度,或者说他根本无视我这个唯一听众的反应,他右手平伸,食指和中指并拢,在空中用力地比划了几个“之”,也不知是在体会公孙氏舞剑的感觉还是杜甫挥毫的气势。
然后,我的父亲摇头叹息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久低昂’!着实好!”我暗暗想:这就叫“心折”了吧。
晚餐后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里喝酒,喝了酒,带着酒意在厅里踱步,有时候踱着步,就念起诗来了。《琵琶行》《长恨歌》父亲背得很顺畅,但是不常念——他总是说白居易“写得太多,太随便”,所以大约不愿给白居易太大面子。
如果是“春江潮水连海平”,父亲背不太顺,有时会漏掉两句,有时会磕磕绊绊,我便在自己房间偷偷翻书看,发现他的“事故多发地段”多半是在“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这一带。
(奇怪的是,后来我自己背诵《春江花月夜》也是在这一带磕磕绊绊。)若是杜甫,父亲就都“有始有终”了,最常听到的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他总是把“哭”念成“阔”的音。有时候夜深了,我不得不打断他的“牵衣顿足拦道‘阔’”,说“妈妈睡了,你和杜甫都轻一点。”
书斋中的潘旭澜先生
毕飞宇认为诗歌的来源多样,最要紧的是从家庭,从童年来的。这方面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存在质的区别。“诗歌伴随了向黎的基础生活,尤其是童年与少年。等她真的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她和诗歌早已经彼此嵌入。”他提倡父母身体力行,让古诗词真正成为家庭生活的一个常态,成为餐桌上的一只碗、一根勺。
潘向黎进一步补充说,出了两本关于古诗词的书后,一些家长便将她当成了诗词教育的咨询人,询问她是否可以列“诗单”?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够吗?哪本选集比较好?对这些提问,她颇感无奈,自言:“宁可小孩懵懂贪玩,也不要用强制性的干涉方式。
耳提面命式的教育只会增加孩子的反感。缘分的事情是急不来的——又急什么呢?”但她也理解家长的苦心,她提议用一些小心思,比如买一些适合孩子年龄段的选本,放在他随时可以看到、伸出就能拿到的地方,只用眼角的余光观察,让他感觉这是他自己的发现。等他有兴趣了,便参与进去。
“诗歌是一种‘无用的美好’,与其说我在推广诗歌,不如说我想要倡导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只是归于个体,我是在古诗词中找到了美的享受。我喜欢古人下了朝堂以后回到家里自我悠闲的状态,这一点古代与现代没有差别,我们都要想办法获取心灵的力量安顿自己,同时对抗外在的对人性异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