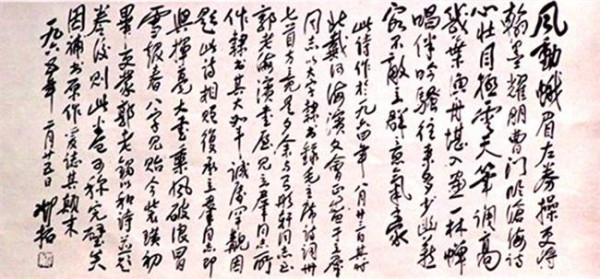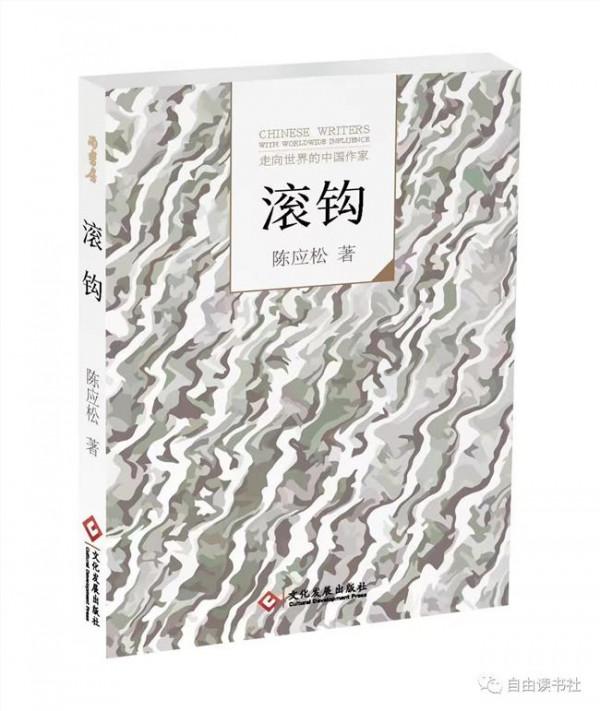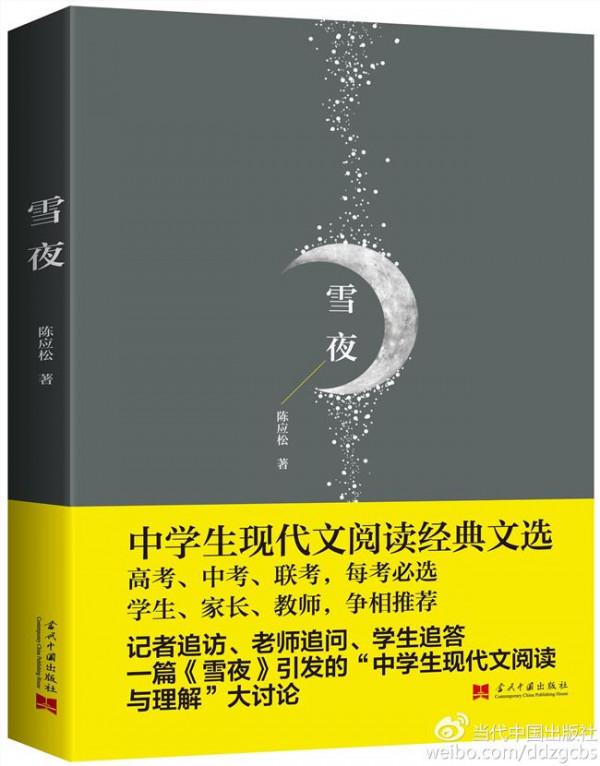自然:人类的自我救赎——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论
人类的堕落、罪恶、文明的虚伪构成了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这是陈应松前期小说的基本主题。但是,他自己也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惑:人类的自我救赎之路在哪里?在这些小说中,他激愤地表达了对人类文明病的批判,但是并没有找到人类切实可行的出路。
这一困惑在神农架系列小说中得到了解决。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通过神农架地区自然、人文风情的描绘,寻找到了人类救赎之路:建立起合乎自然的人伦规范和生命价值观。
陈应松认为,人类不仅要善待自然,珍爱自然,敬畏自然,更重要的是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起伦理价值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是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生。陈应松并没有止步如此,而是由此出发,走上敬畏生命、倡导了神圣的终极价值观,以此寻找到在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中人类的精神出路。
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也许无法避免,但是,人类应该去极力避免现代化所引起的精神困惑。自然为人类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的自我拯救提供了价值参照。
自然因而成为陈应松神农架小说拯救人类的根本路径和方法,也是陈应松小说的价值核心,神农架系列小说完成了陈应松小说创作的历史性蜕变。 围绕自然,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建构了一个特点鲜明的等级世界,城市——乡村——自然构成了这个等级世界的三个梯级等次。
城市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是彻底和乡村、自然脱离的世界,是现代化的典型象征;这里的乡村,主要是神农架地区的行政、自然的区划,是一个连接城市和自然的世界。它相对城市是自然化的,相对自然又是人化的,带有现代化的某些征候。
自然,是指和乡村、城市完全不同的有着自己的生命律动的区域,它由植物、动物、山川组成。陈应松构造的神农架世界中,通过这样的结构方式,陈应松阐释了这样一个主题:对自然的漠视、扭曲、利用只能给人自身和社会造成灾难。
自然不应单纯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它也是人的价值性对象化和伦理对象。 为了体现自然的意义,阐发上述主题,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构造了两个等级系列,一个是城市(人)/乡村(人)系列,一个是乡村/自然系列。
在这两个系列中,以自然因素的多寡构成了对立的两极。城市和乡村是对立的,因为城市是邪恶的。它漠视乡村,排斥乡村。单纯地利用乡村。在城市/乡村的对立项中,乡村充当了自然的象征。
但是在乡村/自然的对立项中,乡村在自然因素上不及自然,因此,在自然的观照中,乡村又是邪恶的,它无视自然的法则存在,最终要受到自然的惩罚。这两个对立项中,自然构成了神农架系列小说的最重要的核心。陈应松通过上述两对对立项的构造,最终达到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式,拯救现代文明病。
一 陈应松的小说创作一直贯穿着城市和乡村对立的主题。他的前期小说基本上都表达了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对城市的唾弃和对乡村的热爱与留恋的感情倾向。他曾这样看待城市: “在城市,连寂寞也充满虚伪。城市的膨胀是人心的缩影。
金钱像肮脏的树叶一样卷起人心的深秋。人们不再传递着季节的喜悦,唯一关心的是行情。”哩① 在他看来,城市只有罪恶、虚伪和算计。而他对乡村则又是另外一种记忆:“记得桑棋吧,记得红薯吧,记得碗堆的清汤和一把对夏天发言的蒲扇吧,记得父亲的驼背和庙宇的青苔吧。
乡村是往事的海洋。已与诗十分近似,差不多都走进了诗里。因此乡村是我们精神的归途,是人生苦恼的伟大歌手。”②与对城市的印象不同,陈应松认为乡村远离了城市的腐朽与堕落,充满了诗意。
对城市和乡村的这种绝然相反的看法,源于陈应松对现代都市的情感困惑,是他对现代人的生存困惑的表达。在小说中,这种生存困惑建立在城市诗意丧失的痛楚中,而乡村是作为都市人生存困惑的救赎存在的。
在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中,城市与乡村对立的结构模式依然存在,但是这种对立的基本点已经从诗意转向自然因素上面了,城市获得了更加清晰的对应点,乡村也获得更明了的内涵。 《松鸦为什么呜叫》讲述了一个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故事。
伯纬为了兑现承诺,把修公路摔死的王皋从工地上背回家。此后,当公路修到伯纬家门口的时候,他就充当了车祸发生后背死人的角色。在伯纬那里,背死者、救伤者是他自发的动力,没有任何外在的目的和要求,就像松鸦看到了死尸要呜叫一样自然。
但是在城市人看来,伯纬的背死尸和救人一定有利益的驱动。小说中,自然的自发性和城市的自觉性就这样展开了较量和对比。在这里。自然的特性和都市的习气出现巨大的吊诡空间,从而让我们看到了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分野。
城市和乡村的分野在更大意义上体现为生命态度和生命规约的差异,《人瑞》对此作出了精彩的写照。《人瑞》展现了自然和城市的对比。人瑞是乡村的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据说有105岁。
这个老人是神农架大地孕育的生命。他按照神农架的自然规律生活,抽旱烟,穿脏衣服,长时间不洗澡。他和神农架融为一体,成为神农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随着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入侵,他的生命就渐渐枯萎。
在商业化的现代文明逻辑中,他成为被都市人窥视的对象,成为传媒猎奇的谈资,成为旅游社的卖点。不仅如此,现代文明开始深入到了人瑞日常生活,人们按照现代文明来规范他,给他洗澡,给他穿漂亮的衣服,给他抽过滤嘴的香烟,甚至给他喝在现代社会常见的保健品。
在现代文明的侵袭下,这个和神农架同气相吸的生命最终走向了枯萎,即使是现代医学也无法留住他的生命。这是个自然生命和现代文明遭遇的悲剧。
在这种对照的描写中,我们发现现代文明、城市其实是建立在对个体的自然生命阉割的基础上。 城市是现代化的主要体现,也是建立在去自然的基础上的。从物质基础上来说,城市是优于乡村的。但是从精神上讲,城市是乡村的自然价值观念的异化。
通过城市和乡村的对照性叙述,陈应松建立起了城市和乡村的价值对照。在二项对立的结构中,陈应松在价值倾向上执拗地走向乡村。这意味着自然构成了这个二项对立结构的支点。作为人类的精神价值趋向,城市被否定,而乡村得到了肯定。
城市的扩张建立在对乡村的掠夺基础上,自然被城市所抛弃。在叙事中陈应松在提醒我们警惕建立在对乡村和自然的摧毁和掠夺基础上的现代化,自然、乡村构成了质疑现代化的对象。
二 如果说在城市和乡村对照性叙述中,陈应松确立了乡村在对自然的尊重上的优先性,确立了反思现代化的价值支点。那么,在人(乡村)与自然的对照性叙事中,自然以巨大的力量超越了乡村,显示了回归自然的必要性和充分性意义。
神农架地区的人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在和城市的对照中,他们具有较多的自然本性,因此在神农架地区人的参照下,都市的险恶、卑鄙得到了鲜明的展现。但是,陈应松的小说所关注的并不仅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对比基础上展开对城市的批判,而是以此为出发点,彰显自然力量、价值甚至伦理意义。
因此,他的小说又构筑了另一个对照系列:乡村和自然的对照。在这个对照中,乡村又丧失了优先的价值意义。 这个对照系列展开了对自然价值和意义的追问。
这个系列中的神农架人不再在外面闯天下,是神农架地区一般的猎人等,他们不与外界发生关系,直接和神农架的动物、植物、自然界发生关联。神农架人对自然的态度是工具性的,在他们看来,动物以及自然界的一切只是他们满足生活的必需品。
他们忽视了自然本身也具有生命,也有尊严;忽视了自然和人类之间其实也存在着一种伦理关系。当人类把自然当作是工具的时候,人类必然要面临着惩戒和惩罚。人类的尊严和伦理意义也必然要受到自然的拷问。
尊重自然,尊重自然的生命意义,构成了人类重要的伦理原则。这是陈应松要在神农架系列中要表达的核心。 《神鹫过境》告诉我们,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只是人类利己的自私行为,但是对于自然来说它是残酷的虐杀,是对生命的无情毁灭。
号是一只在迁徙途中掉队的神鹫,被丁连根抓获。丁连根通过熬鹫的方式,彻底地改变了鹫的生活习性。熬鹫的过程就是人类改变自然,把人的意志强加给自然的重要表现。最终丁连根熬鹫成功,鹫成为了丁连根捕捉其同类的诱饵,号的叫声呼唤了过路的、迁徙的鹫,它们被丁连根一一捕杀。
被改造了的自然,体现出的是人贪婪的物质欲望,这种欲望建立在对生命的粗暴掠夺,和对生命的意义的漠视上。
按照人类的方式改造自然、扭曲自然的本性,受到伤害的并不只是自然自身,这种伤害最终要还归人之身。在《醉醒花》中,巴安常养了一只小熊,并且和熊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感情,熊和人之间出现了和谐的关系。但是最后吃了醉醒花的熊失去控制,吃了巴安常。
在这个非常简单的悲剧故事中蕴涵着复杂的内涵。一方面,熊和它主人关系的友好源于熊的自然性情被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对自然的改造是成功的;但是另一方面,电正是这种改造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因为也正是人,与熊建立起了友好关系的人——伐木队的冉二贱让熊吃了醉醒花而失去控制。
人对自然的改造,带来好处的同时也许就埋藏了不可见的危机。《神鹫过境》、《醉醒花》显示了当人把自然当作工具的时候,必然要受到来自自然的制约和惩罚。
从而自然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逻辑。 《豹子最后的舞蹈》、《牧歌》呈示给我们的是价值理性意义。自然和人之间的并不是简单的工具关系,还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当人将自身的伦理态度强加给自然时,自然会把同样的伦理态度反作用给人类。
于是自然和人类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价值交互关系。《豹子最后的舞蹈》描写了豹子家族走向灭亡的命运。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让豹子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使豹子无法觅食。
豹子家族最后一只豹子,最后也死在猎人的手下。但是命运走向灭亡的何止仅仅是豹子家族。在豹子家族走向灭亡的同时,打猎者的家族也同样走向灭亡。豹子的母亲、兄弟、妹妹、情人红果、情敌石头都被猎人老关杀死。
豹子家族的死亡激起了豹子复仇的欲望。于是在豹子家族走向灭亡的过程中,猎人老关的一家也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他的儿子们和孙子最后在豹子的报复下,走上了死亡之旅。 在自然和人类的搏斗中,由于人类违背了自然的意志,最终遭受到了惨重的教训,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
在乡村和自然的二项对立结构中,陈应松的态度倾向了自然,显示了对人化的自然的一种谨慎态度。自然并不是仍由我们随意处置的对象,它具有自身的生命价值和伦理倾向。
外加于自然的价值准则和伦理意义最终被自然还给人类。 三 陈应松在神农架系列小说中通过构造城市/乡村、乡村/自然的结构方式,让人一步一步地退回到自然,回归到无人化自然的目的地。陈应松并不是要让人在自然面前放弃主体性,而是强调要和自然寻求和谐的、自在的关系。
这种建立在对自然价值基础上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了不一般的社会伦理意义。我以为,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中自然成为找到人类出路的重要通道。
回归自然,自然不仅是人类的生活对象,它还是人类的生活价值尺度。这应该是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的重要主题。 自然并不是人类、现代化进程能完全把握的对象,自然的存在自然有着自身的价值。
在陈应松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神秘的景象,如棺材兽、软骨人、天书、天边的麦子等等奇异景观。有些细节甚至表现出人和自然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差异的情感倾向。《望粮山》多次出现人的动物形象的还原,余大滚一直强调人一天中有两个时辰是牲口,金贵杀死老树时说了一句:“我杀死的是一只獐子,这个时辰他正是獐子。
”《乡长变虎》描写了乡长身上长满了虎毛,差一点变成了老虎。这些个貌似荒诞的细节正是表明了在自然和人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主体与自然之间并不具有等级的差异。
自然并不是可以任意由人类来处理的对象,它有着自己的尊严、甚至是生命。在《牧歌》中,打猎一辈子的张打幡然醒悟,自然其实和人类一样充溢着生命的情趣:“回家的那个傍晚天象依然很怪,好像真有什么要别离似的,晚霞黛青,红鳞变成了卷云,一阵又一阵的大风把山冈都快吹歪了,河水拱起的浪涛像鱼背一样闪闪发光。
各种树木因为大风的长驱直入到处响起折断的喀嚓声,仿佛在过一队大兽阵一般。
真撩拨人啊,让人一下子就想起了过去野猪、鹿子挤满森林的情形,那些神秘的动物,它们有着鬼鬼祟祟的尊严,当你要打死它们时,它们跑得比风还快,真像是一群云精风神。可一忽你又觉得它们是本不该打死的,它们的徜徉极其优雅,一个个如绅士,行走的皮毛绚烂至极,多肉的掌子踏动山冈时无息无声,抬头望山望云时充满着伤感。
你就会觉得它们真像你家中的一员,它们的情绪伸手即可触摸。”③于是,我们发现,自然充满着生命的光辉,有着无上的生命尊严。
在这里,陈应松在自然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伦理关系。我们知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影响甚为广泛。伦理关系、生命意义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自然只是人类的工具,是人类欲望满足的对象。
这种思想的盛行最终构成了人和自然的冲突,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这就是陈应松的小说中的人和自然的二项对立结构所折射的图景。在这个二项对立的结构所引起的悲剧性结局的思考中,他最后表达了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的理念。
《云彩擦过悬崖》阐释了在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能够建立起和谐关系的理念。苏宝良是瞭望塔上的火情观察员,独自生活在山上。在长期和自然的独处中,他和自然建立起了和谐的关系。
在他眼里,自然充满着生命气息,山上的植物、云朵、动物都是他的邻居和伙伴。即使他的女儿被动物咬死,但是在他看来,动物一般的时候是不和人为敌的。正是这样的信念,他在山上从不猎杀动物。在自然中建立起的伦理尺度,帮助苏宝良和人们建立了和谐的人际关系。
他和周围的乡民、过路客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相互关照的良好关系。在临下山的那一刻,他决定放弃下山的机会,长期据守在瞭望塔中。 《云彩擦过悬崖》树立了人和自然、人类社会的伦理尺度。
在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因为人本身首先是自然物。在马克思看来,人本身就是自然的存在,“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
”④作为自然中的一部分,人类要依赖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才能得以生存。
功利性的思想、欲望的膨胀让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中的人和自然的二项对立结构,所要体现的就是人在向自然索取的时候,人把自然当作单纯的功利对象的时候,人类并没有因此获得幸福,相反受到了来自自然的抵抗、制约,甚至是报复。
人类在自然面前并不能获得自由,也无法得到自在的生活状态。因而要像《云彩擦过悬崖》中的苏宝良那样,和自然建立起和谐共生的关系,甚至是伦理关系,才是最为重要的。
另外,对于人类社会组织来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另一种重现。自然的伦理意义也体现在这里。在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所表现的城市和乡村的二项对立结构中,城市对于乡村的功利性的掠夺,不也是人对于自然的工具性态度的翻版吗?从这个意义来讲,人、自然、人类社会其实是一个整体。
马克思早就对此下过断言:“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
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无可辩驳的证明。”⑤因此,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其实存在着整体性,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的交换,同时,自然也在改变着人、人类社会。
马克思据此认为自然是人的对象化存在。 因而自然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伦理的、价值关系。人不是自然的主体,同样,自然也不应该是人的主体。因为人毕竟是按照人的尺度来生活的,而不能按照自然的尺度来生活。
但是,自然、人自身、人类社会应该寻找到共同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原则。三者的和谐共生就构成了宇宙的最高的价值准则。自然、人、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的伦理关系,是个人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完成,同样也是自然存在的最有意义体现方式。
它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木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⑥在马克思看来,人、自然、社会统一于三者的价值、伦理中,只有在三者完全回复到同一的价值基本点上,人才能作为完全的人存在,社会才能寻找到完美的社会存在.
自然也才能成为人、社会的自然。马克思对自然的强调,对我们重新思考社会与人的意义和价值体现方式,对我们来说不无启迪。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找到了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支点:自然。
神农架系列小说对人、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强调,显然具有强烈的社会伦理意义,它突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具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人类社会组织形式建立的标准应该考虑到自然的因素,甚至人类社会的理想的实现,也应该考虑到自然的价值和意义。
人类的伦理关系,不应该仅仅体现在人类社会中,也应该体现在人和自然之间。只有当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对自然应有的尊重的时候,人类社会才能寻找到福祉。
四 当然,陈应松小说中自然的伦理意义并不只停留在此。因为我们不能仅把他小说中所描写的自然看作是实体性、物质性的存在。在我看来,它是一种精神符码。陈应松在小说中执拗地要返回到自然中来寻找世界的伦理秩序,应该有更加深层次的精神拷问。
这种精神追寻就是寻找人类生存的形而上的意义和价值。 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不仅仅是具体生活细节和现场的呈现,自然也具有丰厚的生存论的价值意义。在生存论视野中,人和自然和谐共处,人和自然之间并非是一种算计、利用的关系。
固然,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人类也要借助自然来维持生命,但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平等的,同时,人也应该小心地维护着自然的神圣性。一个中世纪的农民在劳作时尽管也使用了诸如兽力、风力和水力等一些技术,但同时他也被“一个这样的认识所占据,即在神圣的创造委托中去行动;他在造物的名义下去开始并结束他的工作,对他来说,他的动物是减轻他的工作的惟一的‘力量源泉’;他知道土地、植物和动物本身都是由神创造的,并且得自于神;对他来说,生长过程还是一个秘密,是某种不可制造的东西,而且只能加以支持;他把他的收获品看作仁慈的上帝的礼物。
”⑦自然和人类在神的共同看护下,平等相处,并且对自然的情感中包含有神圣的敬畏之情。
因此,人类应该从功利中走出来,对自然保持着神圣的感情,这是人寻找精神家园的主要途径。在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中,他反复叙写的自然,也寄予着一种宗教般的情感。 人在自然的迷失使他们内心狂躁、变态,时刻想君临一切,敌视一切。
这多么可怕。人在互相排斥就像人以强盗的眼光恣意要折磨自然一样,他们除了掠夺就是算计。在算计中掠夺,在掠夺中算计。⑧ 宗教意识很早就在陈应松的生活中留下了影响。
在他所生活的地域就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这种地域特征被他概括北纬30度。在他的成长的岁月里,他就深深感受到了神秘的生活现象。在他的自传性文字中屡次提到青少年时期所遭遇到、所听说的神秘事件。
在他成为作家后的岁月里,这种神秘事物的影响仍然伴随着。他说:“我相信命运,相信冥冥之中的主宰。我并没有皈依一种宗教,但这并不排除我对佛教典籍和基督教典籍的疯狂嗜好,它里面的所有禁忌和终极真理使我与教徒们一样充满了敬畏感。
”⑨在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体验和以后对宗教的思考,使陈应松的小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在他所描写的生活现实上,存在着一个高高在上的世界。这个世界以神秘的、不可测的面目审视着世俗的社会生活。
在《松鸦为什么呜叫》中,这个神秘的力量是人们无法解读的天书。在《望粮山》中,它是天边出现麦子的传言。《吼秋》中则是傻子对未来的预示和“起蛟”的传说。《马嘶岭血案》中只开花不结籽,但是六月一开花是年就有洪水的千年老树。
这些神秘之物超越了现实世界,构成了一个超越性的世界。对世俗的现实世界来说,它是神圣的。它在预示着世俗生活,审视现世人生。 和其构筑的自然的、超越性的神秘世界相对应的是,陈应松反复叙写了人世间的苦难和死亡。
因此,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还存在着一种二项对立结构:超验/现世。不同前两种是具象的二项对立结构,超验/现世是抽象存在的,它隐藏在城市/乡村、乡村/自然的二项对立结构之中。在上述对神农架的两项二项对立结构的描述中,自然和乡村、乡村和城市的对立中,自然以超越的、高踞乡村和城市的姿态构成了对乡村、城市的审视和批判。
正因为乡村失去了纯粹的自然特性,打上了人类活动的足迹,正因为城市抛弃了乡村的自然生活形态,最终导致了人类社会的灾难。
苦难、死亡时的来临,完成了自然的神圣性的构造,完成了超验/现世的二项对立结构。 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充斥着大量的死亡、灾变的叙述。几乎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有死亡。
他如此频繁地写死亡,显然有着他自己的用意在里面,它体现了超验世界对现世世界的惩罚。 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在所构造的“神农架”形象中,完成由艺术形象——伦理价值——生存论的思考。在陈应松的“神农架”中,自然是他的小说全部艺术的支点,围绕着自然完成了小说结构、形象的塑造。
由此出发,陈应松还深入地思考了自然的伦理的意义,提出了具有价值的思想。更主要的是,他的这些小说还走向了更抽象的世界,把具体的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引入到了一个更加具有普遍性的追问上:人类该如何拯救自我? 现代化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道路,同样,现代化所引起的思想困境也无法逃避。
自现代化之路在古老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展开时,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就展开了无穷尽思考、探索和追问。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的国度而言,“天人合一”的思维理路曾经是中国思想的核心。现代化的到来,意味着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抛弃,对自然的生活形态的摒弃。
在现代化锐不可当、高歌猛进的征途中,回望农耕文明,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的主要的道路。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言,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描绘,痴情地对“希腊神性小庙”的构造甚至在后期的小说《看虹录》中对自然神性的深情地礼赞,开始表现出“自然”从现代化的的轨迹中脱落的思想。
原始性包括自然构成了沈从文对现代化的历史道路的反思和审视。陈应松对神农架的“自然”的多层次地拷问时,是否接通了沈从文反现代性的文化和文学的思维理路?我深以为是。
这也就是陈应松小说的根本性的思想和文学的意义所在。 注释:①②⑧陈应松:《世纪末偷想》,武汉出版社,2001。第163—165页,第163—165页,第47—48页。 ③陈应松:《牧歌》,《红豆》2005年第3期。
④⑤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第105页,第84页,第81页。 ⑦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3年,第18—19页。 ⑨陈应松:《大街上的水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10页。














![陈应松作品集 [湖北作家写作姐]陈应松:行走在平原与森林](https://pic.bilezu.com/upload/c/d4/cd44707c317ef59ce6cf5a47ef0679da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