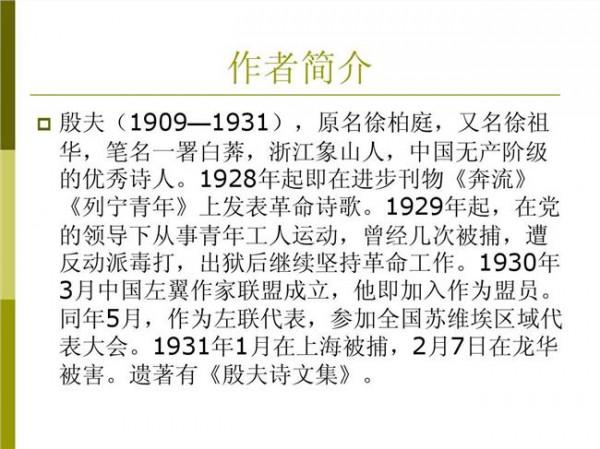契诃夫苦恼 中国最懂契诃夫的人离开了|单读
6 月 27 日,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辞世,享年 82 岁。童道明堪称是中国最了解契诃夫的人,他感叹于这个俄国作家胜于他者的善良与悲悯,共鸣于一代知识分子真正的良心。我们终究还是迎来了这个时代,看着大师们慢慢消融进历史夜空——今天我们回顾了《单读12:创造力之死》中云也退对童道明的访谈,希望能够将大师的温情和敏锐留下,让我们依旧可以追求美,追求福祉实现的那一天。

“实际上,活在审美里面的人,幸福没有耗尽的一天。”
童道明( 1937 - 2019 ),江苏张家港人,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
樱桃园即使毁了也是美的
——童道明专访

撰文:云也退
童道明嗓子特别沙哑,他一笑起来,就像一台需要加油的缝纫机——但他特别爱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关于任何话题。
俄苏戏剧大师梅耶荷德在一篇谈话里,这样描写契诃夫:“契诃夫有个习惯:在有人和他谈话的时候,他会在完全不可笑的地方突然笑起来。一开始这使得说话的对方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在听人说话的时候,契诃夫同时已经在脑子里把他听到的东西加以变形、改造、加工、补充,从中汲取幽默的素材,于是他笑了。”

第一个把梅耶荷德系统地介绍给大陆读者的,就是童道明,他连续翻译了《梅耶荷德谈话录》《梅耶荷德论集》《梅耶荷德传》;至于契诃夫,不但早已无法从他身上“剥离”,而且还在不停生长。他在新书《可爱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赏读》里,写到重读契诃夫书信的体验:“在这三个月里,我天天徜徉在契诃夫的情感世界里,我自己觉得,我更了解契诃夫了,也更爱契诃夫了。”

所以他笑起来更加没个完了。
童道明一直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做他口中的“活学问”,走出书斋,为契诃夫写文章、说话、参加活动,只要一遇人说喜欢契诃夫,他就喜不自胜一整天。逢五逢十的纪念,童道明特振奋,热盼着圈内圈外能有所动作。他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戏剧界,都在重新发现契诃夫。他自己写了三个关于契诃夫的剧本,也有民间剧团很热心地拿去演。
童道明创作话剧《我是海鸥》。
“要善于发现美”——童道明常常这么说,因此现在流行的“暗黑系”、“重口味”,他完全不能接受。但他没抱怨过,因为抱怨不能带来任何生活所需。在我们的谈话中,不论什么主题,一本小说还是一件事,童道明都能拈出其中触动人心的细节,当我把话接下去,他就露出一副“你看,我就知道你也懂”的得意之色。
他说他乐意跟我说话,因为他说什么我都懂。其实我真没读过多少契诃夫,也讲不出梅耶荷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区别,讲不出爱森斯坦电影的妙处。不过,他是一个满血状态下的理想主义者,他可以同一个预期中的我对话。
樱桃园即使毁了也是美的。童心向道,道自彰明。
苏联作家缺乏契诃夫的善良
单读:您为什么这么执着,一直在讲契诃夫?就连写剧本都离不开他。
童道明:当然首先是偏爱,同时契诃夫的声誉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走高,原先他的名望不能与屠格涅夫相比,现在情况变了。欧美国家突然对契诃夫的戏剧大感兴趣,在俄罗斯,以前只是莫斯科的一些剧院在演他的剧本,现在因为欧美人的关系,俄罗斯人也更重视契诃夫戏剧了。在亚洲,契诃夫戏剧主要影响日本,在中国则比较晚,后来北京搞了一个契诃夫戏剧节,圈内圈外才重视起来。
单读:确实,熟悉他的戏剧的人,远少于熟悉他的小说的人。
童道明:但只要用心读了,就会喜欢他。你看,我刚才翻我 2012 年写的笔记:“列宁这么形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对他的影响:‘它把我整个地、深深地翻耕了一遍’”,我评论:“这话很精彩,很传神,也可以用来形容契诃夫对我的影响,他把我整个改造了。
”再看这个:“俄国导演埃布罗夫也是契诃夫的崇拜者,他是这么描述喜欢契诃夫的理由的:‘我喜欢契诃夫,不是因为他拥有这个或那个,而是因为他不论写什么,背后总有一个人,这个人让我感到很亲切很贴心。
’”你知道吗?类似的看法不只是俄罗斯人有,也不只是我有。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到清华去做讲座,结束以后有个女生突然走上来,跟我说了一句:“童老师,我是从外地赶来听的,我就想对你说:我喜欢契诃夫。”说完这句话她就走了。这就是契诃夫的力量,人们对他的感情是那样一种喜欢,不需要讨论什么。
单读:您个人对契诃夫的看法有过什么变化?
童道明:其实我的看法也是一点点被深化的。一个很大的启发来自爱伦堡的《重读契诃夫》,这本书是爱伦堡在 1960 年——也就是契诃夫百年诞辰时写出来的。爱伦堡的观点是,辞书上说的“ 19 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杰出的”、“伟大的”、“著名的”之类的话完全不能说明问题。他说:如果没有契诃夫的善良,他写不出后来我们能读到的这些作品。
昨天我到宝坻,文化部搞了一个文化走基层的活动,请了我去,还请了剧作家费明。他跟我说:童老师,我看了契诃夫戏剧全集新书发布会了,我记住了这句话:善良,对作家来说也是一种生产力。我讲座时,也很想讲这句话,你肯定也读过《金蔷薇》,帕乌斯托夫斯基写的,他说,苏联作家缺乏契诃夫的善良。
我们也一样,以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善良算什么?所以我认为曹禺给我们最大的贡献,不是深刻揭露了中国社会,而是他在《雷雨》序言里的一句话,说“我怀着悲悯的心态”来搞创作,这就把其他剧作家比下去了。20 世纪中国的剧作家,还能演的就是他和老舍等少数几人,他们有真正的人文精神。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 Anton Pavlovich Chekhov ),( 1860 年 1 月 17 日 - 1904 年 7 月 15 日),俄国世界级短篇小说三大巨匠之一,杰出的剧作家,是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单读:契诃夫的戏剧里面居然没有反面人物,这真的很特别。
童道明:是啊,全是正面人物,这样的戏写起来很难,也不容易讨人喜欢。德国有个导演排演《三姊妹》,他说,我为什么喜欢契诃夫戏剧?因为我愿意跟三姊妹在一起。
单读:他都不说专业上的东西,不提戏里的冲突,他喜欢这个戏的温情?
童道明:也有冲突,但契诃夫去世半个世纪之后,戏剧冲突有了新类型,不是人与人冲突,是人与环境的冲突,这样一来,契诃夫就成了一个很亲切的先导性人物。
我发现我常常能拿契诃夫说事,说得最痛快的一件事,是在电影学院,那年三峡工程上马,我讲《樱桃园》。我说最大的樱桃园就是长江三峡,旅行社打出广告“三峡告别游”,其实就是在告别“樱桃园”,尽管它陈旧,但它美好。现代人的困境,就是不得不告别。我看得出来,电影学院的学生把我的解读听进去了。
单读:这篇文章在您出的书里收了吗?
童道明:收了。后来我不断有机会讲这些。比如我说到梁思成,北京城倒塌时,城里只有梁思成为它哭泣,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拓宽马路是最要紧的。我就拿契诃夫来说,让他接入中国的地气。前年南京挖地铁,要砍法国梧桐,南京的市民就不干,你看这就是进步,中国人的进步。
隔膜是 20 世纪文学最大的主题
单读:契诃夫太早慧了,他才活了 44 岁,留下的信却这么多。
童道明:他十八九岁就写出了《普拉东诺夫》,太厉害。但是,除了小说戏剧,他的其他文章都是书信、札记,评论几乎没有。这是因为他不喜欢俄国式的空谈。契诃夫只写过一篇正经的评论,纪念一位去世的探险家,叫热拉夫斯基,契诃夫很爱他。后来文章给了一本杂志发表。热拉夫斯基是个实践者,俄罗斯人整天议论个没完没了,都不如他做实事。
单读:我读以色列文学比较多,以色列最有名的作家阿摩司·奥兹和夫人 2007 年来上海,我们访问他们,他夫人就说起他们有多爱契诃夫,还讲了一篇他们最喜欢的,说一个做棺材的老头给他死了的老伴打了一口棺材,等等。
童道明:这是《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一篇精彩的小说,但一般人看不明白。它讲的是人生的苦涩,活着的时候老夫妻没话讲,妻子死了以后丈夫给他做一口棺材,这多么反讽。然后,他才想到,要去几十年前谈恋爱的河边看一下。你看这就是故事的精华所在,这小说的内涵多丰富!但中国一般的读者轻易就放过去了,觉得故事很平淡。
单读:以色列的作家这么崇拜契诃夫,让我很吃惊,以前我都比较忽略他。
童道明:以色列人有个震撼中国话剧界的戏——《安魂曲》,把三个契诃夫小说组合到了一起,就看他们选的小说,你就知道他们有多么懂契诃夫。
以色列卡梅尔剧团话剧《安魂曲》。
单读:中国人为什么懂得少?
童道明:我经常跟人说,我们应该重视顾彬的观点。顾彬讲话很狠,说现代的中国作家还没有鲁迅那么现代。这话得罪了很多中国作家,但这话多有眼光。我们当代的作家可怜到什么地步:把魔幻现实主义看得这么重,却不知道鲁迅的厉害。
鲁迅厉害在哪里?写隔膜,《故乡》《祝福》《药》,写的都是人与人的隔膜。隔膜是 20 世纪文学最大的主题。有个美国作家说,写隔膜没人能超过契诃夫,中国也没人超过鲁迅。我完全理解顾彬的意思。但我们想不到这些,中国就出了一个鲁迅,我们还经常贬低他。
其实我也是读了契诃夫之后才懂鲁迅的。为什么说契诃夫是 19 世纪的人,他的思想属于 20 世纪,因为他早那么多年就把人与人的隔膜揭示出来了。你看那篇《苦恼》:小孩子死了,我讲给你听,啊啊你别跟我讲,那么我讲给一个青年马车夫,我们是同龄人……完了他也不听,那咋办?我讲给马听——这就是隔膜。
单读:简简单单但是触动人心。
童道明:现在交流工具多了,怎样?隔膜照旧。经典是可以随着时代一道前进的。对于《小公务员之死》,以前的解读是“官高一级压死人”之类,这不也是隔膜吗?我 2004 年写过一个文章,将契诃夫的《苦恼》和鲁迅的《祝福》做对比。《药》讲革命者的悲哀,群氓无法理解革命者;还有《故乡》,回到故乡,看到幼时的闰土现在的样子,中间隔了多少东西,这是鲁迅的真情流露,他对人世的观察多么了不起,但我们已经慢慢疏远他了。
单读:现代人的肤浅在于只看重简单的东西,不要读鲁迅,他太阴暗,为什么要让他来破坏我们的生活感受和心情呢?
童道明:我们不愿意让鲁迅的作品来引起我们的怜悯和恐惧。
单读:我读契诃夫不多,不过特别喜欢《带小狗的女人》。
童道明:对啊,《带小狗的女人》,了不起的小说,最了不起的地方在小说的结尾:男主先去见情妇,然后送女儿去上学,一个人要过两种生活。这是 20 世纪的眼光和情怀啊。他写爱情,不写肌肤之亲,而是写爱情发生以后,人内心产生的变化。
男主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有白发了——这是小说的“点”。这个人本来是就是去浪漫一下,没有想去爱,结果他爱了,他想到自己给别人带来了什么,别人又给了自己什么。这种醒悟和思考是我们所缺的。我说,契诃夫几乎就是个心理学家。
走出象牙塔
单读:您有过必须靠精神食粮过下去的艰苦日子吗?
童道明:我没有十分苦过。至于精神食粮,我觉得读书人一生就读一两个作家,读到产生很强的亲近感,就已经很好了。你知道怎样才算精神食粮吗?就是当我开始想,“契诃夫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的时候,这就是了。
当时特别兴奋,特别幸福。头脑里有了这种反应,什么苦都不在乎了。然后我开始把自己得到的感动、感悟传递出去,给别的读者,让他们跟我一起来懂他、喜欢他,这是我搞研究的一个很大的乐趣,不是关门造车,而是跟同胞分享,跟读者分享。再然后,更高的境界:我可以发挥了。我第一个剧本《我是海鸥》是从契诃夫的《海鸥》里发挥出来的。我喜欢这种延伸,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状态,我想给契诃夫编台词。
单读:有什么得意的台词?
童道明:比如《我是海鸥》里有一句契诃夫的台词:“除了匿名信,我什么都写。”契诃夫确实什么都写,而且他还鼓励别人写。我觉得戏剧很了不起,契诃夫当年不停地督促高尔基写剧本,高尔基就写了《小市民》,现在,高尔基的故乡没什么人再读他的小说了,但《小市民》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保留节目,前两年还来北京演。
高尔基故乡的人通过看《小市民》来走近高尔基。如果高尔基当时没听劝告,去写剧本,对社会是多大的损失。今天的欧美国家,普通人认识契诃夫,不是因为小说,而是因为戏剧,他们那里做戏剧的机会很多。
契诃夫与高尔基
单读:除了契诃夫,您还写别的题材的戏吗?
童道明:我写知识分子题材。我写过一场冯至和季羡林的戏,北京的蓬蒿剧院演了。我是怀着一种为契诃夫写戏的心情,来写 19 至 20 世纪之交诞生的中国知识精英,写他们的良心。其中专门有一场写冯至立遗嘱,冯至的遗嘱很感人,其中说“我希望与我有关的后代,努力工作,不欺世盗名,不伤天害理。”多么震撼,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色,他当时已经看到了学术界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这个剧本盲人演员演过,他们背台词、朗读,后来他们跟我说,领导对结尾不满意。我的结尾安排了一个画外音:“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见到马克思了吗?见到杜甫了吗?见到歌德了吗?”然后舞台上出现本剧全体演职人员朗诵冯至的一首诗《那时》。当时是 1947 年,他为了纪念四个被国民党枪杀的大学生写了这首诗,为他们招魂,呼唤光明正义。领导嫌绝望,说:“难道我们现在没有光明正义吗?”
单读:感觉在您这里,戏剧都是离不开诗的。
童道明:冯至逝世五周年时,邵燕祥说,他有一次在美国,在一个华裔青年聚会上听到有人朗读冯至的《那时》。我听他这么讲,就打定主意,在自己写的戏演出之前,得有一个人来朗读这首诗。首演时濮存昕朗读了,北大演出时是敬一丹朗读,后来中学生、大学生都朗读过。
冯至用《那时》来回忆五四:那个时候曾经期望的,现在在哪里?他后来还是怀着希望的,经常眺望远方,你看美国的华裔青年都能传诵。创作就得有那样一种情感注入在里面。要是只搞研究,多没意思。
单读:您写这些戏,也是想让昔日的情怀复活吧?
童道明: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懂那些知识分子。我没在国内上过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就去了苏联。我没有国学的底子,我的语文水准肯定不如中文系的人,全靠从我学到的大作家那里得到的养料来做事情。我记得头一次在报纸上介绍我的是《中华读书报》,作者说,童先生做的是“活学问”,我觉得这话满理解我的。
单读:回到契诃夫,您在他的书信里看到哪些特别称得上“知识分子良心”的内容?
童道明:四千多封书信我都读了,他了不起,我觉得最值得读的是他对高尔基的态度,和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态度。他投入全身心去研究德雷福斯事件,他说,左拉这次大放光彩,证明原来人可以这样做,这是知识分子立场的经典表现:一群真挚的法国知识分子对当局的对抗,结果其影响超越了法国,成为 1898 年欧洲范围内的一件大事。
契诃夫的一个老朋友手下有份报纸,一直攻击左拉,契诃夫就和他决裂,后来虽然和解,但友谊不复当初。他写信给高尔基说科学院已经选他为院士,沙皇闻讯后震怒,科学院不得不收回成命,契诃夫立刻给院长写信,说愿意放弃自己的职位声援高尔基。你看在这种地方,都见他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节。
契诃夫与列夫·托尔斯泰
单读:一百年前的俄罗斯,90 %的人都没文化,但现在却是阅读大国。
童道明:这真得归功于 19 世纪。欧洲都承认,19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太强大,那种让人灼痛的人道主义,震撼了西方阅读界。起初他们管契诃夫叫“俄罗斯的莫泊桑”,后来就发现莫泊桑不能跟契诃夫比。
契诃夫跟托尔斯泰不同,他太追求自由,没有信仰;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一样,他不激进。我们无法预料,如果他能经历十月革命的话会变成怎样。可以参考的是卡拉林卡,他和契诃夫关系很好,曾一起抗议高尔基被科学院除名。卡拉林卡在十月革命后对无情的对内镇压表示不满。
还有卢那察尔斯基,也是很棒的知识分子。卡拉林卡因为人道主义而无法接受专政,卢那察尔斯基虽然是体制内人,却很理解,在卡拉林卡去世后还撰文悼念人道主义。高尔基也无法接受那种没有必要的残酷,他跟列宁说,您走吧,别在这里待着了。列宁反过来劝他,你走吧,你被知识分子包围了,你出国去吧,高尔基就到意大利去了。
契诃夫温情而敏锐,他最喜欢两个晚辈,一个高尔基,一个布宁,这两个人都曾住在契诃夫家里。回忆契诃夫的文章,数高尔基写得最好。2004 年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我们利用那个时机宣传了契诃夫。十年以后又逢到 110 周年,今年又是他诞辰的 155 周年纪念。这些契机都得利用上。走出象牙塔,很重要的。
可爱的想象
单读:您编译的《梅耶荷德谈话录》我很爱看,梅耶荷德说,看社会新闻时,很想看凶手被绳之以法,但我们在读《罪与罚》时,却想着让主角别杀人,这是新闻和文学的区别。
童道明:梅耶荷德在导演里是个特别有学问的人,他对梅兰芳的赞美就很见功力,后来还把一个戏献给梅兰芳。梅耶荷德的两个学生爱森斯坦和奥赫罗勃科夫,也成了梅兰芳的崇拜者。奥赫罗勃科夫后来写过一个《论假定性》,里面讲他和爱森斯坦是怎么看梅兰芳的。
对中国戏感兴趣、有研究的俄罗斯人有很多。有个俄罗斯木偶戏专家,1950 年访问中国,回去后写了一本《人民中国的戏剧》,他讲《三岔口》给他的启发。他说在世界戏剧的武库里,我们不知道有这样一种武器,能在舞台上表现黑暗。这个黑暗是狭义的黑暗:把蜡烛“噗”吹灭,用虚拟的格斗动作来表现互相看不见对方。你看人家以这样的角度,而不是以一般的鉴赏演员的武艺多么精湛的角度来看《三岔口》,太特别了。
同样的,还可以比较中西的绘画。欧洲的油画,画鱼一定画死鱼,因为他们没法画活鱼,但齐白石却可以画活鱼,他画一些水草,鱼就活了。这是王朝闻说的。王看了我写的关于梅耶荷德的论文,开心得不得了,所以后来他给我编的谈话录写了序言,他用的标题是“可爱的想象”。
单读:读梅耶荷德我也很开心,他赞美个性,他的观察总是很细,他说艺术家必须一直跟自己过不去,不要固化成什么主义。
童道明:苏联在三十年代发起运动,反对形式主义,遭殃的是肖斯塔科维奇,而形式主义的总头子是梅耶荷德,他的剧院被关闭,他被逮捕,以间谍罪处决。五十年代他被平反,他们把他女儿找去,把她父亲的遗言告诉她:我已经活了六十六岁,我希望有一天有人会知道,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梅耶荷德诞辰九十周年时,爱伦堡在他的纪念会上发言,他说:“我多么幸福,我可以活到今天,可以再次来纪念他。”北京人艺的林兆华在一次纪念焦菊隐的会上,上台发言,什么也没讲,拿了一本书,读了一段话:“剧场开放,走近观众,有人批评梅耶荷德,有人赞美梅耶荷德,艺术的青春就在于此。
”中国话剧一百年那会儿,《新京报》记者问他:“你最佩服哪几个戏剧家?”他回答:“莎士比亚、契诃夫、梅耶荷德。”
单读:这本书的印数好像很少?
童道明:但我估计梅耶荷德能让很多人产生共鸣,结果真的很多人知道了这个有文化、有追求的导演。
梅耶荷德
单读:我印象深的是他很方正。他评论契诃夫,说契诃夫跟人说着话,不知不觉就会笑起来,因为他一直在以小说家的敏感,把眼前的人和听到的话修改、变形、找出幽默的地方。这种观察太锐利了,又很温情。大作家永远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他一直在里面玩味。
童道明:是的。我们的导演最缺的还是文化,所以做出东西来没有高度。好的导演总在创造。爱伦堡还讲过,梅耶荷德的《钦差大臣》,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果戈理。
单读:梅耶荷德接触的人、谈论的人都是大师,他说托尔斯泰从来不会迎合什么人,真说得精彩。我就想到现在的人都有年龄焦虑,总怕跟不上年轻人的兴趣。
童道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跟梅耶荷德是最有才华的苏联导演,虽然两人分道扬镳,但斯坦尼还是欣赏梅耶荷德。爱森斯坦也启发了我很多,他懂日文,所以他知道方块字是怎样一回事。他是蒙太奇大师,他说是汉字帮助我认识了蒙太奇的本质。
怎么讲呢?他举例子:一个口一个犬,是吠;一个口一个鸟,是鸣。他说,口 犬不是狗嘴,而是狗的叫声,口 鸟不是鸟喙,而是鸟的叫声。这就是蒙太奇。你看,一对比,我们的词典里显得很枯燥乏味了。蒙太奇早就不只是一个工具了,所有导演都要用它。其实它无所不在,你看围棋棋谱,里面充满了蒙太奇:这步棋下“重”了,那步棋是“腾挪”。你写文章,就要考虑段与段的连接不能太死,要有张力。
单读:爱森斯坦还有些什么别的洞见吗?
童道明:爱森斯坦是梅耶荷德戏剧班的学生,但很快,梅夫人就发现,爱森斯坦不该再在这里学习了,应该自立。于是爱森斯坦从戏剧转到电影。他看了梅兰芳的戏后写了六篇文章,我读到一篇。他说,中国戏曲是现代世界上唯一一个歌舞结合的戏剧,原始状态的戏剧都是这样的,但后来分离,在欧洲,歌剧、芭蕾分出来,但梅兰芳保持了戏剧歌舞结合的古风,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能讲这个话的人,肯定是大学问家。
普希金是俄罗斯的一切
单读:我忽然想起梅耶荷德说的:我讨厌情侣来看我的戏。
童道明:他希望观众都是一个一个来的。他是第一个说出“没有伟大的观众就没有伟大的戏剧”的人。新戏剧怎么出来的?是观众成为作家、导演、演员之后的第四个角色加入到戏剧中来之后。这叫思想家,他的审美能力多么高啊!
王朝闻一看就知道梅耶荷德了不起,“可爱的想象”嘛,懂审美的人不一定全能。纳博科夫就说过:“我的思维像天才,我写作的水平中不溜,我说话像孩子。”我看了就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我讲话不连贯,哈哈,连纳博科夫都有这样的情况。
单读:除了契诃夫,您还特别欣赏哪个俄罗斯作家?
童道明:普希金。俄罗斯人都把普希金看得特别重。你注意到《日瓦戈医生》里,日瓦戈有一段札记:我爱普希金和契诃夫,他们代表了俄罗斯式的童真。有个评论说,普希金是俄罗斯的一切,你一定要相信,俄罗斯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认为那种纯真——俄罗斯式的童真非常珍贵。
想想克里米亚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加入了俄罗斯,二十多年过去,全民公决,96% 以上的人要回归俄罗斯,什么原因?文化的力量。不管属于什么政治党派,有怎样的宗教信仰,没有一个俄罗斯人不爱普希金、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
中国就缺少这样的文化凝聚中心。你看俄国冬奥会开幕式,全是文化人,甚至把纳博科夫也搞进去了。这种民族在意识形态上可以冲突分裂得厉害,但对 19 世纪文学,他们不会有任何争议。
《日瓦戈医生》电影海报
单读:中国人似乎不能理解这种对文化与文学的集体仰望态度。
童道明:我们有一些搞俄罗斯文学的人,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屑一顾。我说,每一个阶级都对世界提供了他们的楷模和英雄,保尔·柯察金就是工人阶级贡献的英雄,地主阶级也能提供他们的楷模。千万不要因为某个时代过去了,就轻慢这样一个主人公。
契诃夫考验我们什么?考验我们的心是不是太硬。你批评一个什么东西,批评错了,害处比表扬错了要大得多。我常说,你搞戏剧评论,一定要有对戏剧的爱,深深的爱。你注意到没?我从没写过批评一个人的文章,但不是说表扬不用担风险,你会注意到,我常常表扬广受批评的剧本和文章:《绝对信号》、《街上流行红裙子》,当初我都表扬它们,而且是在别人批评之后。
单读:缺少了爱,所以才一门心思打出头鸟,干倒同行。
童道明:所以中国话剧的悲剧就是一直出不了真正的悲剧。我们最大的缺失是悲剧意识,是悲悯心。没有一个戏剧大国是没有当代悲剧的,中国一直没有,中国舞台上看到的悲剧都是 1949 年之前的。可是悲剧净化人心呀!
第一个戏剧理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就是这么说的。莎士比亚写悲剧也写喜剧,他的悲剧的价值比喜剧大得多。契诃夫只写喜剧,但喜剧里有大悲悯。有时候大家一看见“悲剧”两个字,就觉得,好消极呀!实际上,活在审美里面的人,幸福没有耗尽的一天。
编辑丨十三
图片来自网络
点击上图,购买全新上市的《单读 19 :到未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