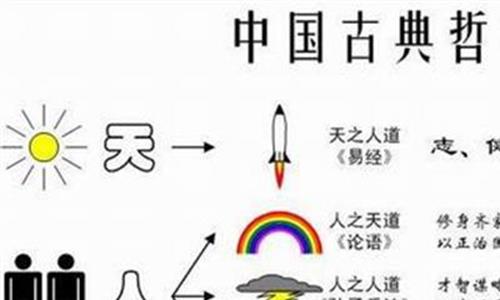天人合一英文翻译 天人合一:中华面具艺术的哲学阐释
面具的存在是一种世界文化现象,面具艺术更是一种世界性的艺术。“使用面具这一现象可以说遍及全球,无处不在。”[1](P9)
面具作为艺术,既表现在静态的面具造型之中,①又表现在动态的各种面具艺术活动的表演之中。这是面具艺术独特性格的双重性。面具表演,顾名思义,指的是戴着面具的表演活动,包括假面舞和面具哑剧(哑杂剧),以及中国的跳神、社火、傩祭、傩歌、傩舞、傩戏等。

换言之,面具的艺术性存在于静态的面具造型和动态的面具表演之中,是具体的人类行为中的造型性表达。
从另一方面说,面具是人的生存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中介”。因为它面对的是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的生存和死亡,所以又充满了神秘性,面具成为构成生存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中介”、出入存在世界和神鬼世界的“密码”和形成娱人世界与娱神世界的“场域”。

“面具跟神话一样,无法就事论事,或者单从作为独立事物的面具本身得到解释。从语义的角度来看,只有放入各种变异的组合体当中,一个神话才能获得意义,面具也是同样道理,不过单从造型方面来看,一种类型的面具是对其他类型的一种回应,它通过变换后者的外形和色彩获得自身的个性。”[2](P19)

中华面具艺术的独特性格,是从与非面具艺术的对照中得来的,这是对研究面具与非面具艺术路径的思考。
中华面具艺术的独特性格,又是建立在独特的神秘审美上的:其与生活状态相异的外部形貌和行为活动,包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各种傩的演绎行为——傩歌、傩舞、傩戏等,它表现出了中国人战胜生活困难的独特一面:企盼愿望的独有精神表达。
中华面具艺术的艺术性,也就存在于这种独有的神秘性之中——一种“天人合一”的叙事之中。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华面具艺术的独特神秘性,也就是其独特的“天人合一”性。
一、中华面具:精神世界的独特神秘性
作为艺术的一种,面具创造的是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是一种神秘的精神世界。这在中华傩面具的行为活动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傩”是中华民族从史前社会就开始的一项驱除苦难、追求美好的精神活动,傩的基本功能是“驱鬼逐疫”和“祈寓福喜”,傩的面具功能也就体现在这种“驱鬼逐疫”和“祈寓福喜”的精神活动中。凡是傩,无论是傩祭,还是傩乐、傩舞和傩戏,都与面具相关——面具成为傩的活动的外在显现的标志。虽然,傩的表演,以及面具、布景、道具、服装和特技等,都与艺术相关,但面具是傩的艺术灵魂——用面具特有的艺术性来显现傩的本质性。
人的世界就是人维世界,是以人为起点的世界。人维世界是人自己创造的世界,人维世界也是人自己展开的世界。人维世界也是一个由三极世界组成的世界:第一极世界——存在世界(第一世界);第二极世界——生存世界(第二世界);第三极世界——精神世界(第三世界)。人是三个世界——存在世界、生存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综合与统一体,这是世界人类作为一个类的物种的共性。
人类创造的精神世界,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非生理存在的世界,是人类为了识别、认识和把握人的存在世界和生存世界所创造的另一世界,也就是由文学艺术和宗教习俗组成的两翼世界。艺术和宗教都是因人的精神追求而形成的。艺术是人类为了精神的交流而创造,宗教则是人类为了精神的慰藉/解脱而创造。
叙事是艺术生成的本质,艺术叙事也是对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展示。
各种艺术的特性——艺术性的差异,也就体现在材料与展开的技艺上的差异。换句话说,任何艺术的独特性,就是叙事的材料(媒材)和技艺的独特性。中华面具艺术的特殊性格就在其面具造型(媒材)和表演(技艺)的独特性,一种在媒材(面具、服饰等)、技艺(活动和表演)与叙事上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又基本集中在面具的造型和表演之中——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面具造型和面具表演的高度统一性——造型-表演的写意性。这种写意的统一性也就是中华面具的艺术性。这就是说,与西方面具艺术相比较,中华面具艺术的特殊性,正是因媒材和技法的不同而导致的叙事方法的不同产生的艺术特殊性。
更进而言之,中华面具艺术的特殊性,是一种独特性格的神秘性,它建筑在两大基础上:一是艺术创造的写意基础;二是宗教习俗的混杂基础。
对中华面具的艺术性而言,宗教习俗的混杂基础——儒释道与民间宗教习俗的混杂,造成了中华面具造型-表演的形态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它带来的是面具造型-表演的形态上更多的单一艺术特性,如各地域傩舞和傩戏的差异,以及藏戏面具作为中国戏剧的特殊性。
但艺术创造的写意基础却具有共性,它是形成中华面具艺术特殊性格的最基本原因,也形成中华面具艺术特殊性格的最基本结果。这就是:中国人在艺术创作上的写意原则,是建筑在自身独有的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的哲学观念上的——“天人合一”的哲性想象上。
二、面具的审美性:“天人合一”的哲性想象
中华面具艺术的“天人合一”性,表现的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时空观念和生活态度。
“天人合一”,在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确切翻译,“human life being in a highly harmony with nature.”只是一个相关的大概意思。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庄子·达生》也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汉代董仲舒则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③“天人合一”后来成为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和根本观念之一,更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之一。
“天人合一”也就是“天人同类”“天人同象”“天人同数”,与“天人之分”说相对立,表明生命与自然同在、人与自然和谐、人天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宇宙万事万物息息相关。“天人合一”思想,也就是人与自然、万物、宇宙的一元统一思想。
所谓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说的是天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天又是人们敬畏、侍奉的对象。而以天为根本,就是以人为根本,人与天之间不存在二元的对立关系。二元的对立关系主要指人对自然界采取相疏离、相对立的文化态度,把自然界当作一个外在于人的世界来看待;而“天人合一”则相反,指人对自然界采取相调和、相统一的文化态度,即人处于自然界之中,把自然界看成一个与自己浑然一致的统一整体。
前者是西方传统文化模式的基础,后者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灵魂。
中华面具艺术的“天人合一”性,指的就是这种人神统一的一元性。这种人神统一的一元性,具体表现为:
其一,一元而非二元:中华面具本身不“化身”为神鬼。
“天人合一”的哲性想象,是“面具”维度上的想象——依据人的生存世界想象出来的非人的“神鬼”世界。“天人合一”的“面具”维度的哲学,是“替天行道”的哲学。以“面具”的角度思考,就是脱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在“替”天说话行事——天与人在这里得到了非对立性的统一。
在中华面具艺术中,凡人与神鬼的关系,不是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也不是神灵天国与世俗世界的关系,而是人神相通相同的关系。
与世界上的面具艺术,尤其是西方面具艺术相比较,中华面具艺术内在的一元性——天人合一性,将面具与面具的装扮者甚至观演者都统一在艺术的“精神世界”之中,因而,在本质上将“摘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神”的人与面具的这种二元对立,推出了面具的表演甚至面具的装饰之外。显而易见,中华面具的艺术性,就是天人合一性,凡人与神鬼在面具上的艺术统一性。
显然,中华面具艺术的这种天人合一性,与西方面具艺术的人神对立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人合一性是人神的一元统一性,人神对立性是人神的二元对立性。所以康德说“以人智去窥探神智”,强调的正是在人神二元对立状况下的人的重要性,向往的是在人神二元对立状况下的人与神的亲近。
可以这样说,中华面具的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西方面具的哲学却是“人神对立”的哲学。对中华面具来说,面具不是天,而只是天的想象;面具也不是人,而只是人的代言;面具更不是物,而只是物的行为。
美国表现主义现代舞代表人物魏格曼,常常让舞者戴上面具表演,以“凸显”人物的普遍和共同性格,这与中华面具舞蹈的“代天传言”的面具功能决然相异。因为在魏格曼的现代舞蹈中,“戴”上面具舞者就代表了这一类“人”或“神”,中华面具艺术,即使是傩面具艺术,表演者“戴”上“神鬼”面具并不代表表演者就是“神鬼”,面具不是“神鬼”,而仅是一种象征和隐喻。
譬如中国民间舞蹈的《跳钟馗》和《跳无常》等,也是戴面具而舞,但舞者决不会“化身”为钟馗和无常,而仅是一种借“神鬼”来“娱人”的舞蹈——一种借面具的外形以形肖的“替代”性娱乐行为。
不仅如此,非洲面具也与中国傩面具不同,常常是“神鬼”附体,面具成为“神鬼”的化身,“在有些地方,从最近曾有面具表演的地方走过都被认为是危险的。当入社仪式到了尾声,面具就会被烧毁。‘Kiss’(基石)这个词根可以为‘迈基石’的解读提供更多证据,它既表示假面表演,也表示附上魔法的物体物质。
”[1](P58)但即使是中华面具艺术中最神秘的傩面具,其本原也是这种“天人合一”一元统一性的表达,即无论面具造型上的多么夸张、离奇甚至“狰狞”,传达的都是精神上的审美意义,而非外形上的“惊吓”甚至“恶心”效果。④
《说文解字》释“傩”为:“见鬼惊骇,其词曰傩。”《论语》黄侃疏:“曰作傩傩之声,以欧疫鬼也。”这种解释非常有意思。“见鬼惊骇”是一种审美活动,非真“遇见”鬼之“见”,所以发出的是表达意愿——驱逐疫鬼的“傩”/“喏”之声,其效果是“欧”,就是讴歌的“讴”——歌唱化/娱乐化地“疫鬼”,也就是“疫”——免疫不顺心的事、倒霉的事,达到冲寿过关、求子还愿、阴阳调和、除灾呈祥的目的。
甚至是最具民间宗教性的傩舞和傩戏,所谓“畜多瘟疫,借神驱逐”,面具艺术的功能也在于“借”,而非“是”。这里的“借”,用中国的民间俗话说,就是“装神弄鬼”——是神灵的装扮而非“化身”,是嬉弄鬼魂而非“附身”。“化身”和“附身”对中国面具的艺术性来说,一定是次要的,甚至是排斥的。
而且,在各种傩祭、傩舞和傩戏活动中,人愿与神愿并存,求福愿与避祸愿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譬如同样是傩坛仪式,就有婚娶、架屋等的“一般庆贺”和驱凶避邪的“冲傩还愿”两种,前者是对人事的承认和肯定,后者则是对神事和鬼事的寄托与敬畏。这种人愿与神愿并存、求福愿与避祸愿同存的情况,说明了面具艺术“天人合一”的内在共同性。
这就告诉我们,中华傩面具造型艺术性,既体现在面具自身之中,更体现在使用面具的具体行为之中。在各种傩活动(傩舞、傩戏、傩歌等)中,面具作为“天人合一”的一元结构的中介,表达的既是表演者与“神鬼”的一元,也是观演者与“神鬼”的一元。换句话说,在中华面具的表演活动中,表演者与观演者都是参与者,戴上面具表示与神鬼“同在”,观看面具也表示与神鬼“同在”。
民间面具活动,即使是宗教性很强的傩戏,民间也有所谓“不说丑话神不灵”的谚语。表演者戴上面具,口出怪语秽言无人怪罪,对神不恭乃至亵渎也见怪不怪,这可以说是人神同一的“天人合一”性,在傩面具活动中的艺术性表现。
唯其如此,中华面具的禁忌并不是神鬼“附身”或“化身”的禁忌,而是对“天”(神灵)的一种禁忌——敬仰和畏惧。
例如流传于安徽郎溪县的“跳五猖”,俗称“五猖会”“跳菩萨”,戴五猖⑤面具和“副身四神”⑥面具而舞。其中,和尚面具用整木挖空,再行雕琢,平时供在祠山架上,跳猖时供人使用。
再如江西婺源傩舞,又称“舞鬼”或“鬼舞”,旧俗每年春节开始活动,至清明谷子下水前结束。其活动结束又叫“收傩”或“封箱”,“在整个演出活动结束后,将全部面具用皮纸包好,服装亦要洗烫整洁,清点装入箱或橱内,然后抬至负责当年保管的大姓人家或狮傩庙内存放……封箱以后就不准再打开了,一直要到十月十五辰时再举行开箱仪式,否则冒犯傩神,灾祸降临。
”[3](P105)可见,即使是跳“鬼舞”,舞蹈活动后,面具也不因“鬼”而烧掉,而是在“大姓人家或狮傩庙内存放”,而且,因婺源“鬼舞”与舞狮同台同时演出,故鬼面具和狮子也一同存放。
这说明“冒犯傩神”与鬼面具无关。鬼面具本身并不是“鬼”,也不存在“鬼”依附面具的情况,而只是表现了对“鬼”的敬畏。这也说明了面具与人的“天人合一”的一元关系,而非人鬼对立的二元关系。
其二,表演而非装扮:中华面具与参与者的身份无关。
中华面具在本质上不是“隐藏”和伪装身份,也不存在欺骗和虚假,它与参与者的身份无关。
“面具”一词不可能被直截了当地翻译成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这个词在英语中强调的是“隐藏”。“摘下面具”形容密探或心怀叵测的人;“戴上面具”“使用假面装束”则是指伪装,甚至是欺骗和虚假。因而,词意的重点是佩戴面具后更改的外观,而不仅是相貌所代表的身份[1](P15)
面具也曾经是古代欧洲戏剧表演的重要道具。贺拉斯在《诗艺》中就说过:“埃斯库罗斯又创始了面具和华贵的长袍,用木板搭起舞台……”说明古希腊戏剧在表演中面具是不可或缺的道具。⑦假面喜剧后来还成了中世纪以来欧洲的一个重要剧种。今天,奥地利山区的“波其顿”舞蹈和世界各地节庆中的假面游行,都可以说是欧洲面具艺术的遗风。这种假面只是参与者身份的象征,或是为了隐蔽身份的手段。
“在纵情狂欢的化装舞会中,不仅性别意识荡然无存,就连通常的社会等级也被颠倒过来。在巴西的狂欢节中,贫民窟中的穷人们向来穿着18世纪葡萄牙宫廷服装,而上等人在这种场合却扮演了反社会体制的角色,如海盗、匪帮、印第安人以及妓女。”[4](P97)可以这样说,西方这种用面具来“掩饰”身份的二元功用,在中华面具中是基本不存在的。
不仅如此,西方古代的面具实用性还非常强,很多时候,面具的功用被用作身体医治的辅助手段,“《英国快报》刊登了一幅图片,是一个戴着长鼻子面具的长发人。实际上这是在中世纪黑死病流行时为病亡者收尸的人佩戴的面具,其特有的长鼻子并不是为了更好地掩饰佩戴者的面庞,而是塞满芳香草药以消除尸体的恶臭并防止传染。”[1](P14)这也是中西方面具一元性与二元性的差异。
其三,钻进跳出:中华面具的艺术性就是表演的合一性。
中华面具的艺术性是造型-表演的艺术性,造型性深嵌在表演之中。当表演者戴上面具“表演”时,不管是引吭高歌、跌打翻滚,还是铿锵亮相、嬉笑怒骂,都是一场“钻进跳出”的表演,他透过面具“表达”的是对“天”的敬仰,观演者透过面具看到的也是对“天”的崇拜。但“天事人定”,天的好恶喜悦,由人来完成。
面具表演与戏剧、舞蹈的“表演”行为是一致的——台上是表演者,台下是生活者。所不同的是,面具表演的参与者借“面具”说话行事,在这里,“我”并非神鬼,“面具”也非“神鬼”,但“我”在为面具“代言——表演”一种艺术性的表演,所以,戴上面具是“钻进去”的表演,摘下面具是“跳出来”的表演。
这就是中华面具的艺术特性,其“天人合一”性体现在面具的独特表演之中。
例如贵州傩堂戏的“先锋小姐”(又称“仙锋小姐),是傩堂正戏《武先锋》的主角,“眉毛弯弯龙戏水,樱桃小口露银牙……收拾打扮多细雅,赛过南海观世音。”其面具造型端庄丰腴、柳眉凤眼、樱桃小口,该剧表现的是兄妹二人大战二龙山的民间故事。
邓婵玉是贵州安顺地戏《封神榜》中的周营女将,其面具造型年轻貌美、凤配战盔,该戏表现的是中国的小说故事。在这里,角色戴不戴面具表演,均与戏曲的穿戴表演并无多大区别,凸显的仅是“天人合一”的娱神性,但“钻进跳出”的表演却成为中国面具表演和非面具表演的“共性”。
在这里,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这与最中国化的表演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的民族特征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作为世界最古老的三大戏剧样式——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戏剧和中国戏曲中硕果仅存的戏曲艺术,在表演体系上不是“化身”的体验,也不是“间离”的表现,而是“钻进去、跳出来”的虚拟程式化表演,一种中华艺术写意原则和精神的体现,这可以说与中华面具艺术在精神上完全一致。
这也表明了,从傩舞、傩戏到舞蹈、戏曲的一脉相承的合理性,以及傩舞、傩戏与舞蹈、戏曲在题材内容上同源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在中国戏曲的脸谱艺术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种“天人合一”性的衍变痕迹。戴上面具跳傩的人(傩祭、傩舞和傩戏),在存在和精神这两个世界中钻进跳出,与戏曲艺人勾上脸谱,在存在和精神这两个世界中钻进跳出,其原理是相同的。
因为,它们都是中华“天人合一”文化结构的体现。
从另一方面说,面具艺术的技巧性,甚至是绝技性,如纳雍庆坛戏在仪式中表演方言山歌,思南傩坛戏在表演中含长獠牙吞吐技巧,安顺地戏中表演者做“刺咽喉”“马上栽刀”等惊险动作,更说明了面具表演人与神鬼的同一性而非对立性。人的绝技就是神鬼的绝技,这与西方古代面具表演所诠释的内容不同。
假面、假面具表演在世界许多地方,如印度、东南亚、非洲、美洲及欧洲都普遍存在,是一种人类文化的共生现象。但很多地方面具的艺术性表现的是“附身性”,而中华面具的艺术性却表现为“表演性”,这正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其四,中华面具在世俗中的“天人”一致性。
中华面具在世俗中的“天人”一致性,指的是“天”与“人”界线的合一性。
傩舞、傩戏与非傩舞蹈、戏曲在节目源(题材内容)上的一致性,说明了面具在娱神与娱人转换上的无障碍性。换句话说,面具作为艺术,在娱神与娱人的功能上是“天人合一”的,具有人神一元的统一性。而傩舞、傩戏的题材内容,很多用的是民间故事,或者历史事件甚或历史故事,如三国故事、水浒故事等,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傩面具的叙事主要是民众生活的“同在”叙事,而非神鬼的对立叙事。
这是其艺术内涵中的一元统一性——“天人合一”的一致性。
譬如安徽贵池傩戏上演的正本戏目,有《孟姜女》(亦名《范杞良》)、《刘文龙》、《章文显》(亦作《章文选》)、《摇钱记》(亦名《摆花张四姐》)、《陈州放粮》、《花关索》和《薛仁贵平辽记》等,几乎都是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与安徽地区徽调等剧种的剧目基本相同,从这种世俗性上完全可见面具活动的世俗性,也可见人神世界的同源性。
又如贵州德江地区傩堂戏的“正戏”分上、中、下三洞戏。上洞戏的主要剧目《扫地和尚》《唐氏太婆》《押兵先师》《点兵先官》,中洞戏的主要剧目《秦童》《于儿媳妇晒谷子》《炯云相公》,下洞戏的主要剧目《幺儿媳妇》《算命郎君》《柳三》等,叙述和扮演的全部是民间民俗故事,充满了幽默和诙谐,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完全是以“人事”说“天事”,面具也就是人脸的夸张和变形,表现出了生动的“天人合一”的统一性。
再如师公戏的面具,有着“十二土地八夫人”,“三百六十都土地,百零八位好夫人”之说,虽是神祗,却有着弯笑的眉眼和可亲的面容,表现了天人的合一性——人对天/神祗的敬仰和崇拜,表达的是对人间丰收的向往和喜悦。
“新春据金制麟狮、龙灯、竹马、彩莲船,间以灯彩,沿门嬉戏,钲鼓爆竹之声震动闾里,盖古人傩以逐疫之义也。”⑧傩的面具之舞,与舞狮、龙灯、竹马、彩船等同时行街活动,也表明了面具舞与非面具舞在“天人合一”的同一性。
中国传统的佛教舞蹈《大头和尚戏柳翠》,后来转换成为民间非常流行的《大头和尚舞》,以及后来的《大头娃娃舞》,面具转为“大头套”,面具的诙谐性被极度夸张、放大,“即看春柳翠,行处月明多。笑著袈裟舞,轻将袅娜驮”,其舞蹈动作也依各地域作不同的风格改变。
如流传于安徽境内多处的舞蹈《大头和尚舞》,风格上就受到当地“花鼓灯”的影响,特别是柳翠的表演舞步及动作主要来源于花鼓灯,其他角色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花鼓灯的动作、舞姿及节奏,并且还以花鼓灯的灯场锣鼓作为舞蹈伴奏。很显然,在这里与其说面具向“大头套”的转换是“娱神”向“娱人”的转换,不如说是“面具”与“大头套”内在的人性与神性的同质性所导致的结果。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天人合一”不是对自我肉身的超越,而是对自我肉身的肯定,一种人为根本的肯定。在这种意义上说,中华面具通过各种艺术行为,不是对人的肉身的超越,而是对人的肉身的肯定——是“天人合一”的一元性肯定。因为,就是中华的傩面具与非傩面具在艺术性上也是“同质”的,即使在宗教性上也非对立的,其不过是在天人关系上的一元结构转换,而非人神二元的对立性“变异”。
可以这样说,中华面具艺术的“天人合一”性,是中华面具艺术的本质规定性。历史上,不少傩舞、傩戏,或者佛道舞蹈向世俗性的舞蹈、戏曲的转换,在本质上是中华面具艺术的这种一元的统一规定性所致,而非商业与市场化的结果,这与西方近现代发生的将一些面具舞蹈作品因商业化由娱神向娱人的改变,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最后,我们说,中华面具并不是“神器”,但对它却如神鬼般地敬畏;中华面具也不是“假面”,但对它却存生活般的真诚;面具更不是“玩具”,但它却带来游戏般的欢乐。中华面具最艺术地体现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表达了人类存在世界、生存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相互纠缠和共生的关系,它与西方面具形成了显著的差异性。
“我们就得承认,跟语言中的词语一样,每一副面具本身并不具备其全部意指。意指既来自于被选用的义项本身的意义,也来自于被这一取舍所排除的所有可能替换它的其他义项的意义。”[2](P19)这是中华面具艺术的哲学所在:“天人合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