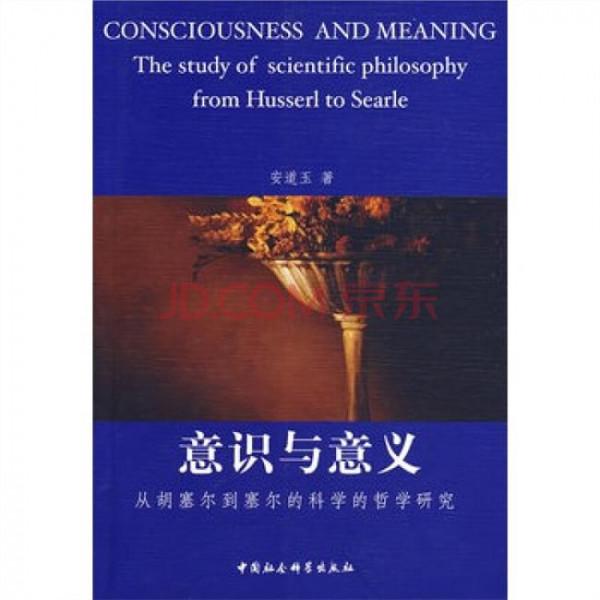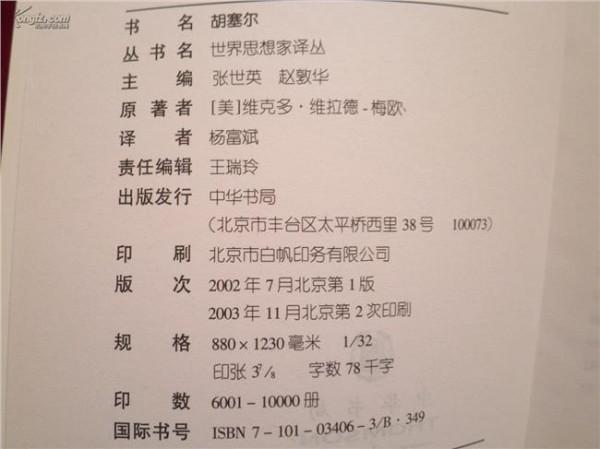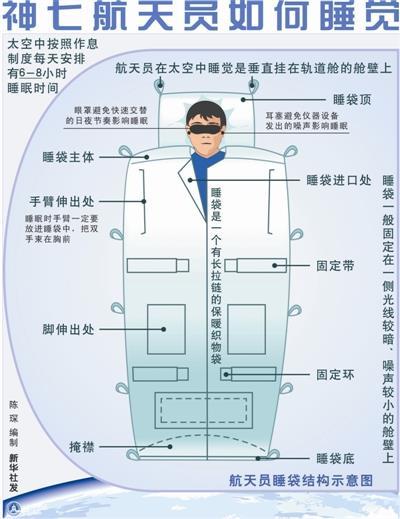张志扬哲学 张志扬:生活世界中的三种哲学生活――中国现代哲学面临的选择
“中国现代哲学”,不是“现代中国哲学”如“新儒学”、“马哲化的意识形态”,当然更不是“西方现代哲学”如“德国现代哲学”或“法国现代哲学”或“英美现代哲学”的中国版。它是什么,仍是一个问题。但有一条路该走则是无疑的,那就是,从西方哲学史启示与理性、超验与经验(先验)两极化的绝对本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反反复复重重叠叠所隐喻的本源上的“悖论偶在”开始,回复“现代之为现代”的既非绝对本质主义也非虚无主义但同时是两者悖论式相关的偶在空间,以察看中国现代哲学应有的身位。
换句话说,能走出西方哲学史而携古代于“现代”,作为参照(不是尺度),中国现代哲学自有容纳中外古今哲学的偶在空间──为“现代”正名。我们了解西方的程度远甚于西方了解我们的程度。其所以如此,除了百年来被动承纳的厚积薄发,“和而不同”、“有容乃大”、“静为躁君”的中国古训仍是值得遵循的现代原则。
先从西方哲学史的现象学描述开始。
古希腊前苏格拉底,问天假神而命“自然始基”;苏格拉底则问人爱智而言“哲学”,使哲学的地位尽人智而达到“哲学”的顶峰(不在柏拉图的意义上):虽有神相启,但敬而远之,因而哲学以“无”求“知”的“问”尽呈“自然之光”遍帔“智”的华林,没有人敢在此“问”下惟我独尊。
柏拉图将此“哲学”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开了工具理念的先河,为亚里士多德所完成。(注意理性原初的偶在形态:隐含“不”的“知向理性”与显明“是”的“知得理性”。容后祥述。)
希腊化-罗马时期,随着城邦走向帝国,空间的扩大与民族的倾轧提出了统治与救世的双重要求,哲学分解为科学与伦理学,而更大的信仰空白为宗教所填补。中世纪,坏说,哲学降为神学的婢女;好说,哲学被神学融为一体而精制(逻辑化)。但由此,神学走上了形而上学神学的道路。必然性的上帝更远离人世的苦难,末世论的救赎完全屈服于进化论的未来时间观,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带回“中心时间”,人“因信称义”的救治才是现世可能的。
文艺复兴,“人义论”取代了“神义论”,即以人的自我或属性为观察并统摄世界的根据,把神的人化取代为人的神化。启蒙运动,其新古典时期,理性综合身心主客而成为“绝对精神”,形而上学哲学几乎又登上了王座(在柏拉图的意义上),以黑格尔为最。
尼采拆毁了“上帝”的形式理性伪装,隐话显说,拥哲学拼命向“超人”一跳,“权力意志”虽在高峰,不但没演成“纪念碑”,反落为“主体的隐喻”。随之江河日下,“真理”拱手交给了科学,剩下人身上的种种“存在”与应变的“方法”,且大多从数学、语言学等拿来,唯隐含对十字架上帝救渡的期待之思。
但其中也透露出一点消息,后现代哲学在重审“现代性”前提时,有一种秘传探询的趋势,那就是带着“悖论”意识回到苏格拉底与第欧根尼之间(“认识”隐含“改变”),使苏格拉底式的“无知之问”从表面的“自然之光”下透射出神秘的的“生成界面”──“悖论”。
首先是生成的“时间悖论”及其“根据悖论”的理性限制,然后是“人两难-神悖论”(“上帝是集中的悖论”)的信仰宽解。可惜,它被后现代主义“怎样都行”的虚无主义喧嚣淹没了。
至使蔑视现代智慧(包含悖论启示)的列奥 · 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不客气地说:“由于哲学的解体,今天有利于哲学的争辩是不存在的”,哲学的荣誉已经丧失,“哲学缺乏成果跟科学的巨大成功的对比,引致了这种丧失。科学是今天唯一堪称人类知性完善的理智追求。对于启示,科学是不偏不倚的。哲学自身已经变得摇摆不定。”〖1〗
这还只说了一面。我再重复其关键之点。
古希腊理性(以“知向理性”为主)有两大自然特点:一是人自知无知(知不可知的“知识”);一是完善知识只能在永不完善的追求中(得不可得的“德性”),总称“知识即德性”。至于希腊理性的政治哲学本质即哲人与民众的上智下愚、上尊下卑的“正义”关系以及“工具理性”(即知得理性)的发端,应算在柏拉图的账上。
两大特点虽然都属“人的智慧”(注意,隐含悖论),但无疑受着“神的智慧”牵引,决非人单面地自以为是,也决非神单面地蛊惑迷信(仍在悖论式的张力中)。
“悖论式偶在”,乃神的存在形式,人的限制形式。这些括号中的话其实是希腊智慧天真地坦诚“自然之光”下秘传的悖论裂隙。所谓辩证法,作为表象特例是可取的,若作为普遍形式则沦为“仿神化”的自欺,至于黑格尔“辩证法”,只能看作对悖论的意识形态化埋葬。(提示:悖论不同于矛盾,不能转化统一地绝对,只能两难相关地限制,断裂是不能消除的。)
自“人义论”始的启蒙理性,在祛魅“神义”时,连因神的启示而限制人的理性的“限制”也一同“祛魅”了,即“背弃”了。因而启蒙理性犯大病焉:理性为了证明自己至高无上的完善能力,极端地膨胀了作为手段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结果手段高出目的成为理性的主宰;由此而来的是,本来起于地中海区域的启蒙理性,随着技术理性的发展,迅速膨胀为全世界的唯我种族中心主义,即对世界其它多元文化实行了粗暴的惟我独尊的“殖民”霸权。
当然,它背后隐含着的仍然是穿着地中海民族服饰的“一神教”(在“诸神之争”中)戒律:“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2〗
但是,此种理性的哲学形态即“形而上学”屡遭自我的颠覆,因为那被理性确立的“本体”不断从王座上推翻下来,以至愈来愈暴露出虚无主义的马脚(“自然之光”下的悖论裂隙只有在不意识的意识独断时才反讽出虚无主义特征)。于是尼采有“虚无主义即颠倒的柏拉图主义”诊断。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内部争霸的惨痛教训,外部反霸的民族兴起,基督教-理性中心主义的迷梦破灭了。
施特劳斯因此重提休谟、雅可比的命题:“理性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怀疑主义,最后走向虚无主义。”〖3〗因为,“理性主义本身建立在非理性、非明证的假设之上;无论它看上去多么有力量,理性主义实际上是空洞的。”〖4〗结论或救治的方案是:回到古希腊理性,具体地说是回到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注意前述,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理念化,即开始切断或掩盖下面的悖论裂隙)。
苏格拉底遵循的毕竟还是人的智慧。施特劳斯因此责问苏格拉底:“你自知人的智慧不完善,为什么不上升到神的智慧?”〖5〗可见,施特劳斯的真实目的乃在于,只有苏格拉底像摩西那样接受并传释耶和华的启示,哲人与先知合二为一、理性与启示融为一体(其实是理性听命于启示),人的理性才不陷于空洞沦为虚无主义(隐言:人的德性生活才呈现上智下愚不移,人的政治生活才呈现上尊下卑有序,是之为“正义”)。
理性与启示的结合意味着哲学的本质返回到政治哲学即政治神学。其隐秘的目的在于恢复犹太教原教旨中心主义(显说以“希腊理性”)。这是施特劳斯的“回头是岸”的解决办法。
你可以不接受他的解决办法,但施特劳斯对启蒙理性以来的现代理性的批判,其切中要害(即虚无主义)则是无庸置疑的、也回避不了的。
正因为如此,一个尖锐而迫切的哲学问题便摆到了现代哲学面前,那就是,
A 过虚无主义的生活好不好?
B 不过虚无主义的生活,再回去过绝对本质主义的生活行不行?
C 如果两者拉锯形成两极震荡,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如何走
第三条路?
我认为,这连带相关的三个问题,是当今世界亟待解决的哲学、政治哲学、社会理论难题。
(奇怪的是,不管前提如何,现代西方、俄国与现代中国、日本,几乎有同步的迫切性。)
“只过虚无主义的生活好不好?”
所谓虚无主义,在哲学上就是没有“本体”、没有“绝对同一性”、没有“永恒在场性”,直言之没有“神”。因而在生活中观念纷呈、行为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价值”与“公共权威”,一切都是相对的,可置换的,恁怎样都行,只要你能占有购买一切的手段。因而,除了手段暂时能控制的游戏规则,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神圣原则。
虚无主义还有若干变种,它不像上述原形易于辨认。对于我们最难理解的就是“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原则上是进步的,有必然规律和终极目的,但过程中,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当终极目的愈来愈推到“灰色的云雾”中去时,所谓必然规律就只表现为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机缘决定论”。
所有这些进步、机遇、转换,其实正是背弃了开端绝对性或丧失了终极目的性的相对主义口实。唯理论的自明前提是预设的,分析手段的形式化仍不过是强化着技术理性,至于经验论、实用主义更不用说了。
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时间、地点、条件,尤其是条件(包括作为条件的技术与技术理性),成为决定者、主宰者。它今天表现为全球技术一体化,一切硬道理中的最硬的道理。在这个意义上,虚无主义是用最实在、最强大的技术主义-欲望主义实现其自身的,它们互为其表里。
伴随技术主义(万能)的是行为、思想、心态之普遍的相对主义欲望化即物化。也就是说,“技术”在今天成为普遍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与“货币”同格,表明:“技术”与“货币”其实都是“工具理性”的物化中介。可以想象,凡被它所购买者,哪里会有绝对的神圣价值呢?
总之,当今生活世界似可用三个表达式概括其现代思想知识状况:
A 就社会构成而言:技术-欲望-大众化
B 就理论形态而言:相对主义 规则系统
C 就思想性质而言:技术理性-相对主义-历史主义= 虚无主义
C当然是A、B的归结式。它无疑比胡塞尔当年分析的“欧洲科学的危机”更深刻。胡塞尔仍然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科学的危机,或换成另一个犹太人施特劳斯批判的说法,即是用理性主义的方法解决理性主义的危机。既然理性主义必然导致虚无主义,理性主义的方法又怎能救治虚无主义的危机呢?在意识现象学中,还原的科学理性还是理性,该缺乏的还是缺乏着(信仰),做不到的永远做不到(绝对同一性)。
例如,胡塞尔的“自我-纯意识”及其“还原”并不能克服笛卡尔早就揭示了的“自我的点积性”或“死的根性”(笛卡尔);何况“自我”在世界中还有一个先行的生成过程(海德格);何况还有“他人的自我”;何况还有“晕圈”外的“无意识”(利科)等。
胡塞尔照样对付不了“时间悖论”和“根据悖论”。
〖6〗同样是犹太人,胡塞尔并没有走到施特劳斯所要求的地步──理性与启示的结合。而没有超验的启示维度,生活世界的残缺与虚无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到海德格,他的存在论虽不是神学,但却隐含着自身的限度及其对上帝的期待。
至于其它一切现代意识形态或种族中心主义,更是明目张胆地借技术来购买自我的普遍主义或世界化。例如,西方正是借自己的技术强势来推行基督教中心主义。它们不意识其中的悖论,即绝对中心主义靠的是相对主义手段实施,因而“得即失”是不可避免的。
“得即失”不仅在于内部的“自我剥夺”(技术剥夺神启),还在于外部的“剥夺剥夺”(后来居上的主奴辩证法)。于是,世界史仍呈现为“堆满头盖骨的战场”(黑格尔)(注意,它不是修饰语,而是两个实实在在的战场:堆满了精神头盖骨与肉体头盖骨)。
是对话走向割据,还是独白走向专制,至少人类眼下,没有谁能判断其是非,剩下的唯有选择,仍然是实力较量,还是在“诸神之争”中。
“再回去过绝对本质主义的生活行不行?”
不管承不承认进步,今天的“民主”、“平等”、“自由”,是从“君主”、“等级”、“专制”的有限性所导致的自我毁灭中衍生出来的;即便今天的“民主”不过是“隐蔽的等级制”,“显白的”毕竟是监督的民多了,独裁的王少了,也仍然不同于“天命世袭”的贵族等级制和“朕即国家”的君主专制。
更主要的是,“智”的范围(包括“智”的类型)能否再收回到“一个人”的权威正义(正名)中?背后其支撑的“一神教”的“神”相应地更先行收归到“诸神之争”中的哪一个“神”呢?换句话说,“神──先知──哲人──僭主──民众”这样一个(“施特劳斯派”)绝对本质主义钟情的等级秩序由谁来决定呢?能否按《圣经旧约》的“犹太先知学”说了算?或者按“理想国的哲学王苏格拉底”说了算?
恐怕连施特劳斯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
当然还有其它类型的绝对本质主义,例如中国“天人合一”的“孔孟之道”,及其下设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尊下卑有序”、“上智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忠孝仁义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