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在论张志扬 张志扬:有意指的“意识”与无意指的“存在”——“3H”或“H
“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黑格尔、胡塞尔都是这样规定“意识”的。如果,意识不是对某物的意识,意识就无意识了,确切地说,是无所意识了,意识陷于黑夜。古希腊自然把“意识”叫做“理性之光”——它必须照见什么、呈现什么。
所以,“意识”的“意识式”或“思维式”即“表达式”为:
“是—什么”(Bewusst--sein)。
(意识中的-sein如何意识为意识者Seiende,如何意识意识者的意识着seined,以及它们如何把意识作为显现本身显现出来sein,等等,是我们眼下意识的内容。至于意识中的-sein同那个神秘的Sein处在怎样“听—说”的无意指“显/隐”关系中,暂时还是晦暗不明的。)
“什么”必须“是”出来、呈现出来,构成命名与定义、命题与判断。“什么”乃是意识“意识到”或“意向到”的“对象”(谓述化中的主词)谓之“表象者”或“显现者”或“在场者”即“存在者”。由此自亚里士多德将“逻各斯”转变为“逻辑学”以来,“语法结构”与“事物结构”的对称性,为“意识结构”提供了自识反思的可能性基础,以至“意识思维——语言逻辑——存在构造”成为形而上学的“存在者论同一”或叫“本体论同一”。
注意,呈现的或“是”出的“本体”既可作为“存在者根基”(“一”)也可作为“存在者整体”(“全”)终归是作为“最高存在者”规定的。
前苏格拉底的最后一人巴门尼德提出了“思想与存在的同一”(Denn Eines und Dasselbe ist Erkennen und Sein.)。(1 Parmenides.Ⅳ.Uebersetzung,Einfuehrung und Inderpretation von Kurt Riezler.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nt am Main 1970. 此条的德译文有多种译法,例如海德格尔把它译成: Wie Denken und Sein zusammengehoeren.
意即“思想与存在相互审听归属”。)在形式上可算作“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开端”,黑格尔就这么认为的;但海德格尔则另有说法:“西方思想史的开端”。
其间解释学类型与倾向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层次与方向上的。往后再回到这里详述。近代笛卡尔之后,更自觉强化了“自我”之“意识”的主体性绝对性——即用“怀疑”显现者的方式确认“作为显现的思维”本身,从而把“怀疑”既认定为意识或思维的“本性”又看作意识回复自身的“方法”。
它的影响是深远的,黑格尔意识的“否定性”即只在“否定之否定”中自我肯定,来源于它;胡塞尔意识的“悬置”或“还原”,也来源于它。
在这样的“意识”面前,没有纯粹的自在之物。所谓“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句话如果要有意义,只能是纯粹的信仰,不能究理的。一究理,它就无法自圆其说了:那个“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意识是怎么意识到的?意识到,“客观存在”已经“以意识为转移”了;不意识到或没意识到,意识何以妄断“客观存在”?“唯物”与“唯心”两极相逢。
所以,问题不在于客观存在一定要不以意识为转移,绝对自在的客观存在对人等于无,而在于客观存在对人或对意识存在的那个神奇的无法同一的“差异”关系或从此“差异”中生成的悖论方式。
但所有这些微妙的关系在对它惊奇的闪现后不久很快被意识的“是什么”方式给遮蔽着了——例如“是什么”本身的“不是什么”就被显现遮蔽着,或者,用辩证法“去蔽”无非把“当下即是”的遮蔽转换成“过程即是”的遮蔽,直到如今还晦暗不明。
所以黑格尔说,“以前以为是自在之物的那种东西实际上并不是自在的,或者说,它发现自在之物本来就是仅只是对它(意识)而言的自在。”(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论”贺麟王玖兴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0页。)于是可以上推到柏拉图的“理念(理式)”之后(用海德格尔的话说,“逻各斯”转向“逻辑学”之后),“意识”——“是什么”的光照就已然遍被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华林。
结论是自然的,在“意识”的光照下——即意识必然是对某物的陈述或判断“是—什么”,那么,其意识到的“存在”也必然“存在者”化了;即便“存在”作为“存在者本质”或“存在者整体”也仍然是“存在者”化的“存在”——“存在论同一”(其实是“存在者论同一”)。
换句话说,在有意指的“意识”下只有有意指的“存在”即“存在者”。特征是,1、一即全,时空充实完满;2、持存在场显露无遗;3、归根结底,没有黑暗者、没有深渊者,如上帝“全知全能”。
“柏拉图主义”或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形而上学史”,无非如此。然而事实是,无非如此的“本体论同一”之如此固置,不过是遮蔽着裂隙的固置,以至必须或难免(不得不)用一次颠覆性的破坏才能显露形而上学的危机——“本体”或“本体论”更迭。
于是,黑格尔抽身出来把“形而上学”对置于否定的环节上不怕反讽地说,“形而上学史”成了“堆满头盖骨的战场”;尼采则把“柏拉图主义”干脆叫做“颠倒的虚无主义”;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对“存在”的“遗忘”还不是“抛弃”,颠覆性的破坏不过是“遗忘之存在”扭身而去的召唤。
尽管西方形而上学史每个阶段的“本体”——“最高存在者”不断被下一个阶段的“本体”——“最高存在者”取而代之,黑格尔为什么敢于断言自己的“绝对精神”不但不会被取代,而且应该成为所有以前“头盖骨”的最后收集者或“最后归属者”,以至它真的是“上帝”或“基督教世俗化的完成”(施特劳斯语)?
非要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因而你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过是“存在的一种解释”而已——“存在即是解释”——“超人”也不过是绝对存在的“权力意志”的轮回解释者。
看得出来,尼采与黑格尔正好是“人义论”之“最高存在者”的两极——代表上帝之显白化“绝对精神”和对抗上帝之虚无化即隐匿化“权力意志”。
海德格尔是应了这一绝对对立的“危机”而后出的。换句话说,如果海德格尔走不出来,现代哲学(包括英美分析哲学)充其量只是笼罩在前两者或主要笼罩在尼采“存在即解释”的虚无阴影之下。
既然迄今为止人所意识的“存在”无一不是“存在者”又无一不是“存在者”的颠覆,那一定是“意识对存在的存在者化”为“存在”所不容,其间的“差异”何在?但是,海德格尔最初的问题方式只能是:作为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第一范畴的“存在”,为什么只能是“存在者”,“唯存在者存在——此外更无物矣”,这个“无物”是怎么回事?(3《形而上学是什么?》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译本,上海三联1996年第137-138页。
)
或许这个最初的问题被惊奇所困扰,有点问非所问,但问题所指向的“那个场地”(不是“什么”)——应该有“裂隙”为意识外生成的“黑暗”之源,则为海德格尔一生所魂牵梦萦:
为有意指的“意识”所意指不到,而为无意指指号的“人”被传召到的无意指的“存在”。
——此系何处?
——今行何处去了?
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西哲界就已登场的“老问题”,可惜,像其他诸多问题一样不了了之。也就是说,在我们这儿,碰到了就是知道了,知道了就是解决了,直到新一轮的震荡又在我们身边发生,仍是知然不然地不了了之。所以今天的学术表现便以“是/在之争”为“新”。
“重复”是记忆的形式,也是遗忘的形式,归根结底是“以记忆为遗忘的形式”。在施特劳斯之后,这种奇怪的姿态重新唤起了我的兴趣。先是回顾“中国现代性思潮中‘存在’的漂移——‘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马克思/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后是重返“林中路”:
林中有许多路,有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即便人迹所至,也多有歧途。路,不走不在,走也未必在,要不,人怎么会迷失在他们的常路之中?每人各奔前程,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似,然而只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护林人懂得什么叫做在林中路上。(仿海德格尔《林中路》题言)
作为重读的个案研究,本文暂限定于“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及“H-Kehre”(“海德格尔转折”)。
重新解读
一、简单回顾康德
笛卡尔的“意识经验”是用怀疑的方式指向自身或呈现自身。因为意识能够怀疑任何非意识东西存在的合理性而在怀疑中把“意识本身”显现出来,确切地说,怀疑就是意识的自我显现,一个以否定为肯定的自我肯定,后来黑格尔把 “否定之否定”规定为意识自身的“绝对确定性”。
这一获得极为重要。它是对“意识向外意识对象者”的怀疑而显现“意识自身”的“自我意识”的第一次意识。难怪黑格尔把他赞颂为新哲学的“陆地”。
然而笛卡尔的“知性真诚”更在于,他同样意识到“意识”有“死的根性”,它表现为“时间缺口”或意识的“点积性”。意思是说,即便意识的本性是对非意识怀疑而绝对自我认同,但“怀疑之思”与反身性的知道怀疑的“反思之思”,其间仍有“时间缺口”,原因在于“自我”是时间性的“有死者”。
弥补这个“时间断口”而维持同一的,内只能靠“记忆”,外只能靠“上帝”。(4参阅JACOB ROGOZINSKI: Wer bin ich, der ich gewiss bin, dass ich bin? vgl.
Tod des Subjekts? Hrsg. von Herta Nagl-Docekal u. Helmuth Vetter; --Wien; Muechen: Oldenbourg, 1987.)
康德向来被看作“启蒙大师”,据说他伸张过“敢于明智”。康德的“明智”是明智到——休谟经验不可僭越,欧陆理性必须坚持——他不得不明智地走中间路线。经验仍然是“自在物”给予我们的方式,同时也是阻断我们的方式,经验之所以接受“自在物”的给予虽不是“物本身”却有普遍必然性,那是被给予经验的形式属人的“意识”有其自身的“逻辑先验性”。
人依此为经验或自然立法。但这个“先验立法”有一个限度,即只限于“经验世界”的规定,其界限就是超越到“超验域”理性必陷于“二律背反”(“二律背反”的断裂已经暗示了深藏不露到不可知的“自在”的深渊——这是康德的“知性真诚”所在)。
换句话说,“意识”(含感性、知性、理性)虽可独立支撑但不可任意僭越,每个环节都有其自身的限度。
我以为这就是康德“意识”之“明智”的表现,或叫做“知性真诚”。然而,任何一方,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只要想追求彻底(偏爱唯我独断),他们都不会满意康德“意识”(对“自在物”)的“自主”与“限度”的所谓“二元论”。康德后继的不同形式的“彻底派”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是大家熟悉的。但当时还有另一类批评者,已被人遗忘,今天特别值得重提。
有人指出,在康德的“意识经验”中首先犯了两个明显的错误:(一)康德把自己的“批判哲学”变成了一种“垄断批判”的哲学,因为他在对象尚未被给定我们之前,就形成某种关于对象的东西,而且还是构成对象的“先验性基础条件”;进而(二)其“超验哲学”把人的思维建立在不可辩驳的确定性(Gewissheit)之上,而不是从易错性(Fehlbarkeit)和不确定性(Ungewissheit)出发。
本来“易错性”和“不确定性”两者实际上是决不可能被排除的,正因为康德知道这两点,他才事先在前提的设定中予以独断地排除了,并以此把这哲学作为“基本原则”来建立。
据说这是当时的“时代病”。柏拉图则是这类要求者的最早代表。“启蒙哲学”本来是趋近对象的,不管这对象怎么难。
结果,康德哲学使趋近根本成为不可能,因为拐进了误区。结论,康德不但不是启蒙大师,反而是反启蒙者。(5引自微阑《阿里斯底波》。维阑(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
也有译作维兰特。)是德国启蒙运动后期的重要代表,史称德国小说的开创者;他创办的著名评论刊物《新德意志信史》在德国文化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担任爱尔福特大学哲学教授期间,维阑研究古希腊史学和卢梭哲学,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二十二个剧本,晚年转而从事古希腊、罗马文学翻译(翻译了阿里斯托芬、色诺芬、贺拉斯、卢奇安、西塞罗等人的作品)——作为康德的同时代人,其色诺芬翻译据说是为了清除康德哲学的流毒。
维阑的小说创作都有思想意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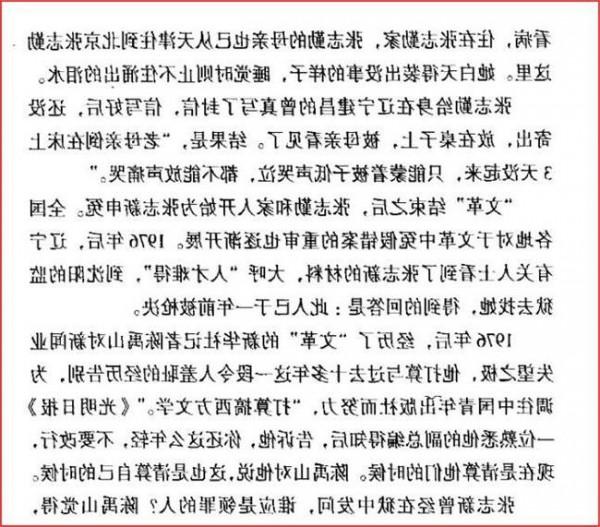



![>滦县张志国 张志国[西丰县原县委书记]](https://pic.bilezu.com/upload/6/ec/6ecf58f26bc1d80536d36331b1e59289_thumb.jpg)
![>西丰县张志国 张志国[西丰县原县委书记]](https://pic.bilezu.com/upload/2/38/23862e17ef4c107b5cb9a8509524dd95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