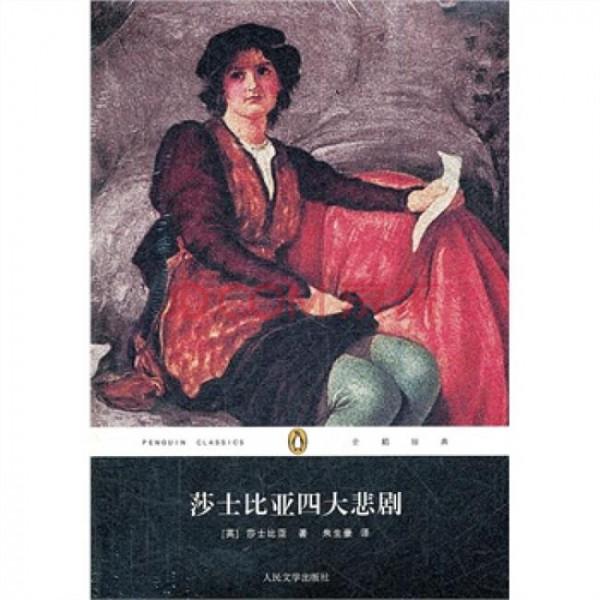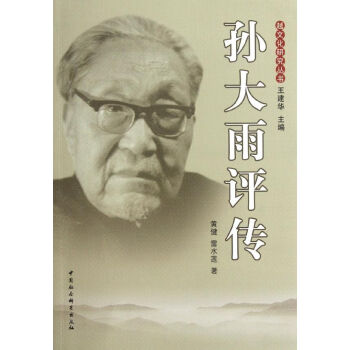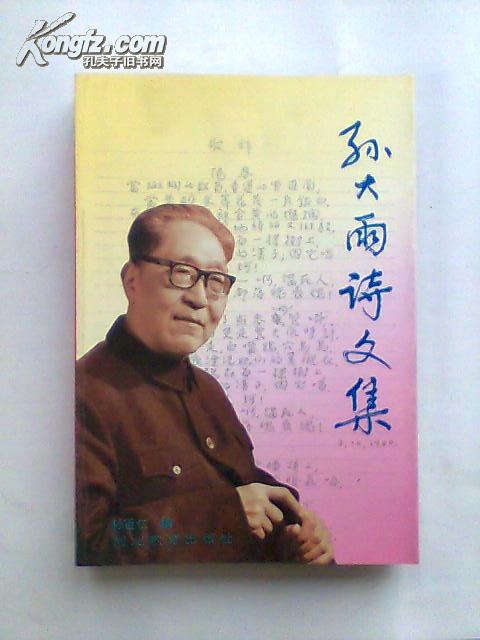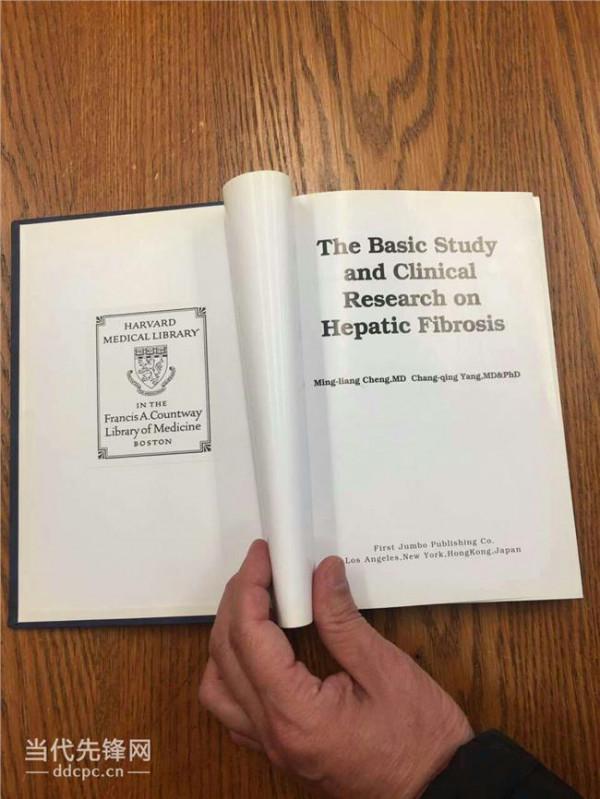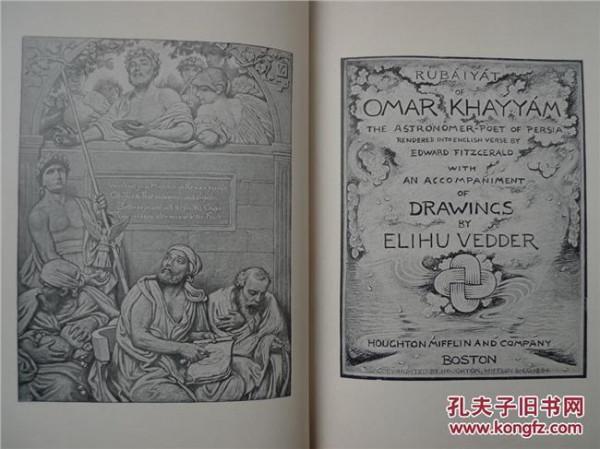莎士比亚孙大雨 孙大雨和莎士比亚戏剧翻译
青岛大学时期,孙大雨结识了京派文学主将、小说家沈从文,殊为可惜的是我们已无法知道两人交游的史实,仅从沈从文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理解的深厚,沈从文在这篇短文中似乎已指证了孙大雨在青岛被解聘的遭际,更是对他此后人生命运沉与浮的最早预言。
1934年,林讲堂主编的《人间世》开设“人物志”,就是以名人写名人,列入其中的大都是近代以来学界的翘楚,而立之年的孙大雨侧身其中,而且是沈从文执笔为他“画像”的《孙大雨》一文。
“十分粗率的外表,粗粗一看,恰恰只是一个人的坯子。大手大脚,还在硕长俊伟的躯干上,安置了一个大而宽平松散的脸盘”,沈从文接着这样写,“然而这个毛坯子的人形,却容纳了一个如何完整的人格,与一个如何纯美坚实的灵魂!
多才,狂放,骄傲,天真。倘若面对这样一个人,让两者之间在一种坦白放肆的谈话里使心与心彼此对流,我们所发现的,将是一顆如何浸透了不可言说的美丽的心”。或许因为经过文学表达的润饰,或许有中国史传统扬善隐恶的影响,沈从文也许给予了他笔下的人物过多的赞美,但是如下的叙写则能看出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的敏感,他的笔触直指人物内心和灵魂,把那人生悲喜的根子在这里都作了传神的展示。
在沈从文的眼中,孙大雨比许多人认识“美”,而许多人比他更明白“世故”,他说孙大雨是一个“有脾气有派头的人”。他继续写到:他身边那些温顺,中庸,办事稳重,应对伶俐,圆滑如球而抹油,在社会上处处占上风的人提及孙大雨就是“大雨吗?”话语里埋伏了点嘲诮,不同意的神气酿在嘴角的微笑里,沈从文写道:“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人平素就是怕魔鬼,怕高山,怕风刮,怕打雷的人”,因而,孙大雨在他们面前简直是一种“恐怖”。
这样不厌其烦地去引证,只是深味于沈从文的精到,“大而宽平松散的脸盘”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孙大雨的印象,孙大雨为人直率,绝不同虚伪和懦弱谋妥协,这使他时常陷入孤立的境地。沈从文说他常常在课堂上与大学生舌战,在大街上与人作战,少数理解他的朋友对他这种精力耗费的用途无一不感到忧虑,而这少数的朋友中就有徐志摩和梁宗岱。
沈从文说,没有他们,孙大雨回国后的成就也许难以取得,甚至“也许早就绝望自杀了”,我们难以知道这后一句话又隐藏了多少难堪的人生故事!
孙大雨这种充满入世应战的精神其实也在一步步使他从诗人、学者、教授的生活圈淡出,导引他走向人生的另一座也许本不该由他领略的峰巅。
1941年底,孙大雨来到大后方的山城重庆,任教于**政治学校外文系,次年,他又加入国民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孙大雨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书生到政治。客观地说,此时的孙大雨对国民党政府还是投了信任的一票,然而大后方的四年现实,以孙大雨的性格与处世原则,使他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信任,他批评,他痛骂,表示对当局的憎恶,他拒绝陈立夫请他到教育部任职的邀请。
1945年底,孙大雨回到上海,应聘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次年,闻一多被暗杀激起他的愤怒,经罗隆基的介绍,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后又参加了 “大教联”(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的简称),他走出了象牙塔,以实际的行动把政治的砝码移到了**的一方,他曾代理大教联**,在白色恐怖下民盟转入地下斗争,孙大雨领导的大专院校包括中学盟员继续活动直到上海解放。
1949年,孙大雨欢呼胜利的到来,因为,这里还有他的一份并不容忽视的功绩,他积极送独生女参军,一方面任教复旦,一方面成了社会活动家,各种委员、主任的头衔纷至沓来。
但政治之路决不会是一片坦途。孙大雨在迎来他的人生峰巅时就已削就了下滑的万丈深渊。
1949年5月27日,正在参加一个聚会的孙大雨等接到“大教联”开会的通知,他赶到会场,原来是原“大教联”成员李正文随部队回来了。久别重逢,他们想的是了解解放区的情况,不想,穿着军装的李正文匆促地宣布改选“大教联”干事会,这使孙大雨等感到莫名和吃惊。结果,“大教联”中的民盟成员在干事会中全部落选。孙大雨后来说落选事件对他打击很大。此后孙大雨就开始了近十年的持续不断向**和上海各部门上告的征途。
孙大雨同样没有摆脱传统人士的心态,他也走上了上书直言的老路,就是那写给**的皇皇的八万言书。当年孙大雨在上书时,罗隆基极力劝阻他,**也不止一次出面调解劝说,然而,孙大雨一经起步,就不再回头,他性格中的执拗、倔强在此显露无遗。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与他同一时代的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聂绀弩后来有咏胡风的诗句:“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读来让人无限感慨。胡风是用三十万言换来三十年苦难,而孙大雨是用八万言书换来二十八年的磨难,同样让人感喟万端。翻开一部中国历史,历朝历代上书者不绝如缕,但沿袭而下的大多都是血腥的结局。
也许孙大雨对十五年前解放区那场影响深远的整风不甚了了,也许他对解放以来针对知识分子的历次运动没有警觉,对“高价征求批评”(时任《文汇报》社长徐铸成语)感奋不已。6月1日,复旦党委邀请孙大雨参加整风座谈会,他说:“响应党的整风号召,我就是走在路上跌脚,摔死也要来的。
” 6月8曰,他的长篇发言刊登在《解放日报》上;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上海乃至国内各大报纸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中点明批评孙大雨是“顽固不化”右派分子;此后孙大雨被内定为极右分子;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和资格,又被推上被告席,以诬陷罪判处六年徒刑。
“**”中,他又一次被投进监狱,且加上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孙大雨把自己的人生盛年压在了政治的天平上,在政治的滩头上历险,他惨痛地失败了。
从1961年第一次服刑期满回上海至“**”前,数年间孙大雨无业在家,生活上除偶尔有市委统战部和民盟市委不定期补贴外,全靠妻子的退休金度日。
历经坎坷的孙大雨整日呆在斗室,忆及人生世相的一幕一幕,他又想到自己三十年代翻译莎剧的夙愿。是的,他的第一部莎译历经战乱,从1935年译竣到1948 年出版相隔十余年,而此后,为了革命斗争,孙大雨没能再重操莎译宏业,解放后,历次运动的冲击,政治生活的波浪,他也无暇顾及早年的夙愿。
而今,面对早年自己购得的无数莎剧版本,孙大雨又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莎剧绚烂缤纷的五彩世界之中。青灯之下,黄卷之中,孙大雨在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越过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回溯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梦幻,诗人复活了,只不过带着如许的沉重:再度进入莎士比亚的迷幻世界,只不过外界条件让人难以想象,还有屈原、李白、乔叟、米尔顿,他在一座座文化峰山之间穿梭、游移、淘洗、沉醉,架起一座座文化之桥。
他陆续用诗体译出莎剧集注本五部:《罕秣莱德》《奥赛罗》《麦克白斯》《暴风雨》《冬日故事》。
孙大雨当年曾庆幸自己走出了象牙塔,而今,重进象牙塔,他心头一定会有别样的滋味。
“**”爆发了,孙大雨的精神驰骋也不得不中断,他又开始了更为惨酷的人生际遇。
第二次出狱后,看看空空的四壁,孙大雨几乎绝望,几十年来收藏的书籍包括莎士比亚剧作、字画文物等被洗劫一空,万幸的是,家人冒着风险藏起来的几册莎剧原作还在。从此,孙大雨白天接受劳动改造,每当夜幕降临,就拉上厚厚的窗帘,沉浸在莎剧的艺术世界中。就这样又译出《罗密欧与居丽晔》和《威尼斯商人》两部简注本。
从1934年起,前后半个多世纪,断断续续,孙大雨共译出八部莎剧。由于孙大雨对莎剧的诗剧或戏剧诗的性质的把握。因此,孙大雨认为将莎剧译成散文话剧有背原作风貌,虽然距理想还有距离,但自信要比较接近于莎氏原文风貌。
?輦?輰?訛 在众多的译剧中,除林同济和卞之琳受孙大雨的影响用音组构成的韵文翻译莎剧外,“其他的译本,所有梁译、朱译、顾(仲彝)译、曹(未风)译、曹(禺)译、方(平)译……都把莎剧译成散文(或实际上是散文,尽管形式上分行)的话剧……”?輦?輱?訛 尽管关于莎译理论上还有分歧和争鸣,孙大雨更近于原作风貌的莎译,应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与评价。
1967年,台湾文星书局出版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四十巨册,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校订、补译,推出以朱生豪为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和朱生豪的全译分别成为海外和大陆较为人们熟知的版本。
1991年始至今,孙大雨的八部莎译以各种版本和形式出版。今天,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孙大雨译《莎士比亚戏剧八种》,其中,六部集注,两部简注,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既容纳了几百年来世界莎学研究的成果,也包含孙大雨自己的很多创见,许多争论的问题在这里孙大雨都给出了自己的阐释,值得莎士比亚翻译和研究界高度关注。
1984年夏,在胡耀邦等的亲自关注下,孙大雨错划的“右派”得以改正,此前他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被摘去,当年的判决也被撤消。孙大雨要求工作:“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他用一句典型的孙大雨式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心愿,然而,复旦的大门对他却紧紧地关闭。
从1945年来到复旦到1958年因反右而被开除,十余年间,孙大雨人生的峰与谷都与复旦血肉关联,撇开政治观点的分歧乃至个人之间的恩怨,复旦也该有海纳百川的襟怀,一部复旦校史,怎么也绕不开孙大雨在复旦的人生刻痕,而我们却在复旦出版的几种《教授录》中觅不到孙大雨的名字。
“**”结束后,孙大雨已是古稀老人,他要抓住生命的尾巴,日夜耕耘不辍,还致力于英诗中译和中国古诗的英译。然而时间橐橐可闻的脚步已经步步近逼,到九十年代初,孙大雨已不能再伏案写作了。
1997年1月5日,我接到孙大雨逝世的讣闻。送别那天,我从四平路上的同济大学再次穿越市中心,赶到龙华。寒意袭人,天还刮着大风,有点凄凉的告别仪式让人更添寒意:来告別的百十**多是他的亲友和学生。孙大雨躺在鲜花丛中,安详的面容一如我几年前见他那样显得若有所思。
我想,不论人们识与不识,那座文化的峰峦已清晰地刻上了孙大雨的名字。